这场公开选妻,把我看吐了

前几天一条#中式恐怖#的词条,悄悄冲上热搜。
实景演出《又见平遥》中,一个名为“选妻”的表演段落引起争议。
这部分细致地展示了如何用封建标准衡量一个女性配不配迎娶,比如是否三寸金莲,手指如葱,掌纹不断,臀部丰满。
故事定位清朝末期,因此也有人辩解,这只不过如实反映历史。
于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这到底算继承封建还是批判封建?
在我看来,众多网友在表演中体会到的不适感,终究是最真实的。
《又见平遥》值得聊聊,但不光因为它身上的争议与骂声。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看透这“中式恐怖”的来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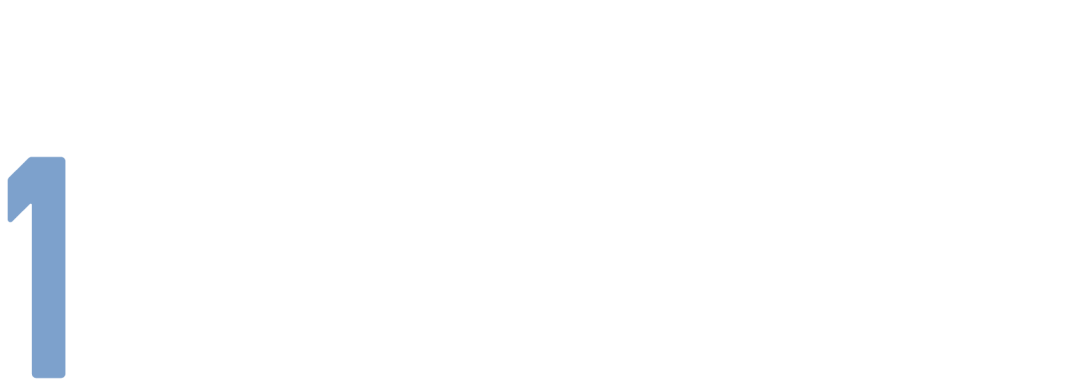
《又见平遥》是一出情境体验剧,一直因沉浸式的体验感而小有名气。
它讲的是清朝末年,平遥一家票号的东家赵易硕为救人,倾尽家产带人远赴沙俄。出行前,城里的百姓听闻这义举,纷纷给未娶妻的赵易硕送妻,有送自家妹妹的,有送嫡女的,只为让他赵家也留下血脉。
演出旨在体现忠孝礼仪的传统道德观,玩的是很旧式的悲壮叙事。
那么,《又见平遥》是故意搞男凝吗?
我不敢一句话说死。
一来,剧情上的爹味确实可以解释为“映射历史”,就好像一切古装剧都无法跳出三纲五常的文化背景,所有的批判也总得以展示为前提。
二来,《又见平遥》虽不乏男凝,但貌似也不缺女凝……
不过话说回来,我始终相信某种程度上的“所见即所得”。
作品意识哪怕再前卫,若观众只get到腐朽的表现,那又有什么意义?
《又见平遥》的问题是,它虽有些传统的气节,这气节却要以女性的牺牲来凸显;虽呈现了弱者的困境,这困境却被描绘地过于轻浮,因此显不出重量。
细说引发争议的“选妻”片段。
比谁的三寸金莲能放置在瓷盆里、谁的手指纤细雪白、谁的掌纹没有断掌(断掌克夫)、谁的背光滑白嫩、谁的面容姣好,最后比谁的屁股大。
其中,各位女演员穿着肚兜展示背部,向观众扭动臀部,动作香艳。
完全看不出这是正派的人家和全城的黄花闺女在结亲,倒像是逛窑子。
若谈“批判”,无论呈现方式如何,它总得有一种能被大众普遍感知到的苦难底色。
就像鲁迅《祝福》开头结尾都在写新年的热闹幸福,却不会有人真觉得这是什么“一起包饺砸”的欢乐时光。
而在《又见平遥》中,我相信只有女性能感受到这毛骨悚然。
紧接着,终于选出一位最”珍贵“的女子,夫家称其品性够好。她被披上红衣,当晚就为赵易硕留种。
为了体现男主的正派,他向该女道谢,结果女子说:
少东家
你选中我
是我的福分
我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个争气的女人
我要给你生个儿子
我愿意
使不得,夫为妻纲
我不能受你的礼
这确定不是《娘道》台词?
更可怕的是,赵易硕次日就离家干“大事”去了,而千挑万选只为让他一夜留种的夫人,难产死了。
女主的价值就是个血脉器皿,她的大义不凸显于人格,而凸显于子宫。
为体现赵家时代英杰,祖先们个个正襟危坐,道貌岸然,而刚刚那些被选的女子依然穿着肚兜环绕当中,尽显妖娆。
只有被选中的,为夫为死的夫人穿着得体、端坐中正。
对自己的死亡,她的自我评价充满自豪和觉悟(大意):
生都生了
死就死了吧
赵家这么多代
唯有我这个女子被允许牌位进祠堂
OK,“祠堂”这个词祭出来,这段插曲的性质根本算是定谳了。
更讽刺的是,她从头到尾只有一套着装:嫁衣。
当中,还有另外一场隐秘的婚礼,同样让人难受。
那段沐浴戏中,每位镖师都有一个长相喜庆的姑娘为其擦身。
镖师把女孩抱起,让她们咬自己,又因太太疼把女孩甩到跪地哭泣。
台词说着,这样即使死在路上,也有了最后的慰藉。
再隐晦,成年人也不难看出性安抚的意味,而这也便是女性在“丰功伟绩”前,能扮演的唯一角色。
和妻相比,这次上交身体甚至无名无分,只是纯粹的献祭。
这就是#中式恐怖#的含义:古代喜宴,对男人而言才算喜事,对女人而言,那是下半生的丧礼。
而时代进步到今天,为何仍有这种以大义为名的“丧事喜办”?
“娶”字由“取”和“女”组成,本义为远古时代劫女为妻的抢亲风俗。
这是来自字典的解释。
可见,在整个封建时代,婚嫁之喜往往是以剥削为本色的。
《又见平遥》里,个体被整合进宏大叙事中,女性被展示身体,说着自豪于为男人牺牲的话语,完全是没有感知的工具人,所有情感都被抹除。
是他们太关注大义忘记个人表达么?也不是。
镖师们的表演中有大量个性化表达,比如牺牲后,镖师鬼魂有的说想回家吃碗面,有的说想念自己的女人等等。
人虽死,人情味还在。
而女性角色却恰恰相反。
女性感受被清空,意味着封建婚礼针对女性的迫害和残忍,被创作者代替女性容忍了、宽恕了。
而这也即是所谓“恐怖感”的核心来源。
我想起一些主题类似,却更加有时代性的表演。
张碧晨和孟佳的《三拜红尘凉》。
一出场,两人扯掉红面纱,风韵又不失表达感地开场。
她们全程保持淡淡的忧伤氛围,以古代女子视角,向现代观众们诉说着她们的悲凉处境:
听那锣鼓喧天 谁伴着泪眼
荒唐的婚姻在世间
从未有相见却能牵住红线……
一拜天地日月
二拜就遗忘这一生
唱到喜宴后,余生喜乐悲欢都无关,自己将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时,往地上倒酒——
人还活着,却已开始祭奠自己,妙绝。
曲终音落,当观众以为表演结束时,点睛之笔来了。
舞台旁边突然响起喜庆的唢呐声,一只迎亲队伍来到舞台中间,为两位”新娘“披上她们才刚刚扯掉的头巾。
此刻,她们连诉说都被剥夺了,乖乖被困在薄薄的红头纱里,变回一个温顺的玩偶。
这个仅几分钟的舞台好在哪?
好在它向观众传达了女性个体的感受。
相比之下,为了彰显某一主体,先抹掉女性的话语,再代替她在空白的对话框中强行填上臣服、献媚的表达,其间差距可谓高下立判。
说到底,网友揶揄《又见平遥》为“中式恐怖”,恰恰切中了它的伪善——
借的是弘扬传统的名义,说的却仍是宗族文化、封建道德、父权制度、三纲五常的东西。
虽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旧时女性的遭遇,却用喜庆、香艳的呈现,掩盖了其深层的强迫性质。
把伤害包装成美好,称一句恐怖便不为过。
说来讽刺,反而是一些以”中式恐怖“为主题的鬼片,反而更着重于女性的遭遇。
《倩女幽魂》系列,讲的都是混乱世道下,人不如鬼的社会状况。
第一部,聂小倩虽是鬼,依然躲不了被作为性资源摆布的命运。先被树妖姥姥利用来诱骗男人,又被许配给需要巴结的黑山老妖。
小倩着红衣时华美至极。
但嫁人时,黑暗蒙蔽红艳,她被扇巴掌,被组成黑山老妖的千万个男性人头啃食。
无论生前身后,她都不曾有过选择的权利和自由。
第二部,傅清风和宁采臣两情相悦,却被许配他人。
出嫁时的嫁衣造型至今经典,但美丽并不代表喜乐,她落寞和眼泪依然述说女性之悲痛。
再到聊过n次的《梁祝》,祝英台泣血无人管,红衣加身如囚服,凤冠上头如枷锁。
红衣和婚礼再美,始终和女性自己的幸福无关。
她们始终匍匐跪倒在地,下半生注定囚禁于一场“喜宴”。
反而,唯有扔掉男性视角下“美丽的”凤冠,她们才能重获自由。
这些作品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先进意识,只是足够诚实。
诚实到不会无视历史的暗处,不会拿弱者的血泪来装点伟大。
说到底,《又见平遥》的争议不是素材上的问题,而是表达上的问题。
展现落后的意识形态没有问题,关键是以怎样的角度去使用。
例如莫言写《丰乳肥臀》——
“她是铁匠的妻子,但实际上她打铁的技术比丈夫强许多,只要是看到铁与火,就血热。热血沸腾,冲刷血管子。肌肉暴凸,一根根,宛如出鞘的牛鞭,黑铁砸红铁,花朵四射,汗透浃背,在奶沟里流成溪,铁血腥味弥漫在天地之间。”
他其实也荤腥不忌,对女性躯体的勾勒、幻想大大方方。
但丰乳肥臀的美在这里不为物化或凝视,反倒是一种强大、震撼的母性象征。女人的肉体能孕育整个世界,更能撼动整个世界。
又如《色·戒》中,同样要以女性的被动献身去完成伟大的事业。
但在李安的解读中,王佳芝的力量是聚力万千的。她不是在,而是以女性的躯壳,轻易瓦解了整个父权结构。
不求如今的文艺作品能达到相似的思想高度,但起码,不要无视现实。
传统婚礼的黑暗性质,其实到现在都仍有残余。
例如“扔筷子”这样的婚俗。
新娘出嫁,要往后扔一把筷子,寓意不再吃”娘家饭“,和原生家庭一刀两断。也有说法是表示不带走娘家的财富。
所以很多新娘在扔筷子时不舍、痛哭,但还是被强行履行。
这和所谓“泼水”的仪式其实是一个道理。
又比如“做性子”。
让新娘坐在簸箕里抬回家去,一个人放在祠堂列祖列宗面前,意在搓掉其锐气,进门后温顺,孝敬公婆。
还有“离娘肉”。
娶亲前,男方要准备几斤猪肉给女方送去,有的地方还要附带猪腿,这个肉就叫“离娘肉”。
什么来由呢?飘翻到其中一个版本,让人汗毛直立——
有一媳妇对婆婆不好,被神仙变成一头猪后又被丈夫宰杀。丈夫得知真相还觉得她罪有应得,砍下一只猪腿拿去了岳丈家。
还有的地方让新娘妈妈在婚礼割一块猪肉,象征和女儿的分割。
这些仍然留存的婚俗,无不遵循着类似的逻辑——
娶亲是一次交割仪式,新娘则是任人处置的鱼肉。
恰如《倩女幽魂》中宁采臣的慨叹,原来无论是人是鬼,她都逃不过身不由己的命。
1987年的呈现,依然映射着今天某些女性的困境。
反而现在还有这么多场景,在擅自替她们吹起唢呐?
当男演员展示着强壮和伟大时,女演员跪在一旁,卑微地低下头颅。
当男演员展示悠久文化内涵的面食文化,充满力量感时,女演员集体裸背对着观众席扭臀,展示身体……
飘常说,女性困境,是一张结构性的网。
这事单独摘出来看着好像是挺小的,但若掌握话语权的创作者们,都以这种充满爹味的视角代替我们,那么这张网格就会密一些,又密一些。
《梁祝》中,祝英台非要死亡才能素面归真,重获人权。
但《又见平遥》的女性,由生到死,在剧中是续种的工具,在剧外又是煽情卖情怀的工具。
至死,都不能解脱。
中式恐怖,不过如此。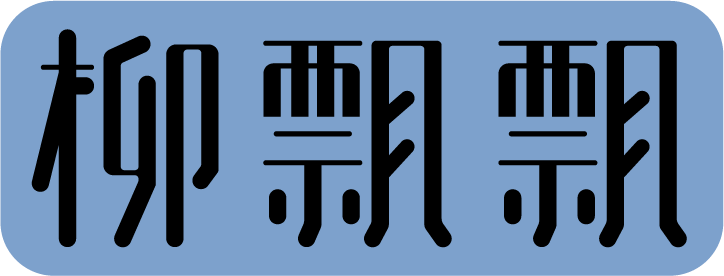
中式的恐怖不是鬼,是无视人性的人
↘↘↘
阅读原文 关键词
镖师
《又见平遥》
女性
女性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