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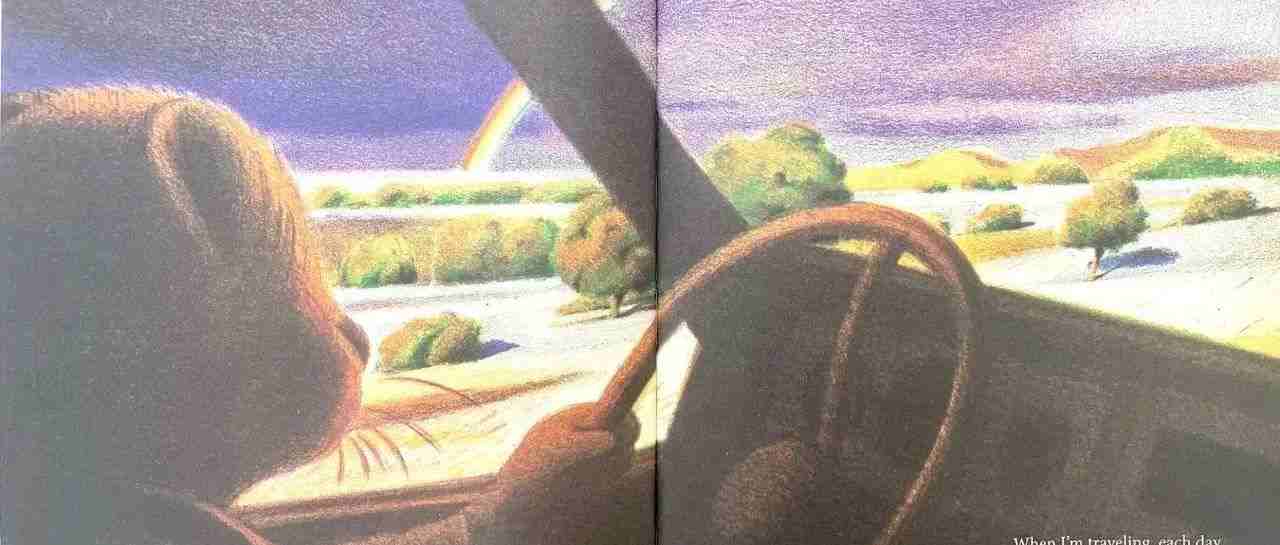
小乐写在前面:
这是一篇由几句狠话引发的故事,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萌发了为此“写一篇小说”的疯狂念头。当想到可以以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创作”时,顿时感到因为疏离而带来的轻松有趣。当晚写完了一稿。修改了几遍之后,咬牙发出来。整个过程有很多体会和感受,是很有意思的“初尝试”。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还请多多关照。
“你能不能不要和妈妈说话?
”为什么?可是我想和你说话啊!”
“你下午不是不想和我说话么,现在我也不想和你说话!”
“哎哎,老婆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因为他的做法有问题你也错给他看,你要教给他对的做法。”
“你闭嘴!”
她知道他说的对,所以不能说理,只能蛮横。但这不够解气。“FXXk!”骂出这个词儿之前,她正在切白菜,趁着这口恶气,顺手把菜刀一砸。
瞬间就安静了。“法克…法克“ 背后传来天天的声音,无知无畏的让人心慌。“法克,法克,大克大克,压克压克,法克大克压克…” 小孩不咸不淡玩儿起rhyme, 似乎没有参透那个简单发音所代表的意思,包裹的怨恨,或者说来自成人世界的脏。
丈夫已经不在身后,她拿起菜刀继续对着白菜撒气,同时启动前额叶,试图梳理这么大火气打哪儿来。
答案并不远。 下午全家都在孩子上了一学期武术课的活动中心看年末汇报演出。雨时停时下,孩子的表演凑合能看。报这门课纯粹因为他的好朋友在,武术课上了几个月也没见他感兴趣,总站在最后一排,学的心不在焉。每次朋友缺席,他就也不想去。在这个年龄,对于一个慢热的孩子,朋友是尝试新鲜项目的决定性变量。
本来课外班学什么也不重要,问题在于要宁凡接送,而且上课时间只有50分钟,干什么都很尴尬。这学期几乎每天下午都是这样,时间被搅的稀碎。这么折腾自己,孩子还意兴阑珊,不如别上。
天天上小学三四个月了,她还在努力适应这种四六不靠的时间表。学校的课后托管没有报上,每周四天两点半放学,一天一点半放学。早已习惯了幼儿园五点半放学,突然多出来下午大块的空白,只能用各种课外班填上。就这么稀里糊涂慌里慌张的报了7门课后班,打补丁般填充时间,时间表上还是有几块让心烦的空白。以前总觉得自己不是那种给孩子时间排满课外班的妈妈,但如果不上课外班就意味着自己要陪,她怕。
后来她知道,课外班大多只有一小时,加上接送的时间,还是每天下午早早就没法工作了。与其满腹怨气,不如调整期待,早睡早起早干活。失望好像是少了,但并没消失。当工作越攒越多,当他上课不情不愿时,还是会忍不住埋怨。最糟的是他对你的牺牲不知情不领情,仿佛一副理所应当。理所应当是所有关系里都要不得的心态,但你能拿孩子怎么办? 丈夫这时总会安慰她,让她找自己最轻松的方式,但哪里有这样的选项。她有时都希望自己是那个在一小时车程之外上班的人。
比如今天下午,虽然表演磕磕绊绊,但好在活动丰富,孩子们一波波上台。小孩子的表演总是让人开心的。甚至有几个瞬间,当看着台上不同肤色,带着伊斯兰头巾的孩子,唐氏症的孩子都洒脱自信的舞动着身体、毫无保留的相互喝彩时,宁凡想到新闻里世界充斥着割裂与无知,灾难和战火,心里还是生出了感动。当时都想好了,要以“我们看新闻,更需要看身边的生活” 为主题写一篇文章,她都两个多月没有更新公号了,想到就心焦。想写的很多,时间太少。
看节目的时候,她的手表总在震,那是说好下午在附近公园见的朋友发来了消息。“我们到了,你不着急。”“ 我们坐到咖啡馆里面了。” “你们大概几点来?我们想着要不要先去买个菜。” 很客气,但逐渐透露焦急。
没个准点的约会,当然让人急。她有点后悔约了这个下午,原本以为表演两点多就能结束。谁知下雨,上台推迟,演出时碰到幼儿园同学又要一起玩,然后又要在餐车吃taco, 爸爸给买了,他又因为里面有菜不想吃了,丢给了爸爸。
正打字告诉朋友大概半小时后过来,天天突然宣布“我要走了”。好不容易在人群中钻了出来,准备离开。一群阿婆上台跳起了hip hop。这恐怕是今天最好看的节目了。她停下脚步,拿出手机拍视频,自己也跟着扭了起来。多好,这就是明天的我啊,从现在就开始练,到时候我肯定是最靓的奶奶吧。宁凡边看边美滋滋的憧憬着未来。
1分44秒的视频结束后,她心情雀跃的加快脚步赶上了丈夫和儿子,却看到天天正闹脾气,拖长了音嚷嚷:“走,走,妈妈为什么不走”。
“妈妈看婆婆们跳舞好开心呀。“
”你为什么看婆婆跳舞要开心?为什么?”
这问题来的气势汹汹,无从回答。问题里没有好奇,只有抱怨。又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他是世界的中心,他想留就要留,想吃就要吃,想不吃就不吃,想走就要走。他的理由通通都是 “because i want to”。告诉他了一万次 “你想要”不是理由,他还是不懂,他就是想要。每次她都为这个如此理直气壮好的自我中心,以及难以撼动的任性搓火。没孩子之前,她对孩子和自己唯一的期待就是通情达理。
但直到今天,宁凡依然在努力调试自己去适应一个不讲理的孩子,都七年了。她是学政治的,不懂儿童心理学,只是觉得孩子和成人完全是两个物种,而孩子总是更有权力。有时她甚至觉得越是擅长用道理和逻辑立足于世界的人,就越难和孩子沟通。因为道理的世界,一切都有条有理、因果清晰,整整齐齐,但小孩子运行起来无序混乱不管不顾,像个外星生物。这两个界面之间没有简单接口,只有生拉硬拽,在无数次碰撞摩擦中,让小孩建立起秩序和规则。
已经不记得怎么边走路边应付着一个吵闹的小孩上了车。她懊恼着上一秒还开开心心的,下一秒就被搞得心烦意乱。在爸妈陪了他好几个小时之后,他凭什么不满意妈妈多看了1分44秒的演出。“凭什么” 是她明知很蠢,却无法按耐的句式。虽然她知道答案,凭什么?就凭他比你晚来世界的几十年。
终于和友人在公园见到了。刚开始天天也开心,但很快开始叫冷。爸爸回车给他拿外套。穿上后还说冷,要回家,怎么说都没用。对方是没孩子的年轻夫妻,看孩子闹起来当然识趣的说那就下次再聚吧。
走到车边,天天不肯上座位,“如果我坐到位子上,你们就要给我买麦当劳”。果然讨起厌来可以用无边无际,他的弹药充足,随时随地发动进攻。
“你必须坐在安全座椅里,并且不会有麦当劳吃。这两件事情没有关系,本来晚饭吃什么可以商量,但你用这个条件来要挟我们,我们很不高兴,晚上不会再吃它了。“
丈夫说的宁凡没意见。但天天叫嚷的更不得安宁了。在高分贝的背景音下,她竟然还有力气和丈夫商榷了一下“要挟”这个词用的是否合适 ,一路吵吵闹闹的到家了。
然后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白菜还在切,她带上耳机,长按启动了降噪,耳边立刻清净了,剩下的只有那个被称为最懂中餐的英国女作家的声音,她正读到新书中关于宋嫂鱼羹的部分,原来宋嫂鱼羹的英文是The Harmonious Geng:
”中国古代文学中,人们常常把治理国家的艺术比作给 "羹 "调味。公元前六世纪,齐灵公的政治顾问晏子在试图解释为什么政治中的和谐--来自不同意见的融合--不同于盲目和谄媚的附和时,使用了一个著名的烹饪比喻:
和谐可以比作 “羹”。你有水、火、醋、肉馅、盐和梅子,用来煮鱼和肉。先用木柴把水烧开。接下来,厨师将各种配料混合在一起,用调料调匀,不足的添加,多余的去除…厨师和君主的共同使命是创造和谐。统治者将为他服务的人的才能进行混合和搭配,以创造和谐的国家和社会,而厨师则对食物进行切割、混合和调味,以创造和谐的口味。令人惊奇的是,同样的原则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厨房里依然行之有效。现代的中国厨师和古代的大臣一样,仍然试图从对比强烈的食材和调料中创造和谐与平衡,从它们的颜色、质地和味道的微妙相互作用中组成他的菜肴和菜单。我的朋友在向我解释菜谱时说:"你只需要加一点糖,不是为了品尝它的甜味,而是为了调和菜肴的味道。在中文里,"和 "与 "调 "是同一个字。
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尤其是南方,汤匙仍被称为 ‘调羹’。"
“调羹”,原来故乡的方言背后还有这样的故事。这让她觉得亲切,放松了下来,想自己出门待一会儿。书店八点关门,还来得及去待一个多小时。
“我要出去一下”,她宣布,语气中透着点深思熟虑和趾高气昂。“ok”,丈夫语气简短又平淡,让她有点泄气。但也就是一点而已。年轻时和男友吵架,夺门而出,心里演的的是一出戏,言情剧对女性在此刻反应早就敲定了剧本。过了那个年纪,在冲突中离场更是一种方法的执行—在另一个空间整理和重启情绪,从而以稳定态回到生活。和丈夫在一起十多年,他们早就了解彼此的脾性。他知道她身体里的某个系统正在努力工作,平息自己,她知道他知道。他们之间有牢固的信任和充分的理解,偶尔的争吵也是来去自如,有时候甚至爆发都成了一种把早已打包丢进阁楼的战斗力拿出来测试一下,体会还没丧失这个能力的乐趣。
开车去书店的路上,宁凡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她常被人问到为什么能读这么多书,都在哪里买书。仿佛读书成了可以炫耀的事,就像另一些人的名牌包包或腕表。这些年,越来越多人开始“晒”读书,当然读的多读的高级,是纸质书,在独立书店买书,仿佛都成了微妙的彰显一个人能力、品味或者道德的标记。
也有一段时间,当被人问到的时候她感觉挺好的,但同时也窘迫。直到有一天她突然明白了,不停地读书,在独立书店买书,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不得不。或者说,她的生活里,没有太多其他地方可去,其他有意思的事情可做。书店,成了她需要逃避生活时的避难所。那是在她内心兵荒马乱时,给她故事,诗歌,知识,绘画,给她空间和时间平息风暴的地方。
多年前和当时的男朋友常吵架。在异国的城市,她总为无处可去感到绝望。如果在国内,叫上朋友,K歌,吃夜宵,哪怕只是在街上散散步,情绪也就散去了。而那个如野兽般无尽扩张的庞大城市,这些都没有。那些时刻是年轻时她对孤独最深刻的体会。也是从那时起,她知道了宏大和微小,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微妙关联,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urban girl。
在有了天天的前几年,宁凡逃离生活的念头愈加频繁。和婴儿朝夕相处的日子,各种感受格外剧烈,幸福和厌烦跌宕起伏。好在那时搬到了开车几分钟就有好几家独立书店的小城。也从那时候开始,她养成了逛书店的习惯。在书架前,目光移动于一本本书,人就被吸进那些词汇,句子,和揭开新鲜帷幕的世界。在这样的短暂时刻,生活的窒息和琐碎忘记了,对自己的失望放下了,对孩子和丈夫的埋怨飘散了,连自我都默默隐退了。
后来疫情迟迟不绝,书店作为“生存必须” 早早被允许恢复了营业。无论现实有多魔幻,一家人分秒挤在一起的生活多让人发狂,只要钻进书店,哪怕带着口罩,也感觉自己在大口呼吸。在这艰难的几年里,书店于她,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让人硬撑下去的精神支柱。真相前所未有的直白,没有购买,书店就会死掉,而她也将失去自己的避难所。了解这些,买书的选择也就顺其自然了。
最近一年,大疫远离,孩子也大了,但人生依然有解不开的脚镣。身份不自由让她难以跨越国家边界,财务和时间不自由,也没法四处旅行。再一起,幸好有书店。行万里路太难,读万卷书触手可及。目光在纸面奔跑不能替代真实的体验,但思想的自由足以飞跃现实的边界。
原来,对书店的依赖是这样一点一点长起来的。她不是道德或品味高尚,也不是有钱有闲,反倒是那些“没有”,那些束缚,和对现实的无能为力,把她推向了书店。
顿悟的那一天,她买了宫越晓子的I dream for a Journey。 被困在日常生计中的旅店看守人,听着客人们讲着远方故事,总梦想着属于自己的旅程。终于在梦里带着旅行箱,坐上飞机,踏上夕阳下的海滩, 探望昔日老友。当越走越远,远到开始思念自己的小旅店,他睁开眼睛,继续接待入住的客人。 终有一天,他会踏上旅程,去往远方,而这会让所有人感到吃惊。 宁凡在书店翻看过这本书好几次,模模糊糊觉得不错,却抓不住那故事,踌躇着也就放了回去。此刻,她无比想念这本书,想念那只困在生活里梦想去远方的小熊。此时此刻,没有什么比这只小熊更懂她了。
停车进店,碰上的是店主布莱德。在店员推荐的书架上,宁凡知道他是一个喜欢看晦涩的哲学,语言学和电影史的男人。他总埋头在店里搬书,很少与人搭话。但今晚,看到她进门,布莱德满脸温暖的笑 “Hey,Fan, 很高兴看到你,你这周过的怎么样?”。 避难所的存在已经够好,但更好的是那里有了解和关心你的人。
打烊前五分钟她离开书店时,背包重了一点,心也满足又愉悦。回家路上,她想起爱丽丝.门罗的《逃离》和克莱尔.吉根的《南极》这两个关于女性逃离婚姻生活的故事。就算是婴孩,都有被玛格丽特.怀兹.布朗揭示了真相的《逃家小兔》。
也许世上每个人都有出逃的渴望,谁也无法掐灭那或许微小却永恒燃烧的火焰。卡拉心里的针一直在,倘若那个女人没有被冻死,也应该还会有下一次重蹈覆辙。
她们的家附近可能没有书店吧?刚冒出这个猜想,宁凡就觉得自己可笑。但谁又知道呢?如果多一点书店可以在夜晚亮着灯,人类的孤独、危机、空虚和苦难可能都会少一点点。
回到家,父子俩都睡了。 孩子在学习着成长,丈夫是好意,她也不过是一个疲惫的妈妈。不是每场事故都有单一明确的过错方。很多时候,谁都没做错,但事情会突然变得无比难看,这就是生活。幸好,她有避难所可去。太阳升起时,迎接她的也会是家人的拥抱和理解。
- 相关往期文章 -
- 版权声明 -
文章版权归成长合作社所有
欢迎转发朋友圈
转载请联系我们
- 关注我们 -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