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人拥有一切,除了睡眠 | 谷雨

人类的古老反应模式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一间10平米的白色诊室里,下午时分,睡眠医生范滕滕迎来了17位患者。
第一位女士从700公里外的山东烟台赶来,34岁,脸色蜡黄。她说她白天上班,下班带娃,然后就是和丈夫吵架。到了睡觉时间,她没有一丝睡意,而身旁的丈夫“呼”一下就睡过去了。这位女士感到气愤,“我就一宿在那儿躺着,睡不着。”
“平时有什么感兴趣的事吗?”范腾腾问。
“没有,跟我对象一吵架,就更没有想吃的,没有想玩的。”
“那周末都干点啥啊现在?”
“带孩子写作业。”
大家为睡觉这事而来,但倾吐的都是人生困境。一位职场年轻人说工作压力大,没睡好,心率蹦到了120,但这不是关键,他非来不可的理由是,他的上司因为失眠,已经耳聋了;一位父亲带着高中三年级的女儿来看病,这孩子一上课就犯困,一睡着就起不来,医生说可能是发作性睡病,让住院三五天查一下,父亲一听急了,“那不行,高三没时间”;还有一位80岁的大爷,戴雷锋帽,背黑色双肩包,风尘仆仆地推门进来,大嗓门一喊,“医生,我睡不着啊,晚上我只能坐公交车满北京城转。”
一百个失眠患者可以说出一百种感受。一位来复诊的女士形容,每天晚上都很困,但一躺上床,就如同站在一堵高墙面前。她努力从墙角往上爬,总算要爬到墙头时,“啪”掉了下来。她感到绝望,“持续十几次都是这样,永远翻不过那堵墙,真的困死了。”
面对这些为睡眠而焦虑的人,范滕滕总是专注地看着对方,说话轻声细语。他是中国第一个睡眠医学专科医师——2014年,北京大学在国内第一个设立了睡眠医学的课程,范滕滕是那一届唯一的学生。在睡眠医学里,睡眠障碍有100多种分类,失眠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门诊一年接诊近2万人,其中失眠患者超过三分之一。而根据2010年中国睡眠研究会公布的调查结果,每10个成年人里有4个人失眠。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失眠的背后往往是焦虑,是内心潜意识的一些冲突。就像海里的冰山,失眠只是浮出海平面的一部分。”范滕滕解释道,“单纯地用镇定安眠药,短期内是有疗效,但长期来看,药物并不能根除失眠。好多患者跟我说,给我开镇定最强的药,我开玩笑说,你打一针麻醉剂就可以了。”
来到医院的失眠患者 ©视觉中国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有两位睡眠医生在中国医师协会的网站上发布了《防控时期健康睡眠手册》。手册里这样写道: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的关键时期,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或多或少产生担忧和恐惧。失眠和恐惧一样,是我们人类的古老反应模式。面对危险,我们的反应模式只有两种:“战”或“逃”。无论哪种,我们的睡眠都必然会受到影响。可以想象,远古时期的人类面对自然灾害或者猛兽,无论是与之搏斗,还是躲避起来,都是无暇安然入眠的。
豆瓣小组“睡吧”是失眠患者的聚集地,组长李明告诉我,新冠疫情以来,小组的成员数呈爆发式增长。这个小组成立12年来,有7万多人加入——近3年成员数直接翻倍。
李明是一位软件架构师,定居澳大利亚。他说,每到很热的夏天和很冷的冬天,来小组里求助的人就会增多。而一到春秋的舒适季节,以及法定节假日,尤其是十一长假时,求助的人又会显著减少。他的推断是,天气好不好、能不能出门影响了很多人的睡眠状况。而这三年,失眠患者就像潮水一样涌进了睡吧。
“疫情期间在家待着不上班吃了睡睡了吃……突然有一晚到凌晨四点才有困意……结果越急越睡不着……大家能给我点意见吗?”
“在美国读书,(2020年)5月底的时候,因为疫情被关了将近三个月的我彻夜失眠了……每天隔着时差跟我妈哭诉。”
“真的好痛苦,没工作+失眠,已经大半年了,谁能帮帮我?”
“担心家人有点咳嗽怕得了肺炎……一整夜心慌不能平复,躺下闭上眼睛身体还抽抽,眼皮很乏,身体却僵硬……我该怎么做?还有不知道多少天的煎熬!”
睡吧奉行的准则是,组员间互帮互助。就像患者去医院看病一样,先填写一份睡眠评估,然后发布在小组里,评论区便会有志愿者(身经百战的失眠患者)前来给予建议。但疫情后求助的人实在太多,而且大部分选择了私信,而不是按组规公开发帖,小组里二十多个志愿者也不堪重负。作为组长,李明只好在组规里加了一条:私下求助他人需要按对方时薪付费。
即便如此,一位失眠的全职太太仍主动私信了李明。她有一位很能挣钱的老公。她的生活是这样的:带孩子在小区公园玩,刷手机,吃外卖,做美容,修指甲。听起来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但这位女士失眠了——那意味着,哪怕拥有再美好的生活,她也无法真正享受这一切。
“她精神状态不太好,就算给她看小组里的文章,也不太能看懂。平时也没什么人可以去聊天,没什么事可做,感觉比较孤独。”李明说。在打了五六次电话后,全职太太的孩子到了去上幼儿园的年纪。李明提议,不如趁机去学一项技能。讨论来讨论去,女士选择去一家美容院当学徒。那之后,李明再也没接到她的电话。
在失眠这件事上,李明有15年的实战经验。第一次失眠出现时,他还是一个沉默寡言、总是学习到凌晨两点、身体孱弱到跑步只能跑两下的高三学生。“我晚上睡不着觉,脑袋里就有一个想法,因为我住在五楼,结束这个痛苦的最快方法是——从这个楼上跳下去。”
上了大学,住进集体宿舍,他的失眠顿时好了。但世界杯一来,他便开启了晚上看球、白天睡觉的日夜颠倒模式。起初问题不大,白天他也睡得着,但就像站在摇摇欲坠的悬崖边上,一根手指头就可以把他推进失眠的深渊——同寝室友养的2只猫生下了4只小猫,一到清晨就是群猫乱舞——李明再一次失眠了。
“我发现这个失眠是接二连三的,而且每次情况都不一样,我就不太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是一个工程师嘛,我希望把事情弄明白。”由此,李明在2010年成立了“睡吧”。
你不可能永远22岁
“引起睡眠问题的原因实际是很复杂的,精神心理因素是一个最常见也最高发的原因。现在国内已经有数据表明,这两年出现焦虑问题的人,可能有八千万人,这些人受到不良情绪的影响,当然也出现了睡眠问题。”电话里,62岁的郭兮恒告诉我。
他是朝阳医院睡眠医学中心的主任,有长达37年的睡眠医生从业经验。一次在给上百人讲课时,他接通了一个反复打来的陌生电话。“郭大夫,我今天是要跟你道别的,我不想活了,最近又睡不着了,实在太痛苦了。”这位失眠患者同时患有重度抑郁。好在郭兮恒最终劝住了他。
和范滕滕所在的精神科不同,郭兮恒归属于呼吸科。这就是睡眠医学的特别之处了,它是多学科交叉,还包括神经内科,耳鼻喉科等。睡眠医学的发展不到百年,而国内的睡眠医学始于1980年代,那时,郭兮恒的研究生导师、北京协和医院的黄席珍教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睡眠呼吸实验室。而今,国内不同等级的睡眠中心至少有5000多家。
人们因为失眠而来到睡眠门诊,但郭兮恒解释道,失眠既指睡眠障碍里的失眠症,同时也指一种症状,比如有人有呼吸系统疾病,因为呼吸困难而睡不好觉,则属于继发性失眠。
“这两年就存在一个问题,有些老年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肾功能衰竭需要透析的,这些疾病都要定期去医院检查,但要么可能进不去医院,要么能进去他又不敢去,怕自己被传染(新冠),导致过去规律的治疗变成了不规律,睡眠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要找出一个人睡得不好的真正原因,常常需要借助一种检测手段——多导睡眠监测。我曾跟随北大六院专门负责监测的技师旁观过整个过程。被监测的人需要住院。夜里8点,技师推着一台笨重的台式电脑进入病房。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一张给患者,另一张给陪护人——谁也不知道睡着睡着会发生什么事,郭兮恒曾有个患者在做睡眠监测时,夜里11点多突然出现严重的呼吸暂停,抢救到次日仍去世了。
那台电脑上连接着几十条五颜六色的电线,它们的末端是一块金属贴片。技师用胶带把它们分别黏在了患者的手、脚、胸、以及最重要的头部上——那样子看起来像进了ICU,曾有一位患者自拍一张发给领导,“我能请一天假吗?”领导回复,“请一年都行。”这些线最终在电脑上呈现为几条正在前进的曲线,那是脑电图、眼动电图、心电图、肌电图等——简言之,患者的大脑和身体被数据化了。
失眠患者进行睡眠监测 ©视觉中国
睡眠医学上曾有一个词叫“矛盾性失眠”,大意是,你觉得你睡得不好,但多导睡眠监测显示你睡得挺好。这个说法直到近年来才被取消。一位睡眠专家向我解释,失眠向来更看重主观诊断,也就是,“你觉得你没睡好就是没睡好。”对于睡觉这件事,科学家们至今也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生物学解释,“人怎么睡着睡着就醒过来了,醒着醒着怎么就入睡了,睡眠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都是最本质的脑科学的问题,人类还没搞明白。”
在郭兮恒的睡眠门诊里,他发现一点变化,以前他的常客更多是因为年龄变大而睡眠变浅的老年人,而近些年来看病的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多。不久前就有一位22岁的年轻人来找他问诊。
年轻人说,他晚上失眠,白天犯困,然后工作上就出了差错。来睡眠门诊看病是他挽救工作的最后一个机会——老板声称要开除他。至于他是怎么失眠的,起初也没什么特别,就是凌晨两三点睡(和工作无关,纯粹是撒不开手机),有时熬一宿,第二天再补觉,然后在某一天晚上,他想睡也睡不着了。这个落魄的年轻人既焦虑,又自责,“郭大夫,我怎么脑子就不好使了?”
事实上,这个年轻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眠(有条件睡但睡不着),而是长期的睡眠剥夺——该睡觉的时候人为地不睡觉,然后想睡的时候也睡不着了。按睡眠医学的标准,失眠分为短期失眠和慢性失眠,前者可以自愈,后者久病难医。郭兮恒告诫年轻人,“虽然你还年轻,但你不可能永远22岁。”
范滕滕有一位45岁的患者就尝到了睡眠剥夺的恶果。那是一名互联网公司的高管,他不仅“996”,还总是凌晨几点给员工发邮件。如果不是降压药也降不下来的高血压,以及两次突如其来的心梗发作——在北大六院,心内科和神经内科的医生告诉他,没查出太大毛病,建议转诊睡眠科——这位高管根本不会走进睡眠门诊,他对范滕滕说,“我没有时间睡觉。”
后来高管才知道,他不是心梗,而可能是睡眠不足导致的急性焦虑发作。治疗后,他先是恢复了睡眠,然后奇迹般地,高居不下的血压也降了下来。
“他就是人为地睡眠剥夺,本来能睡好觉,但睡前非得来3杯咖啡。”范滕滕说。“上次有一个记者问我,‘范大夫,你听说过什么叫奋斗型失眠吗,就我白天工作一天,我996了,晚上好不容易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我不睡觉,我要刷下手机,玩玩自己的。’这根本不叫失眠。”
根据《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2)》,中国人每天平均睡眠时长已经从12年前的8.25小时,降到了如今的7.06小时(还能拯救),而20世纪初,人们的平均睡眠时长有10个小时(难以置信)。
作为这份报告的指导委员之一,郭兮恒说,以前他上电视节目的时候会说,成年人的睡眠时间正常是6-8小时,“后来我发现,大家越睡越短,我说睡够6小时属于正常,有人就敢睡5个小时。现在我调整了策略,就说合理的睡眠时间是7-8小时。”
失眠又短暂地消失了
作为一名真正的、身经百战的失眠患者,睡吧组长李明尝试过各种解决办法。他看过心理医生,看过中医,也尝试过瑜伽、冥想、户外运动这些非药物的方式,最终他得出结论:本质上没有帮助,因为下一次还会失眠。
在失眠了将近10年后,李明决心要根治它。他开始查阅各种文献资料,国内相关研究少,就啃起了几本和失眠相关的英文书。
彼时国内针对失眠的治疗方式只有一种:吃药。根据范滕滕的老师、北大六院院长陆林2020年主编的《中国失眠障碍综合防治指南》,目前被批准用于治疗失眠的药物有:部分苯二氮受体激动剂、褪黑素受体激动剂、部分抗抑郁药、食欲素受体拮抗剂等。以及,书中提到的“虽未被美国FDA批准但广泛应用于临床的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
药物治疗 ©视觉中国
在范滕滕的睡眠门诊上我就发现,几乎每一位患者都会问:这药有副作用吗?范滕滕的回答是,你的担心产生的副作用可能比药物的副作用还要大。这当然只是一句玩笑话,因为在开药这件事上,他已经做到了极其谨慎,“使用药物有两个原则,一个是选择副作用相对小一些的,第二就是短期阶段适用的。”
在李明看的那些英文书里,一位美国睡眠医学博士撰写的书引起了他的注意。“我看过够多东西了,但他介绍的这些东西我从来没听过,甚至我去看心理医生,他也没有提到过这些理念。”那本书里介绍了一种全新的、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简称CBTI)。尽管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李明说,仅仅只是读完那本书,他当晚就不失眠了。
两年后的2012年,睡眠医生张斌翻译了一本同样来自美国、更加系统地讲解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的书《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如今已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精神科主任、睡眠中心主任的张斌告诉我,那本书算是CBTI在国内的正式引入。“头三年出版社的老师就会抱怨,你那三千本书还没有卖出去呢。”张斌在电话笑了起来。
“大约是在2015、2016年的时候,突然出版社就给我打电话说,再写一本吧,这个书已经都卖没了。后来我知道他们重印了很多次。”2017年,张斌主编了《中国失眠症诊断和治疗指南》,在其中,他正式把CBTI定为失眠的首选治疗方式,认为其疗效优于药物治疗。
如果翻开那本薄薄的、只有一百多页的《失眠认知行为治疗》,仔细查看CBTI的所有事项——CBTI把措施分了两类:一线和二线,前者最重要,后者辅助于前者。而作为仅有的三个一线措施之一的“睡眠卫生教育”,一共有14小条:
14、避免白天打盹
看到这些,想必你和我一样困惑,这简直就像上学时悬挂在教室墙上的行为准则,它看起来条缕清晰,过于简单,但你又很难保证自己一定能做到,或者说根本做不到。而最让我困惑的是第11条——别把问题带到床上。我还能控制自己的大脑不要在床上思考问题?
张斌给的回答非常有技术性。“有什么问题,你就用纸记下来,或者记到手机上,这个东西我搁到那儿了,有这么个形式的动作。然后告诉自己,现在想也没用,明天再想。”
这些方法对李明很见效。那时,他像一个标准的三好学生那样,严格地按照CBTI的要求去做,那些凡是身为现代人都难以抵挡的诱惑,他都一一拒绝了,过着看起来最健康的生活。“我不会参加一些晚上的聚会,也不会去做一些非常激烈的事情,我也不会去喝咖啡,晚上我会早早地上床睡觉。”
但奇迹没有眷顾他,一段时间后,李明又失眠了,而且还有了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次失眠,次数多到他根本数不过来。有几次是他在和睡吧小组里求助的人讨论失眠,然后突如其来地,他感知到了一种熟悉的对于失眠的恐惧——或许只有资深失眠患者才能理解这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恐怖感——当晚他便无法睡着。CBTI也救不了他。
是在一次晨跑结束后,李明沿着山路走回家,天气很冷,但清晨的阳光打在他身上,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愉悦。“我突然决定不再研究如何解决失眠。”李明说。在那之后,他渐渐意识到,失眠就像感冒发烧一样,今年有,明年也会有。新冠疫情爆发之初,有一天他梦到了病毒,凌晨三点惊醒后就睡不着了。他起床喝了杯咖啡,如往常一样开启了这天的生活。
我问张斌,作为一名睡眠医生,你会不会也失眠过?
49岁的张斌在电话那头笑了,“你要说因为我是治疗失眠的医生我就不会失眠,那不可能。”“CBTI里面会讲,睡前三个小时不要做特别兴奋的事,但如果有朋友来了,大家聚一聚,晚上喝喝酒,唱唱K,这种事肯定会有的呀,我怎么可能8点钟就回家了。当天晚上我要是睡不好了,或者因为喝酒早醒了,这是必然的。我要是按正常规律作息,这开心的一天就没了。”
“我了解失眠,能正确地面对它,我不会为它恐惧,不至于失眠慢性化,这样就可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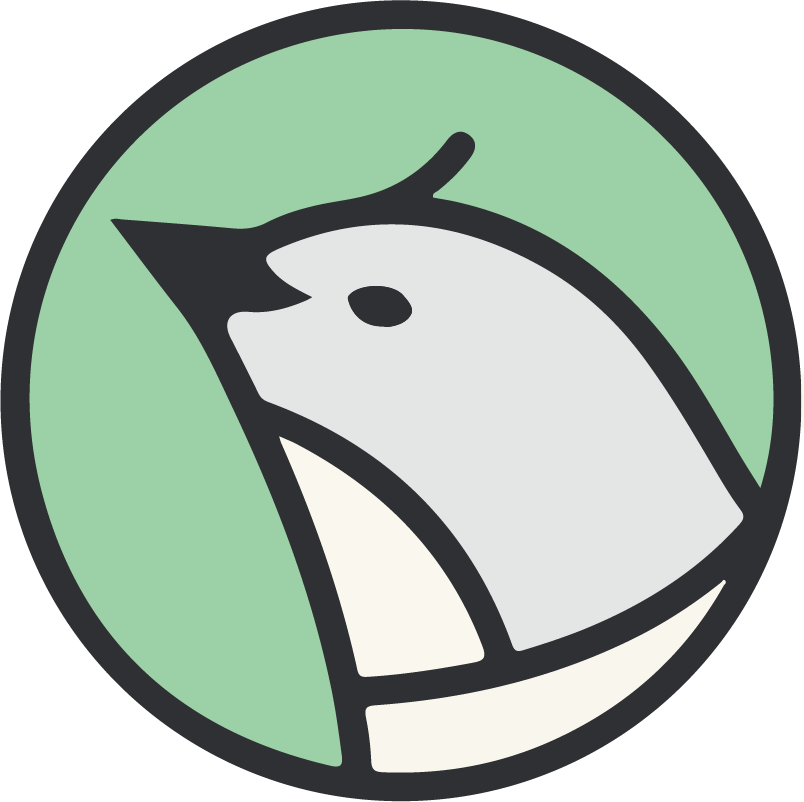 (来源:腾讯新闻)
(来源:腾讯新闻)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