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对战争的认识为何如此撕裂?


战争伦理和群体认同分歧
徐贲
人大复印:《伦理学》2003 年 10 期
原发期刊:《开放时代》2003 年第 04 期 第 4-16 页
摘要:本文讨论的是三种不同的关于战争理由、动机和目的、行为约束等等的伦理原则和主张。这三种战争伦理分别是自然法则观、政治现实主义和伊斯兰教。战争伦理与人们的群体认同密切相关。与本文述及的三种战争伦理相联系的分别是三种非常不同的群体观:人类、国家和信道者。
从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到2003年3月美国的“志愿联盟”军入侵伊拉克,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暴力、杀戮、恐怖和战争紧紧地扣住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对“9·11”事件,有各种谴责或欢呼的反应。在伊拉克战争迫近和到来的日子里,从联合国安理会到世界许多城市的大小街头,人们辩论战争的合理性,表达各种各样的反对或拥护的立场。这些分歧和争论都涉及了一系列与暴力和战争有关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现实的国际政治关系,更是涉及政治理念和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分歧和冲突。
在“9·11”之前,不同战争伦理的互动基本上是环绕着“正义”问题在自然法则观和政治现实主义这两种源自西方的现代伦理话语之间进行。“9·11”之后,以伊斯兰教某些极端“圣战”名义进行的恐怖主义使得人们在自然法则观和政治现实主义之外,也同时关注真正属于伊斯兰传统的战争伦理。对战争理论深有研究的政治学家华尔泽(Michael Walzer)坚持强调战争伦理与人们群体经验的密切联系。(注: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2d ed.(New York:Basic Books,1992),p.18.)
自然法则观、政治现实主义和伊斯兰传统的战争伦理间的差别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与这三种战争伦理相联系的是三种非常不同的群体观:人类、国家和信道者。这三种不同的群体观的性质和层次不相同,彼此之间存在着交接和部分重迭的可能。对于每个同时感受不止一种身份认同的人来说,他对某一特定战争的态度往往混杂着不止一种立场的道德和利益考量,不是简单的“反战”或“拥战”立场所能一言以蔽之的。从群体身份认同来厘清不同战争伦理之间的差别,将会有助于我们从表面的“战、和”之争深入到涉及基本原则分歧的理性讨论中去。

一、战争与战争暴力
自然法则观以人的自然普遍性为出发点,而政治现实主义则是以国家为出发点。以人的自然普遍性为出发点,要求道德之善完全与人的理性相一致。相比之下,以国家为出发点,则往往特别着重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强调“国家理性”,即从国家利益来看的合理性。在自然法则观那里,“正义”是和“善”联系在一起的,善以自身为目的,善没有自身之外的目的。(注:Germain Grisez,Joseph Boyle,and John Finnis,Practical Principles,Mo ral Truth,and Ultimate Ends, 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32(1987),103-108.)源自奥古斯汀(Augustine)的和平为善的观念正是以善的自我完足为核心的。人天生以群居为本,人的自然天性要求人与人之间和睦合作。共生共荣的实用性进而获得了普世戒律的表述:“爱你的邻人犹如爱你自己。”从古代的天理、圣戒到现代的人权,“人类相爱”的普世戒律可以引申为互不杀戮,互不仇恨,乃至互相宽容,互相尊重和权利平等。在自然法则观那里,非正义的战争是罪恶的,因为它伤害了自然的善。正义的战争不罪恶,是因为它有助于恢复遭受伤害的自然的善。人类行为选择应当从善的原则出发,在这一点上,自然法则观与和平主义既一致,又有区别。区别在于,和平主义把通过战争来争取和平看成是一种以恶求善的行为,并认为它本身先已背离了善的行为取向。
自然法则观并不试图定义什么是战争,而只是沿习罗马思想家西赛罗(Cicero)所谓的“战争为暴力争夺”的一般说法。(注:Joseph Boyle,Just War Thinking in Catholic Natural Law,in Terry N ardin,ed.,The Ethics of War and Peace,p.40.)自然法则观不追求普遍的战争定义,这是因为不同的战争有不同的理由、行为、目的和动机。不同的战争之间存在着极大的道义性差异,不宜混杂在同一范畴之内。自然法则观对具体战争的思考不是注重它的行为特征,而是注重它与自由意志的正当选择相关的目的、理由和行为约束。从正当性着眼,形似类同的战争其实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在自然法则观那里,有正当性和无正当性的战争不是同一种类行为的两个类别,它们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种类的行为。
政治现实主义者并不总是把战争视为一种有悖自然的非常状态,他们中有不少甚至接受霍布斯(T.Hobbes)把战争状态当作“自然状态”的看法。这里所说的战争并非指实际暴力冲突状态,而是指某一个“以战相争的意愿昭然若揭时段。”(注:Thomas Hobbes,Leviathan,ch.13.)这个定义强调的是敌意而非暴力。以这个定义来看,“冷战”是战争,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都处于战争之中,美伊之间在开战之前,就早已在进行战争了。政治现实主义对战争的更为具体的定义是“政治单元之间所进行的有组织的暴力。”(注: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105.)这个定义强调的是战争暴力的组织形式,战争与其它暴力形式的不同全在于其官方,而非私人的性质。
政治现实主义并不把和平等同为正义,因为如果和平等于正义,那么人们在能达成关于正义的共识前,必定无和平可言。政治现实主义认为,还不如将和平视为暂时没有组织性暴力,而不是已经有了正义。和平不但不等于正义,有时还会与正义相冲突,例如以和平维持暴政。但政治现实主义也认为,正义能为持久和平创造条件,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正义就有利于世界和平。政治现实主义有时主张为国家利益而战争,但也经常出于明智考量反对战争。反对战争是因为战争可能对国家造成伤害。政治现实主义不把明智考量等同为道德考量,因此它往往对战争的非道德性反而有更清醒的认识。
政治现实主义不相信自然法则观对“正义”战争的细分镂析。它认为,彻底的道德主义只能得出完全摈弃战争的结论。在这一点上,政治现实主义倒是与和平主义相当一致的。但是政治现实主义认为,和平主义一味摈弃战争,实为不明智之举,因为在世界上这么多不合道德的人群中,少数人又怎么能做到完全道德?(注:Machiavelli,The Prince,ch.15;ch.8.)还有的政治现实论者认为,和平主义者一味拒战,不仅不明智,而且不道德,他们不愿在“行动”和“绥靖”之间作必要的选择,结果往往是在世界面对人道灾难时助纣为虐。

自然法则观认为,人类应当确立一套普遍适用的伦理规则。人类的行为是否道德,应当以这些普遍性的伦理规则为衡量标准,不得以行为后果的成败为指归。自然法典所包括的道德戒律不等于实际存在的法律或惯例。自然法则所指的是普世性“天理”,即阿奎那(T.Aquinas)所说的人神一致的道德真理。“天理”不等于“王法”。普世的道德戒律话用于一切人类公共或私人生活的所有行为。政治现实论在是否可以确立普遍性道德戒律的问题上与自然法典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因此也往往被看作是一种道德怀疑论。事实上,政治现实论并不完全否定道德对公众生活的支配力,而是强调,这种支配力是很有限的。政治现实论强调后果决定手段。人的行为,尤其是公共人物(领袖、官员等等)的行为,其意义在后果而不在动机。政治现实论者不是完全不受道德的约束,但在他们认为在道德理性与“国家理性”有所不合的时候,道德理性应占据次要地位。在国家利益或现有秩序受到威胁的时候,战争理所当然可以成为正当手段。
自然法则观倾向于将战争视为一种罪恶,但也承认在某些情况下的战争是允许的。在自然法则观看来,战争本身无“正义”可言。只有为某种正义事业进行的战争,没有自身为正义的战争。为正义事业的战争,必须在一切防御和妥协手段都证明无效之后方能进行,否则不能说是为正义事业而进行。只有当自己受到攻击,不得已开战时,战争才算有了正义事业。即使如此,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不是杀戮对方。
政治现实论认为,战争有其积极的一面,并非全为罪恶。战争是一种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政策手段。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稳定、安全、发展)的需要而决定战争或不战争,使用或不使用暴力。政治现实论者不接受非暴力说。他们认为,暴力常常被滥用,但绝对排斥使用暴力则是迂腐愚蠢的。对于凶狠的对手,绥靖忍让是没有用的,仁慈换不来仁慈。在国际关系中幻想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府(如协调全球关系的联合国)只不过是营造空中楼阁而已,这样的世界政府并不能消除战争,它顶多只不过把国际战争变成另一种内战罢了。
与自然法则观和政治现实论相比,伊斯兰教在战争和战争暴力问题上的认识具有极鲜明的宗教色彩。它并不单纯以实际的武装冲突来界定战争。和犹太教及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并不把和平简单地等同为没有战争。没有战争可能只意味着停战,和平则并不仅仅是停战。和平(salam)只有以服从神的法典为条件方能实现,而神的法典则要求所有的人都承认神的权威。在伊斯兰教中,神就是阿拉,而和平只有在穆斯林群体中方能实现。穆斯林信道者们所享有的和平最终会因所有不信道者的贩依或降伏而遍泽人世。
与和平一样,战争也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实实在在的武力冲突,另一种是寓义的动乱。在阿拉伯语中,“战争”可以指战斗或厮杀(qital),也可以指动乱或争斗(harb)。“9·11”事件以后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说法是圣战(jihad)。这更是一个多义之词。它可以指努力、奋斗,也可以指自我动员以抗外侵,为伊斯兰而战,或者打击伊斯兰的仇敌,等等。不同的穆斯林往往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召唤不同的圣战。
在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派那里,呼吁圣战就是呼吁暴力。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义的理解。许多虔诚的穆斯林拒绝用暴力来解释圣战。他们主张宗教宽容,不相信暴力或强迫能产生真正的信仰。对他们来说,非暴力既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也是一种包含“正义”意识的美德。
伊斯兰学者哈西米(S.Hashmi)在他对伊斯兰战争与和平伦理的讨论中指出,尽管“圣战”和西方的“正义战争”分属不同的传统,但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远多于分歧之处”:“和正义战争一样,早期(伊斯兰)理论家设想圣战是为了尽量减少战争的理由,以此增加和平的可能。和正义战争一样,圣战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上的,那就是,社会与社会间的关系应当是和平的,应当免遭不断的、破坏性战争的涂炭。”哈西米对圣战的解释与其说是在描述现实情况,还不如说是在努力沟通伊斯兰战争观和世界性的现代化战争观之间的联系。哈西米承认,圣战的和平是一种在穆斯林“社会与社会间”的关系,至于这一关系如何扩展到现代意义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那就不能不是对伊斯兰传统思想本身的挑战了。(注:Sohail H.Hashmi,Interpreting the Islamic Ethics of War and Peace,in Terry Nardin,ed.,The Ethics of War and Pea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147.)

二、战争的理由
在战争的理由问题上,自然法则观和政治现实主义都重视战争的“正当”理由,它们的区别集中地体现在对这种理由与“自卫”或“自保”的关系上。自然法则观比政治现实主义更为强调要限制发动战争的可能。关于战争的正当理由,政治现实论强调的是“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而自然法则观强调的则是“自我卫护”(self-defense)。政治现实主义把战争视为一种国家工具,在用时便使用。对这工具要讲使用价值,对这工具的限制也同样要讲使用价值。接受或不接受对战争的限制,全看这限制对国家有没有用。一旦限制妨碍国家利益,当然不能让限制妨碍国家使用武力。国家使用武力可以是为了保全国家,也可以是为了保全国家权力。这使得国家在国际或国内有同样的动武原则。国家在面临它所见到的危害或威胁时,可以向敌方做“先发制人”的打击。先发制人是一种具有正当性的“自保”手段。
“自保”的合理性有一个程度问题,威胁越紧迫,越明确,先下手为强的做法越具合理性;越遥远,越模糊,这种做法就越具“侵略性”,越缺乏“正义性”。人们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有不同的解释,分歧往往并不在于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先发制人”,也不在于“9·11”以后的美国是否受到恐怖主义攻击的威胁。分歧往往在于,美国自己觉得受到的威胁是否确实与伊拉克有关系,或者这一关系到底直接到什么程度。有人试图把“9·11”攻击解释为一种阿拉伯“受压迫人民”打击美国霸权,武力“自保”或“自卫”的行为。这种解释是说不通的。自保与自卫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行为。十九个劫机者中有十五名是沙特人,但美国并没有攻击沙特或任何其它阿拉伯国家,更不要说杀害这些国家的平民。
自然法则观强调自卫,反对为自保“先发制人”。与政治现实主义的自保原则相比,自然法则观的自卫原则对战争理由的限制更严格。在自卫的原则下,不先动手是绝对的,只有先遭侵略或攻击,然后才进行的回击才能称作为自卫反击。而且,先攻击者遭反击,其对反击的反击仍为不义攻击的一部分,不能算作自卫。“自保”和“自卫”的区分对于我们理解和判断美国出兵伊拉克十分重要。“9·11”美国受攻击,以自卫的原则来看,美国对“基地”的一切回击皆属自卫,因此皆为“正义”。
美国在全世界追捕基地成员亦为正当行为,任何国家窝藏基地成员,美国都可视之为敌对势力(动武不动武则另外出于政治现实的考量)。如果伊拉克确与基地有联系,那么美国的行为可以说是“自卫”。迄今为止,伊拉克与基地的联系并无强力证明,自卫说当然也就无坚实根据。但美国入侵伊拉克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清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以此理由入侵,充其量只能是政治现实论的“自保”说,它的道义性是比不上自然法则观的“自卫”说的。即便如此,如果美国不能证明伊拉克确实拥有这样的武器,那么连“自保”说也难以成立。伊拉克是否拥有这样的武器呢?无论伊拉克政府的说谎纪录多么糟糕,在有真正证据之前,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美国以假设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和伊拉克与基地有关系,而在无确凿证据之前就进攻伊拉克,如果说这种做法在道德上站不住脚的话,那么一些反战人士在还无法证明伊拉克没有这些武器和与基地没有关系之前,就先断定美国的行为是“侵略”(既非自卫也非自保),在道理上也同样站不住脚。这是因为双方道理所必须依赖的“事实”尚无法知晓。美军入侵伊拉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清查这些武器,也只有这样才能对世界有所交代。最终证明能美国入侵伊拉克是否具有“自保”合理性的,只能是美国自己。这可以说是孤注一掷的做法。这是因为,即使美国真能找到证据,反对美国的人扔然可以说这是美国栽赃伊拉克的结果。
虽然自然法则观在“自卫”问题上比政治现实论严格,但它在为道义而出战的问题上却又往往比政治现实论放得开。自然法则论者在看到一国受到不义伤害时,他们比政治现实论者更愿意采取纠正伤害、惩治伤害者、捍卫普遍正义的立场。自然法则观往往坚持人权高于主权,不象政治现实论那么死死抱住国家主权不可侵犯、主权高于人权的说法。尽管自然法则观在原则上赞同惩治邪恶,但它并不总把战争看成是惩治邪恶的正当手段。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邪恶总是由一小撮人所造成,而战争则会殃及那个国家许多无辜国民。殃及无辜的危害会使武装惩治恶者(如伊拉克的萨达姆)的道义性大打折扣。
自然法则观认为,出战前的胜算越大,可预见的负面影响越小,出战越有道义性。美国在出战前不断强调速战速决的可能和精确武器不会造成重大平民伤亡,正是从自然法则观来寻找出战道义性。萨达姆政权越能将战争拖长,越能增加伊拉克平民伤亡,也就越能消除美国的道义性。自然法则观估计战争胜算和可能伤害,是出于对自己出战的“正义性”的考量,这和政治现实主义后果划不划算的得失考量是不一样的。

与政治现实论和自然法则观相比,伊斯兰教在出战理由问题上的立场就远没有那么明确和系统。曲洪在他对中东政治伊斯兰的研究中指出,伊斯兰经典上,“唯一讲得不大明确之处是举行圣战是否有前提条件的问题,即真主只‘容许’自卫性战斗,还是也可以‘主动出击’,随意以武力去征服那些拒绝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这两种说法都有多节(《古兰经》)经文作为依据,……因而争论也在所难免。”(注:曲洪:《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5页。)由于伊斯兰教传统中习惯将战争设想为信道者和不信道者间的冲突,它缺乏对国家间战争的讨论,它对战争正当理由的看法也是宗教性的。就其经文依据来看,自卫和自保都是正当理由,但这与现代国家关系意义的自保与自卫并不相同。战争理由的泛伊斯兰化使得穆斯林可以不分国界地去参加其它穆斯林的圣战。这种泛伊斯兰化可以从前伊拉克政府呼吁穆斯林人民赴伊参战的动员辞令中看出来。当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战争时,战争总是被描绘为不信道者对穆斯林或穆斯林世界的敌意行为。
在穆斯林内部发生的战争,按照伊斯兰教法理属于“受谴责”的行为。然而,一旦通过一项教令(Fatava),宣布对方为“叛教者”,对其宣战也就获得了道义的支持,成为“正义之师”。因此,圣战永远可以说是信道者与不信道者或叛教者斗争的事业。现代的穆斯林法理学家试图将伊斯兰传统法理与现代国家主权和国际关系结合起来。他们所强调的伊斯兰教自卫原则与自然法则观的自卫原则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例如“圣战”的自卫性包括争取民族解放和反抗外来军事侵略。
伊斯法理学与自然法则观的相似之处还表现在“人道干预”的问题上。例如伊朗革命领袖穆达哈里(A.M.Mutahhari)就说过,“最神圣的圣战和战争,其目的是保护人类和人权。”(注:Ayatollah Murtaza Mutahhari,Defense:The Essence of Jihad,in Mehdi Abedi and Gary Legenhausen,eds.,Jihad and Shahadat:Struggle and Martyrdom in Islam(Houston: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Islamic Studies,1986),p.105.)印度—巴基斯坦学者穆图蒂(M.A.Maududi)则认为,穆斯林应当在敌对势力威胁到其它穆斯林的人权时,义无反顾地投入圣战。当然,伊斯兰教所说的人权有其特殊的含义,例如,穆图蒂所说的“人权”指的是不被赶出家园,保存伊斯兰的社会秩序和维护其宗教生活。(注:转引自Sohail H.Hashmi,Interpreting the Islamic Ethics of War and Peace,p.161.)(注:Sohail H.Hashmi,Interpreting the Islamic Ethics of War and Peace,in Terry Nardin,ed.,The Ethics of War and Pea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147.)伊斯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相对淡薄,这反使得穆斯林在人道干预问题上不象非穆斯林那样在主权和人权哪个为先的问题上多有争论。
三、战争的目的与动机
战争离不开目的和动机。自然法则观强调必须区分战争目的(intentions)和战争动机(motives)。目的指的是企图通过战争达到的目标,动机指的是导致选择战争的情绪原因。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否正当,反对者或支持者一般都以他们自己所见的出兵目的为理由。反对者说美国的目的是掠夺石油,控制中东或世界;支持者说美国的目的是铲除专制政权,解放伊拉克人民。双方各执一辞,似乎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较为仔细的观察者则会发现,“9·11”以后的美国对自己的生存安危充满了危机感,而正是这种危机感和由此而生的强烈安全要求,成为美国“先发制人”战争的主要动机。目的和动机是有区别的,目的必定具有某种好的或者坏的道德意义(如“侵略”和“解放”),对目的的判断其实就是一种道德判断。动机则不然,许多动机出自人类共同的感情和心理因素,如恐惧、危机感、愤怒等等。动机本身往往并不具有道德意义,只有当动机影响了目的的形成,动机才具有道德意义,例如,“9·11”后美国人的不安全感和谋求自保意识,这些动机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因为它们是正常的。如果这些动机形成杀戮穆斯林的目的,那就是不道德的;如果这些动机形成的是自我保护的目的,那就不能说是不道德的。先发制人只是手段,它是否具有正当性,应放在战争理由而非战争目的中讨论。同样,一些穆斯林长期所经历的挫折感、压迫感和无力感可以是他们恐怖攻击的动机,这些动机同样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当这些动机形成自强自保的目的时,它们可以是道德的,但如果形成的是不分青红皂白杀戮一切美国人的目的,那它就是不道德的。
自然法则观为战争道德正当性确立的是一种多重限制原则,即战争的所有考量因素必须全都正当,战争才算具有道德正当性。这是一种很高的道德标准。战争考量可以是出自某种正当目的(如出兵打击侵略者),但如果另一些附带目的非属正当(如决策者出兵,是为了获得一己的政治利益),那么发动战争仍无正当性。同样,某战争有积极的后果(如推翻专制政权),但如果它出于非道德的目的(如掠夺它国财富),那么它仍然不是道德的战争。自然法则观认为,出于仇恨或者追求杀戮和残忍的战争是不道德的,战争的正义目的不是杀尽敌人,而是解除敌人的致害能力。因此,竞争中善待俘虏不是笼络人心的权宜手段,而是道义必致的行为。在自然法则观看来,单单主张和平或反对战争并没有不证自明的道德正常性。主张和平的道德正当性同样与其目的和动机有关。多重限制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和平主张。和平主张虽拥有某一道德目的(不杀戮),但如果其它目的或动机不道德(如为讨好某些选民,或出于仇恨某别国的狭隘民族主义),那和平主张仍然不具道德正当性。这样的和平主张在道德上是虚伪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因为它会自愿充当某些政治势力控制一般民众的伪道德工具,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在战争目的和动机问题上,政治现实论更为明确地把重点放在“动机”上。政治现实主义认为,人们很难能对别人的目的有清晰无误的了解。判断国与国之间敌意行为的目的是侵略还是自卫,那更要看判断者站在哪个立场上说话。再美好再道德的目的,有时也难免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战争要造成对方的破坏和伤害,这本身就可以看成是战争的目的,但达到这一目的的动机则可以不同。马基亚维尼就说过,君王残忍,但并不为残忍而残忍,君王有德无德,全视其动机而定。(注:Machiavelli,The Prince,ch.15;ch.8.)罗森泰(Joel Rosenthal)指出,许多美国的政治现实主义者都深受韦伯(Max Weber)的“责任伦理”说影响,因而把目的放在次于后果和动机的位置上。(注:Joel H.Rosenthal,Righteous Rights:Political Realism,Responsible Power,and the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Nuclear Age(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1),pp.42-46.)在韦伯那里,动机是“政治家”(不同于政客)伦理和政治考量间的桥梁。韦伯认为,政治家是那些为追求高尚理想,能够负责任而不惜弄脏手的人。(注:The Profession and Vocation of Politics,in Max Weber,Political Writings,ed.,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isty Press,1994),pp.309-369.)政治家勇于担负责任,哪怕为此必须承担道德罪责。政治现实主义者会认为,在对待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英国的布莱尔比法国的希拉克更象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当然,这是就民主制度中的政治家而言的。在民主制度中,政治家在缺乏民意支持的情况下,必须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勇于担负起领导的责任。但是如果后果不佳,他仍然必须引咎下台。
政治现实论者对那些老是自称道德目的良好,老是以不道德目的猜度别人行为的人,往往抱怀疑的态度,在政治现实论者看来,这些人是伪善的。在别人干预他人灾难时,这些人总会对干预者的动机百般挑剔。这看上去是出于道德良心,其实是为自己袖手旁观找借口。政治现实论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如干脆承认自我利益,而不要空谈道德。在国际事务中,本来就是各国照顾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现有的国际关系准则(如不干涉内政,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的作用不是为世界设计或维持什么崇高抽象的道德价值或原则,而是维持现有的国家间权力平衡。联合国内各国间辩论所用的正义辞藻其实不过是一种将本国利益道德化的圆滑外交辞令。尽管政治现实主义拒绝弹唱道德高调,但它有时候却也会采取一种类似道德主义的立场。政治现实主义在一些关键时刻会认“总得有人出面解决”或者两害取其轻的态度以求决断。美国出兵伊拉克可以说是一个例子。战争不好,这是尽人皆知的。但面对侯赛因政权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威胁,总得有人不惜“脏了手”加以干预。这种在别国息事宁人时独自担当的“责任”感,它其实是一种以善良动机为非善行为寻求合理性的道德主义。当然,和其它形式的道德主义一样,这种“责任”道德论也同样有可能沦为非善行为的借口。
在传统的伊斯兰圣战思想中,建立一统的伊斯兰帝国曾是圣战的至上目的。这个目的是在八世纪下半叶上升时期的哈里发国家霸权向外扩张中形成的。这一圣战思想将世界区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一个称作为“伊斯兰家园”(Dar-al-Islam),另一个则是“敌占领土”(Dar-al-Harb)。(注:曲洪:《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6页。)圣战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异教徒控制下的敌占领土转变为实施真主法律的伊斯兰家园。随着近代基督教在欧洲的崛起和伊斯兰东方的衰落,近世的伊斯兰解释不再强调扩张性圣战的正义性。十九世纪以后,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认为,传统的圣战思想已经过时,“穆斯林只有在遭到‘明确无误’的压迫的情况下,包括正当的宗教信仰遭到破坏,日常宗教活动无法举行时才能诉诸圣战。”他们中还有的在解读经、训原文和重新审视教法有关论述的基础上重新肯定了“自卫性圣战”的原则。他们坚持认为,和平共处是历史上伊斯兰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常态”,而战争属于“特殊情况”。这样的解释也许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它从现实出发,对传统观念重新加以解释的灵活态度还是可取的。这一解释符合现代国际关系准则,代表了主流趋势。此后,当代的一些穆斯林学者提出了“伊斯兰国际法”概念,并据此赋予传统的圣战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使圣战观念逐渐失去原有的宗教意义。(注:曲洪:《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8-59页。)但是,八十年代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断用极端主义观点解释圣战,使圣战成为不问对象、不分场合、不择手段的暴力恐怖。“9·11”事件便是这种暴力恐怖的高峰。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对这种恐怖主义的反击中,始终小心翼翼地避免将它和伊斯兰教直接联系起来,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正确”解释伊斯兰圣战,而且是为了争取广大的穆斯林,避免把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变为一场不同宗教或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
四、战争的行为限制
战争的行为是另一个直接影响战争正义性的方面。对于战争行为的正义性,自然法则观认为,必须用同样的道德法则来制约战争理由和战争行为。大到一个国家,小到每个士兵,谁都必须按照道德原则来从事战争。这些道德原则包括,不得为仇恨而战,不得为杀戮而战,不得以无辜平民的生命作为战争手段,应当尽量避免战争的伤害和破坏,应当区别对待军民和不杀害非战斗人员,等等。日内瓦公约条款便是规定这些战争行为限制的。自然法则观坚持认为,即使在难以严格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情况下,也仍然必须至少在道义上坚持这一区分。而那些显然以平民为目标的军事或暴力攻击,则绝对是必须谴责的恐怖主义行为。
政治现实主义也主张约束战争行为,但它是从后果决定论出发的,这和从普遍的仁慈道德原则出发不一样。政治现实主义提倡适度暴力,这是因为暴力行为的目的一旦达到,暴力便无须再继续下去。政治现实主义在对待非战斗人员的问题上也奉行后果决定论的明智原则:如果我不如此行事,则敌方亦不如此行事,结果对大家都没好处。政治现实主义在考量战争伤害时不讲究所谓的超然生命价值。它重视自己人的伤亡远甚于对方的伤亡,所以会采取一切军事手段,尽量降低己方伤亡。降低自我伤害是政治现实主义军事思想的首要目标。同样,政治现实主义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对方的利益重要。这些做法和它在国际事务中把国家利益放置于人类或世界利益之上是一致的。
伊斯兰教关于战争行为约束的先例可以追溯到古代部落间战争的“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包括,每一年中的某些时候不得进行战争,保护老幼妇儒的战士荣誉,战争仅为手段而非目的,等等。当然,这些规则的道义性又总是被归结为对《可兰经》和对先知有关行为(“真主启示”)的某种解释。既然战争的目的是创立伊斯兰世界秩序,而肆意杀戮和破坏并不能促使这一目的的实现,那么当然也就不能提倡了。当伊斯兰教用“真主启示”来规定战争行为约束时,它和自然法则观颇为相似。当它用手段和目的一致来看待战争行为约束时,它又与政治现实主义异曲同工。伊斯兰的战争伦理虽不能完全以自然法则观和政治现实论这两种现代模式来理解,但也并不完全无从与这两种模式发生联系。至于以圣战名义进行的、专以平民为攻击对象的恐怖行为,那倒反而与任何形式的伊斯兰教战争行为约束不相符合了。

自然法则的或政治现实的战争伦理不仅运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运用于国家之内的极端情况,如革命、反抗专制,民族独立等等。甚至在非暴力反抗的情况中(如良心反抗)也有与战争伦理有关的反抗伦理问题。自然法则观认为,人们在两种情况下可以正当反抗:第一,政府的权力是篡夺的,不合法的;第二,合法的政府有了极不正义的行为。当人民以武力反抗政府权力的时候,他们必须接受与国与国交战时同样的行为约束。自然法则观特别强调通过正当程序实行惩罚。正如士兵不得挟私报复一样,公民们不得对罪犯进行私自报复,不得私自惩罚不义的统治者。人们可以有条件地允许不义统治者继续统治,但却决不能容忍篡政者。因为即使为“正义”目的去篡夺政权,那也是一种不义行为。自然法则观允许暴力革命,也支持对政府恶法和恶令的象征性抵抗(如公民不合作)。只要反抗依据的是普遍的道义法则,用暴力镇压反抗就是不义的。在“天理”和“王法”发生冲突时,自然法则观站在“天理”这一边。
政治现实论在公民反抗正当性问题上则表现出相当的暧昧性。政治现实主义在国家的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立场。第一种是把国家本身视为具有内在本质价值的实体,任何现有的国家政权,无论其性质如何,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都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连批评它也是干涉主权国家内部事务。另一种立场则把国家仅仅当作实现群体价值目标的工具,只有当国家能帮助达到这一目标时,它才有价值可言。从实质论和结果论这两种不同的国家观念可以得出对公民反抗合理性的两种不同解释。从实质论来看,国家镇压异见,维护稳定和政府权威是天经地义的。从结果论来看,国家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紧急关头,才能镇压异己。保存国家是为了使国家能为公民服务,国家主权的基础是主权在民,背离公民意愿的国家是不值得保存的。
与自然法则观和政治现实主义相比,伊斯兰教则包含着一种更为质朴的反抗伦理。早期圣战思想以经文启示为根本依据,包括了普通人自卫反抗的权利(《可兰经》22:39)。根据这一经典,遭到进攻的穆斯林是“被压迫者”,他们自动从“万能的真主”那里得到了“反抗的许可”。这种朴素的反抗伦理至今仍表现在无数穆斯林对他们心目中“美国”这个压迫者的反抗意识之中。但是,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直接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当今世界结构中,这种抽象的外国压迫其实往往是某些国家中统治者向外转移被压迫者仇恨所制造的假象。
不管美国的中东政策有多少错误,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回避的,那就是,在许多穆斯林国家中,专制体制、不民主、秘密警察恐怖统治,这些才是广大民众生活在严重的贫困、社会不公正和政治腐败之中的根本原因。而且,这些也是他们“被压迫”最实质的内容。把中东地区广大穆斯林所遭受的压迫感和屈辱感统统归咎为“以色列恶魔”和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勾结,这虽然可以起到相当大的民众煽情效果,但却无助于真正改善那个地区人民的实际生存环境。在当前的国际世界中,以某一群体与其它群体的差异来解释普通人的全部屈辱性的生存经验,这是原教旨主义宗教或极端民族主义得以存在的广泛基础。这两种意识形态是当前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它们之所以危险,并不是因为它们有能力征服世界,而是因为它们既非理性又没有能力去征服世界。正因为如此,它们的狂热信徒才会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毁灭这个世界,甚至包括他们自己。
人们对待战争或和平的态度总是在不同程度上结合了道德原则和实际利益的考量。无论是道德原则还是利益意识,往往都决定与人们所直接认同的那个或那种群体。这个群体可以象“人类”那样普遍,可以象“国家”那样疆域分明,也可以象“穆斯林”(或“某民族”)那样植根于某种传统的“我们”。华尔泽曾经指出,不同的群体观相差悬殊,彼此间很难存在共同性的“浓厚”价值观,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设法达成一些“稀薄”价值的共识。浓厚的价值是积极地“提倡”,稀薄价值则是消极地“禁止”,前者注重于人们普遍的责任,后者只着眼于大家共同的祸害。
从根本上说,战争伦理只是一种稀薄的价值,一种关心禁止甚于关心提倡的伦理。战争伦理关心的首先是如何在战争和不战争、约束和不约束之间进行选择,而不是如何建立一种正义的国际法制秩序,以使战争永远消除。(注:Michael Walzer,Interpretation and Social Critici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Thick and Thin: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Notre Dame,I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4.)这两种目的虽然有根本的区别,但却没有本质的矛盾。要想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高程度的道德成就,恐怕还得从低程度的道德实践做起才行。


最近微信改版打乱发布时间
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
将“海派评论”设为星标🌟
保持联系,一起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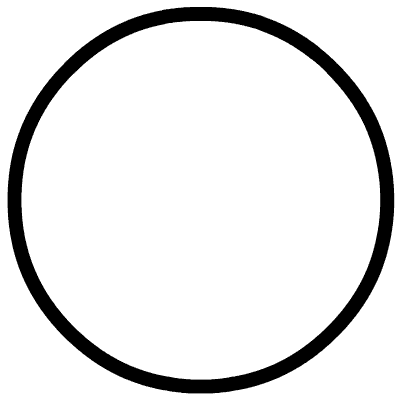
关键词
世界
就是
国家
战争伦理
利益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