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涛|历史记忆


作者|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全球史、中外关系史、德国哲学史及中国学术史的研究。
回忆
近年来,口述史(oral history)在中国铺天盖地袭来,各个行当、各个专业的人都在做口述史。记忆与历史(过去)的关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人经历了事件,他的记忆就一定可靠吗?即便是让当事人感受惨痛的经验,如果让他感到讨厌的话,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也会选择性记忆,意即选择性地忘记。
这样事后想起来,有时居然发现是一种美好的回忆。人在潜意识中会将回忆加工成自己愿意接受的形式,当时的痛苦自然就从记忆中消失了很多。
以前学德语的时候,学到法国作家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的一句话:“Die Erinnerungen verschönern das Leben, aber das Vergessen allein macht es erträglich.”意思是说,回忆美化了生活,而遗忘使得生活能够忍受。这所讲的是人记忆的选择性,不一定是有意为之,也是潜意识的选择。
钱锺书在1980年年底为杨绛的《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中写道:“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杨绛要将干校的故事写得诙谐、滑稽的缘故,不然人是没有办法忍受的。
最近读东野圭吾的《平行世界·爱情故事》,其中的故事便是涉及记忆修改的主题。
《思想小品》李雪涛 著
新民说 2021年9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裹上樟脑的记忆
有关记忆,相较于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orth,1770—1850)所认为的记忆可以像保存木乃伊一样封存的想法,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的说法更有意思:
There’s no memory you can wrap in camphor.
But the moths will get in.
中文的意思是:没有记忆可以裹上樟脑,免受蠹虫的侵害。
我觉得后者特别精彩,因为所谓永恒的记忆是不存在的。
酷刑
世界各国都有具有折磨性和羞辱性的刑罚,在中国一直到清代依然有所谓的“十大酷刑”(当然不止十种),这包括:剥皮、腰斩、车裂、俱五刑、凌迟、缢首、烹煮、宫刑、刖 刑、插针、活埋、鸩毒、棍刑、锯割、断椎、灌铅、弹琵琶、抽肠、骑木驴等。之前读到明末抗清将领张煌言(1620—1664)的四句诗:“等鸿毛于一掷兮,何难谈笑而委形。忆唐臣之啮齿兮,视鼎镬其犹冰。”(《放歌·武林狱室书壁》)即 便是将生命看作鸿毛,也很难做到从容笑谈地就义吧!“鼎镬之刑”是将活人放在鼎沸的油锅中炸。在古罗马此类的酷刑被称作 summa supplicia,包括将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将被判处死刑的人扔给野兽,将活人烧死,将活人装入皮袋沉入水底,等等。尽管这些方式同样是反人性的,但古罗马人在酷刑方面好像远不如中国人那么有想象力。

泛亲属化的称谓
在德国生活几年后,回到国内,感到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泛亲属化的称谓。以前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毛爷爷”“周爷爷”“雷锋叔叔”等的称谓,尽管这些人跟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亲属上的关系。在单位里,特别是在年轻同事的孩子面前,我的辈分不断攀升:从以前的大哥哥,到叔叔,现在已经成为爷爷了,我只是觉得很别扭。有一天顾彬教授也在,一位同事让她女儿叫顾彬“太爷爷”,顾彬没有什么反应,可能他会觉得中国人莫名其妙。我妻子的德国同事,也开玩笑说,她来中国后,从外国姐姐,变成了外国阿姨,将来必定会成为外国奶奶的。
1949 年以后,整个中国的称谓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所有的人不论男女都称呼“同志”;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下海”成风有一段又都称“老板”;也有一段大家都互称“师傅”。现在电视节目最常用的称呼是“老师”,好像一夜之间,神州大地全都是人民教师。正常的“先生”“女士”的称谓用 起来好像很别扭,在中国就是实行不起来。
而在民间,我们依然使用着“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这些亲属化的称谓,连我的博士生们也按照年龄,互称“师姐”“师兄”。实际上看似亲切的泛亲属关系是最为复杂的,以我这样的智商,既弄不清楚各种亲属的关系,也真的不太懂得与这些“叔叔”“阿姨”的相处之道。
泛亲属化的称谓在中国自有其历史传统,早在先秦的时候,中国人就开始称呼地方官为“父母官”了。孟子说 :“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这在一个父权社会中是很普遍的。其实拉丁文中的 Papa(爸爸、父亲)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对教皇的称谓。
礼仪之邦
每次坐地铁,都能听到车厢里刺耳的广播,说我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腊碧士教授夫妇有一年“十一”的时候来北京,有一天游完故宫后我们一起吃饭。席间,他小心翼翼地对我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对别人的存在予以漠视的人。我当然理解他所说的这一点,因为在欧洲有时也会跟其他人发生身体的接触,对方总会致歉说声“对不起”,他们习惯了这种小心翼翼表达的对别人的尊重,也愿意接受这样的致歉。其实这是一个根本的教养问题,与是否曾经是“礼仪之邦”,好像关系并不大。
我在其他语言的网络上很少看到中文网站上这么多的语言暴力,粗俗的语言乃至谩骂,充斥着一些网络,而有一些不优雅的说法反而被认为是“原生态”“真实”的说法。每次我给学生上的第一堂课,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是要教他们如何跟人打交道,如何写邮件。

柏杨论德、日与中国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复兴”,柏杨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当然也跟中国做了比较:
……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国家,可 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好像一个三头六臂的好汉,咚的一声被打晕在地,等悠悠苏 醒,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仍是一条好汉。而我们这个三期肺病的中国,一时站到世 界舞台上,不 可一世,可是被冷风一吹,当场就连打三个伟大的喷嚏,流出伟大的鼻 涕,有人劝我们吃阿司匹林,我们就说他思想偏激、动摇国本, 结果一个倒栽葱, 两 个人都架不起。
柏杨所谓“一等国民”和“三期肺病”的说法,其实是说明整个民族的受教育程度。
国耻与现代性
鸦片战争真正使得东亚的日本、中国这样传统的农业国进入了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这个过程尽管对日本来讲并不容易,但日本人却将这种国耻化作了对现代性精神的一种追求。从 17 世纪耶稣会时期开始对南蛮文化的摄取,到19世纪早期基于“兰学”的发展,日本对于欧洲科学的态度变得更加开放。
到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于欧美文化的摄取可以说是更加全面,并且从历史上来看,日本并没有像中国在18 世纪晚期由于耶稣会知识输入的停止而中断了与西方的关系。

至今你在日本的很多城市还可以看到一些日本人和洋人的塑像,日本人之所以纪念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曾经为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做出过贡献。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历史观。
对话与讨论伦理
1989 年,捷克剧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1936—2011)等人在布拉格成立了“公社论坛”,制定了八项的《对话守则》:
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
不做人身攻击。
保持主题。
辩论时要用证据。
不要坚持错误而不改。
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
对话要有记录。
尽量理解对方。
只有经历了之前捷克斯洛伐克铁幕下生活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哈维尔的这八项对话守则的内涵。

20 世纪德国的两次焚书
每次到法兰克福,我都会来到罗马人广场的中央,看一眼在那里镶嵌在地上的一个纪念纳粹时期焚书的圆形纪念牌。1933年5月10日,受纳粹思想鼓动的青年学生,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的歌曲,高举着火炬,将数万本的所谓宣传“非德意志”思想的著作焚毁。这一“反非德意志精神运动”(Aktion wider den undeutschen Geist)在柏林的倍倍尔广场(Bebelplatz)规模更为巨大。当年的5月9日,帝国内务部长弗里克(Wilhelm Frick,1877—1946)在向各州宣传部长的演讲中宣称:
要培养有政治觉悟的人,他们的全部思想和行为都应当根植于服务并献身人民大众,他们应当与国家的历史与命运完整地结合在一起,永不分离。
历史却告诉我们,纳粹的意识形态本身是一场人类的灾难。这一愚昧的行为,在六八级的学生运动中,再次出现。1968年,因学生运动领袖杜契克(Rudi Dutschke,1940—1979)在反越游行中遭枪击,愤怒的学生冲上了街头,包围了出版业巨头施普林格出版社,焚烧了满载图书报纸的火车,因为这家出版社旗下的《图片报》(Bildzeitung)曾公开指责过这位学生领袖。
张燧在《千百年眼》(1614)中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的做法可谓疾首蹙额 :“以祖龙烈焰,煨烬之中,仅存如线。”(《千百年眼》卷一《上古文籍》)焚书的做法不仅烧毁了大量的古代书籍,也开启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禁锢和文字狱的先河。书籍承载着长久以来人类的文化,焚书意味着对文化的破坏,这当然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
—End—
本文选编自《思想小品》,推荐购买原书进阶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包括图书名与公号名)。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最近微信改版打乱发布时间
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
将“海派评论”设为星标🌟
保持联系,一起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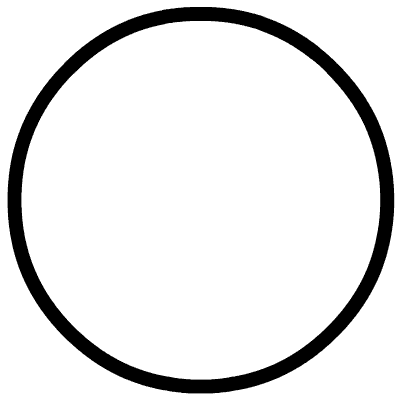
关键词
历史
德国
爷爷
日本
在中国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