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晃:谈父母情是个难受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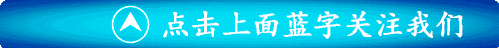
【留美学子】第2384期
7年国际视角精选文摘
教育·人文·名师·媒体生态圈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留美学子】导语
2012年09月洪晃父亲洪君彦去世,当天文化名人洪晃在其微博中写道:“爸爸走好”,并在后面贴上一颗点燃的小蜡烛的图像。

家庭教育中,人们常提到“原生家庭”给后代带来的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
阿德勒留下令千万家庭反省的格言“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Fortunate people have their whole life protected and healed by their childhood, unfortunate people have to have their whole life protected and healing from their childhood. - Alfred Adler (February 7, 1870 - May 28, 1937)
其实洪晃的家庭很复杂,可以说,她从小没有像其他孩子能够获得的原本许多正常家庭里父母给予的爱,然而,从她的言谈话语、她笔下的人生百态却呈现着开朗、诙谐、洒脱!这是为什么呢?
本期内容,在洪晃的叙述中,有一段父亲给她一句非常重要的留言,使她在15岁时,就可以释怀了她人生中许多缺失。

我曾经向他抱怨,认为父母离婚让我这辈子不能愉快,他开导我说:“其实你自己活好了就行了,干嘛老想父母的事儿。”那时候我才15岁,别人都说这句话好不负责任,我倒是觉得,这句话救了我,以后我真的活的挺好的。所以我还是挺高兴继承我爸的逻辑,虽然毛病多了点,但是总而言之还是活得挺自在的。

洪晃:中国互动媒体集团CEO,《世界都市iLOOK》杂志主编兼出版人。12岁时被送往纽约学习,1984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州瓦瑟学院。曾经做过咨询、有色金属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工作。专栏作家,出版自传《我的非正常生活》和杂文集《无目的的美好生活》、《廉价哲学》。
我的母亲章含之
在我心目中,妈妈是个悲剧性人物,但是,她是史诗规模、莎士比亚级别的悲剧人物。

妈妈一生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她的生母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尾声,也就是她已经40多岁的时候,才和她有正式而且相对平凡的接触的。妈妈进章家门的时候不到一岁,她成为外公第二位太太——溪夫人的女儿。
溪夫人就是我的外婆,妈妈从小没有得到什么母爱。溪夫人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姨太太,每天打麻将,在外面吃饭,而妈妈几乎是几个江北的阿姨带大的,我想妈妈小时候过的是不缺吃、不缺穿,只缺爱的生活。记得妈妈说,她小时候信天主教,经常一个人在教堂里面发呆。

外公和溪夫人的感情并不好,抗战的时候,就把溪夫人和妈妈都留在上海,并没有带去重庆。这使溪夫人很不高兴,而且居然在上海认了一个“干儿子”,老上海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妈妈说,外婆那时候就对她不管不顾了,每天让这个“干儿子”骑自行车去接妈妈,妈妈就坐着“二等”回家。有一回,回家的路上下大雨,这个“干儿子”骑得特别猛,居然把妈妈甩在马路上了。但是他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个7岁的孩子已经摔在马路中间,只是到家以后才发现后面没有人了。妈妈说,她只好坐在马路牙子上挨雨淋,等了一个多钟头才被领回家。

妈妈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她的生母通过我的父亲,又找到她。据我父亲告诉我,那是因为他认识我的亲生舅舅,也就是妈妈同母异父的哥哥。当时妈妈非常激动,这似乎解释了她小时候所有的委屈孤独和不幸。当时,妈妈甚至想脱离章家,回到自己生母身边。
这事情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而那时候的革命教育也迫使妈妈认为,她的生母放弃她肯定是因为太穷,而穷人都是好人。反而,像章家这种封建家庭一定是反动的,她如果投奔她的生母,那简直就是革命的一步。
而就在她下决心要走出章家门的时候,妈妈被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的秘书找去谈话。他告诉妈妈,章士钊是共产党统战的对象,党不希望在他刚刚回北京几年内,由于共产党的政治教育,丢了自己的女儿。所以,底线就是党需要妈妈待在章家,好好当女儿。
在那个年代,这句话可能比什么“养育之恩”之类的人之常情更能够说服一个二十几岁的女青年。也就这样,妈妈留在了章家。但是从那以后,她一直偷偷跟自己的生母保持联系,每次去上海都去探望她,她一直寄希望于这个生母能够给她一生渴望的母爱。

由于妈妈是这么长大的,所以她不知道如何向我交代这么复杂的家庭背景。更何况,溪夫人,我的外婆酷爱我,对我简直是好得不能再好。外公章士钊80多岁终于有了个第三代,对其更是百依百顺。我从小跟我外公、外婆在四合院里长大,是他们在一个动荡的年岁中给了我一个无忧无虑、快乐的童年。妈妈知道我和外公、外婆感情深厚,这就让她更加难以启齿告诉我家里这些复杂的背景。1976年夏天,我从美国回来过暑假,就在唐山大地震的头一天,妈妈跟我说:“明天去火车站接你的外婆。”
我以为是我外公的第三位夫人从香港回来了,“殷婆婆回来了吗?”我问。
“不是的,”妈妈说,“明天早上你去之前我再给你解释。”
结果,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妈妈和乔冠华当然连夜全去了外交部。早上,妈妈来了电话,说来不及跟我解释了,但是八点半赶到北京站,在右手的大钟下面会有一男一女,那是我的表哥和表妹,男的叫瓶瓶,女的叫罐罐。他们是去接他们的奶奶,也就是我的外婆。然后,不容我再问任何问题,妈妈就把电话挂了。

那年我15岁,在纽约已经住了3年,完全是个美国孩子了。从我的视角来看,1976年的中国本来就是一部超现实电影,所有一切都不可能是真实的——这个国家就是奥维尔的《1884》。所以,地震震出来个莫名其妙的“外婆”和两个叫瓶瓶罐罐的表哥表妹似乎非常正常。
我对妈妈的生母——我的亲外婆的态度跟妈妈正好相反。我记得这个有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的老太太是个非常势利、不真诚而且话实在太多的老太太。在来的第一天晚上,她就在史家胡同的饭桌上热泪盈眶地对我说“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让我们一家团圆。”
我当时觉得这是变相地在骂抚养我长大的外公外婆,而51号是他们的家,所以我跟妈妈大吵了一架。结果证明我是对的,在乔冠华去世之后,妈妈最需要亲人的时候,这个老太太选择了跟已经被她遗弃过一次的女儿划清界限。
妈妈是个传统的女人,她太把男人当回事,我总觉得她思想中有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情结。有这种思想的女人,最后总是要找一个值得她彻底自我牺牲的男人。妈妈的一生中,这个人就是乔冠华。

他们在有生之年没过什么太多的好日子,光隔离审查就有两年。而乔冠华走了以后,妈妈守了25年寡。在这25年中,妈妈写了4本书,每本书的主角儿都是乔冠华。在公众眼里,这是她的美德,是一个美丽的中国女子应该做的。在我眼里,这就是她悲壮的地方,也是她为什么是悲剧人物的原因。
我很想她,很想再有一次机会让我改变她的悲剧命运,让我再有一个机会让她最后的25年过得更加开心一些。可惜,我不会再有这个机会,这将是我终身的遗憾。

我的父亲洪君彦
我爸爸是个乐天派,就是在文革最艰苦的时候,他都能从生活中找到乐子。记得有一年秋天,他从江西干校回到北京,晒得特别黑,我们大家都心疼他这个旧日的上海公子怎么成了农民,而他却高兴地操着上海口音的英文,装成巴基斯坦人,跑到外宾供应站去给我们买了好多大虾吃!还笑呵呵地说:“要不是晒这么黑,谁会信我是巴基斯坦人!”

我小时候爱吃山楂片,直到现在我爸看见我还送我山楂片。我现在不爱吃,觉得跟纸壳贝儿似的。但小时候实在没什么零食,就觉得山楂片是最好吃的东西,他到现在还是转不过弯。在有了巧克力冰激凌奶油蛋糕的时代,山楂片实在是不好吃,但在他脑子里就不是这样,每次见到我就跟我说,给你带山楂片了!
我妈妈说,我身上的坏毛病都是从我爸爸身上继承的,也的确是,我爸聪明不用功,我也是;我爸好吃,好抽烟,不注意身体,我也那样;我爸结过三次婚,我也整整三次,还在比他小得多的情况下,就把这三次都结完了。
我爸爸退休前是在北京大学教经济的,据他的学生说,他能把经济讲得生龙活虎,据他的同事说,他就是学术文章不好好写,所以别人都当头版头条的经济学家了,而他老人家却退休了。
我小时候记得我爸爸教我骑自行车,带我去圆明园。还有就是他跟我妈妈离婚那一天,他把我送到史家胡同,就在11路车站(现在的111路)跟我说,我跟你妈离婚了,所以今天不回史家胡同了,你今天自己回去吧!我刚要过马路的时候,他说等会儿,我带你过去。他带我过完马路,看着我回去,然后再坐公交车原路回北大。这时候难受真的没法说,你就觉得这个人就这么没了。

他和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怪的恐惧,我怕我爸爸会死。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爸如果没有呼声,我就忍不住要把手放在他的鼻子上方,看看他是不是还在呼吸。我和我爸爸的亲情是在自行车上培养的。
我那时候每个星期日的傍晚都要从史家胡同赶回外语附校,我爸爸总是陪我走,我坐车,他骑车,每当我坐的公共汽车赶上他的时候,他都要狂蹬一阵子,逗得我哈哈大笑。我那时候坐11路,到动物园倒车,再坐332在魏公村下车,下车以后要走一段路,每次我爸爸都用自行车带我进去。我坐着他的“二等”和他聊天,觉得我爸爸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人。

WG时期,我爸和我妈离婚以后交过一个女朋友,两个人吹了之后她去领导那里告我爸,那时候想整人就提“作风问题”。一整一个准儿,再加上我们家老爷子又是离过婚的人。
领导找我爸爸谈话说:“老洪啊,你怎么犯这种错误呢?本来都要让你复课教学生啦。”我爸闷头不说话。
领导又说:“老洪啊,干校的苦你还没受够吗?你要是再受一次处分那可就又得回干校了。”我爸听了有点动心了,大概干校挺不是待的地方,于是笑眯眯地对领导说:“那我怎么办呢?”
领导看我爸有悔改的意思,就比较高兴,建议说:“老洪啊,这么着吧,我和党委再说一说,你就跟这个女的结婚吧,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啦。”我爸一听,连想都没想,就说:“那就算了吧,我还是回干校吧。
领导没有见过如此不知好歹的,气愤地问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不顾全大局的决定,我爸理直气壮地解释说:“你想想,她没结婚就这么整我,那要是结婚了,还得了!”
就这么着,我爸又回干校放了几年鸭子,前一阵子,我爸爸住进了朝阳医院换肾,他乐呵呵的,开刀的前一天晚上居然和我后妈一起下馆子吃饭,然后又去看老朋友,气得我骂他们两个人怎么都这么不懂事,然后把他们赶回了医院。
开刀的当天我们都坐在医院里等候他的体格检查结果,手术大夫来了,身后跟着心脏科主任,他们说我爸的心脏不好,做手术有一定的风险,要他再考虑一下,然后又把我和我后妈叫到走廊里,仔细地解释了一遍。
我后妈立刻眼泪汪汪,不知所措地回到房间问我父亲是否坚持做手术,我爸斩钉截铁地说: “做,做,做,要不然什么好吃的都不能吃。”我告诉护士我爸爸坚持换肾的原因,她们都笑了,说:“这是什么逻辑。”
我爸爸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他算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活得比较自在的一个人。我曾经向他抱怨,认为父母离婚让我这辈子不能愉快,他开导我说:“其实你自己活好了就行了,干嘛老想父母的事儿。”那时候我才15岁,别人都说这句话好不负责任,我倒是觉得,这句话救了我,以后我真的活的挺好的。
所以我还是挺高兴继承我爸的逻辑,虽然毛病多了点,但是总而言之还是活得挺自在的。
父母、亲情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难受的话题,我能留下的记忆就那么一点,不想再被人拿走了。



【留美学子】近期发表
说出丈夫那段经历 需要我的勇气
斯坦福妈妈: 孩子成长让父母发现了什么
我女儿是这样考入藤校哥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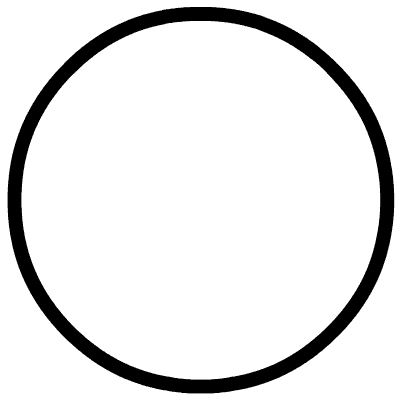
关键词
时候
外婆
洪晃
外公
我爸爸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