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9·11】20年前的今天


纽约 911 Memorial Building (照片来自网络)
(一)
20年前的今天,仅仅一个多小时之内,接连发生在纽约曼哈顿、宾州田野和首都华盛顿郊区的前所未有的事件,让9/11这个数字变成了史无前例的特有专用名词。
深沉的事件震撼了世界,惊炸了美国,更象是电击一样地刺在了每个纽约人的心尖上。
每年的这一天,总会有各种方式的纪念活动,也有各类的媒体报道。这固然令人欣慰 —— 过去的事情毕竟没有被遗忘;但有时我又疑虑这样的追忆是不是已故人所希望的。
每到这个时候,被贴有 “狂傲” 标签的纽约人,显得格外地谦卑寂静,他们更愿意把思念视为个人的隐私,默默地缅怀那个永不消逝的记忆。普通百姓常以细微平凡的实际行动,在内心深处祷告祝愿 (其实,从来没有停过),取代那些累赘繁琐、行规蹈距的庸常方式。因为,每个从9/11走过来的人,心灵深处都有着各不相同的触动和感受,语言文字是难以表达出来的,新闻媒体更是不可能捕捉到。
描述9/11的文字成千成万,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似乎更加积极主动地去详载传播。
曾经几次想到要记录下那个从记忆里抹不掉的日子和事件。可是,总有顾忌之心,不愿意正视面对过去的往事;也担心记述中出现的遗漏瑕疵,会对不起那些已过去的人,有失尊严和尊重。先生更是坚决地反对并阻止,认为太多的炒作 (他不叫写作) 是有意地利用事件做噱头,是对人与事的不公不尊不敬,甚至是亵渎。自然不允许我“随波逐流”。于是,我放弃了笔记的念头。
20年后,尽管不愿意重新回味那一天的经历,可是,发生的事却仍然历历在目,只是有的微小细节开始变得朦胧。这多少引起些担忧和紧张,觉得在更多的模糊来临之前,应该有一个记录,只是限于自己的经验而已。

(二)
那天早上,我和以往一样,离家上班,走路15-20分钟,就可以到办公室。走到第4大道和第10街或者第12街 (这就是上面所担心的模糊细节)之间交叉的地方,一道震耳欲聋的声响突然从天而降,一架客机低空快速飞行,感觉就像是从头上冲过。虽然马上就消逝了,还是不大不小地吓了一跳。在摩天楼林立的曼哈顿,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低空飞过的飞行物,连它的颜色和logo都看得一清二楚,机体硕大无朋。那大概是早晨8点40分左右。
没几分钟,就听见低闷沉重撞击的声音,好像是发生在相距比较远的下城。随后一片刺耳的警笛声顿时响起,似乎都是从曼哈顿的West Side (西边) 传过来的。这时候,已经走到更南边,接近Astor Place和Broadway (百老汇) 交界的地方。
虽然是9点正式上班,但是大家在时间上还是比较灵活的。5点下班后,不少人还会留下来继续工作。平常我们的Receptionist(前台接待员)8点半就到了,打开主门。可是那天9点左右,我是第一个到达办公室的,开了主门。与平日一样,往里走,进到我的窗户面对着Washington Square Park (华盛顿广场公园) 的房间,打开电脑。在等它启动时,从窗户望到公园,外面有点与往日不太一样,好多人站在公园正中间的喷泉的北边,举头朝南,也就是往下城的方向注视。可以看出来,大部分人不是游客,更像是和我一样的在单位各部门工作的职工和过路的行人。
更反常的是,这时办公室里还只是我一个人。一般这个时间,大家差不多都到齐了。挺奇怪的!站起来后,准备下楼,到公园那边看看。正要关主门的时候,一位保加利亚或者是匈牙利 (又一个模糊的记忆) 的年轻女士进来询问问题。给她解答时,Receptionist边擦眼泪,边低头走进了办公室。客人问我receptionist为什么哭,我觉得她有些多管闲事,不想搭理她,但是最后还是用一句话打发了她:“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她离开后,receptionist试着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公园的人在瞧什么。不知道是因为她哭时说的话语不清晰,还是我的听力出了故障,不能完全领会她的意思。赶紧下楼,跑到了公园。那时已经9点多了。
华盛顿公园是观赏坐落在下城金融区、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塔”的绝佳地点之一。高耸的建筑隔着3英里多长的街道,俯视着公园的正中心,在遥相呼应的距离之间,没有任何遮眼的障碍物。

纽约 911 Memorial Building (照片来自网络)
都说眼见为实。可是那一瞬间,只觉得眼睛有了毛病,进入视野的景物,就是无法转到脑子里去过滤处理。一座双子塔上有一个巨大无比的黑洞,另一座在冒烟。旁边有人在说,飞机攻击了世贸中心。那一刻,才意识到,早些时候,在路上撞见的那架低行吓人的飞机,是冲着双子塔而去。
短短的时间之内,一座塔楼像电影里的慢镜头那样倒塌下来。哭声、惊叫声和各种各样的声音一起喷射出来。听起来扎心的难受。不愿意看到另一座塔楼的命运,转身离开了公园。
惊慌失措之中,又回到了办公室。人还是不全,老板倒是坐在他的屋里。给我解释了他所知道的仅有的信息。这时,轰轰的军用飞机迅速飞过,振聋发聩,然后就没有停过。那时刻,本能地就可以听辨出来民用机和战机的声响。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记得对着老板突然稀里糊涂地冒出一句:“Where are the FBI and CIA?” (FBI和CIA在哪儿呢?) 此时,部门的一位高管小跑进来,要大家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她又是上下左右地在楼里转,要求别的办公室的职工也回去上班。
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马上跑过去接。是未婚夫打来的。他从健身房里出来,跑到我的办公室附近,拨打路边的付费电话。他说已打了无数遍,我都不在,急死了。我赶紧下楼见他。只看他是浑身大汗,一个劲地大喘气。他要我跟他一起回家。可是,单位还没有下令让回去。我要他先回家,别再出门。
返回到办公室,就收到了指示,要大家赶紧离开。撤走之前,不少人匆忙地交换了各自的家里电话号码和住址,特别是给那些家在曼哈顿外的同事,以防他们被困,回不了家,至少有一处可投靠。后来听说,因为停止了公共交通服务,他们长途跋涉,久经周转,数小时后才步行到家。
匆忙地跑下楼,往家赶。路上是人人快走奔跑的景象。
(三)
到家后,未婚夫算是放心了。站在窗子边,望着下城那边的滚滚白烟,痛苦万分。平时欣赏不已的双子塔已经消逝,再也回不来了。
发生的一切太突然,那么地逼真,也那么地超真,可是,又怀疑到底是不是真的。
谢天谢地,未婚夫就在身边。他最初是要在9点钟,到北塔楼的23层开会。只因为其中参与的一方,头天晚上从加州飞来,航班误点迟到。西海岸和东海岸本来就有3个小时的时差,加上延误,远道之客马上要求修改第二天会议的时间表,从9点换到了11点。由此,未婚夫在会议之前,有时间去健身房。两个小时的变动也就改变了他的命运。我一辈子都在感激那位从未见过面的加州人。
后来听到不少类似的情节 —— 那天偶然的、或者无意的时间更改,变成了生与死的分界线。
在家里不知所措,恍恍惚惚,都在想应该做些什么,又不知道该干什么。听到新闻提到医院缺血。未婚夫拉着我就往距家最近的Beth Israel医院方向跑。
志愿献血的队伍已经有上百人,排到了快两条街以外的地方,还不断地在加长蔓延。男女老少都有,更多的是年轻人和中年人。一片万籁俱寂,大家有条不紊地排队等待。
一位面熟的高个子男人从队伍的前头,开始与志愿者一一握手。他的前后跟随着像是保安人员。离我们不远时,才认出是纽约州州长George Pataki,在感谢每位鲜血的人。他的握手和致谢就这样顺着长队一直延续下去。
无论计划措施是多么的缜密周全,千万的准备也有万千的不足。何况在那种空前未有的状况下。
排队等了几十分钟后,医院传话说,不必再等了,医院没有足够的储存设备,接收不了更多的献血。也有人说,医院不需要那么多的血。因为,急救车从世贸中心那边已经带不回来还需要输血挽救的人。后者更让人难受。
没有能够出上力,很有失惑感。回到家,又是面对着下城那边的滚滚烟雾和发出来的异味,还有电视机里反复重播的、沉重的撞击画面。
亲朋好友的电话接连不断地打来,问候查看是否安全。回答久了,都变得有些机械。有的人在电话里伤心地痛哭,有的默默无语长久。。。不知道是应该继续接电话还是不该接,该说还是不该说。
后半天都干了些什么?是怎么度过的?真是迷糊不清,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些不明不白地无辜离去的人,他们的灵魂仍在,永世长恒。活着的人用毕生去追思他们,为他们祈祷。
也不尽地慰藉感叹,自己的身边还站着另外一个生命(后来成了自己的另一半)。要比那么多的人幸运!
人生微小脆弱,随刻即逝。关键的一刹那,又经常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当它在自我把握之时,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每秒每分,珍重共命运的亲友们,好好地活着,阻止重蹈本来就不应该发生的那一幕。

纽约 911 Memorial Building (照片来自网络)

推荐阅读以往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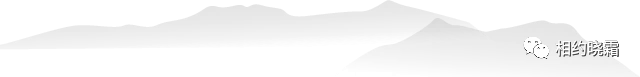
关键词
双子塔
曼哈顿
9点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