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与陈省身:两位同时代的数学大师(二)


华罗庚和陈省身都生于秋天,两人相差不到一岁,今年将迎来陈先生的110周岁华诞。“赛先生” 拟分篇刊登11年前蔡天新教授为纪念华罗庚先生诞辰100周岁撰写的文章,以飨读者……
评论区点赞第一的读者将获赠蔡教授签名本《数学传奇》。
撰文 | 蔡天新
从清华园到欧罗巴
旧中国的科学底子薄弱,尤其在1930年以前,当时只要是在外国取得博士学位回来的人,统统被聘为教授,这些人回国后待遇优厚、衣食无忧,尤其是因为教学繁忙、资料匮乏,缺少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基本上放弃了学术研究。
以姜立夫为例,在南开数学系最初的四年里,只有他一个教师,因此什么课都得他亲自讲授。1949年以后,他又在广州创建了岭南大学数学系(1952年并入中山大学)。而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当时只有法国的硕士学位(罗庚到清华那年他再次留学巴黎,两年后获博士学位返回清华),却是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现名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大学数学系的创建人和首任主任。
可是,清华大学毕竟是 “皇家学院”,美国退回的 “庚子赔款” 除了资助姜立夫这样的青年才俊留学以外,还用以创办和扶持清华学校(1928年升格为清华大学)。
还是在清华学校时期,这所学校请来了康乃尔大学数学硕士郑桐荪(后来成为陈省身的岳父),由他担任大学部算学系主任。1928年,正是在郑桐荪的举荐下,熊庆来出任更名为清华大学的算学系主任(几年以后浙江大学的陈建功也举荐苏步青接替自己的系主任职位),不久又有芝加哥大学博士孙光远和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加盟。
这四位教授中,也只有孙光远仍在继续做研究,他的主攻方向是微分几何,毕业论文发表在美国著名的《数学年刊》杂志上,回国后也多次在日本的《东北数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令陈省身十分仰慕。而清华之所以吸引陈省身,还因为它的研究院可以派遣成绩优异者公费留学。

陈省身先生
孙光远是浙江余杭(杭州)人,与陈省身算是半个同乡。省身从南开大学毕业那年,清华大学刚好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院,他遂成为孙光远的研究生。不过,这位学问出色的孙教授个性也比较特别,没过多久,他便因为与学校领导闹矛盾,竟然撒手不管自己的研究生,奉行 “凡清华的事我一概不管”。
两年以后,孙光远应母校南京中央大学之聘永远离开了清华。不过,孙教授后来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也曾长期担任数学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1978年,陈省身回国时到访南大,专程看望了孙先生,一年后孙先生就去世了,此乃后话。1933年,陈省身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硕士,答辩委员会的三位成员是叶企孙、熊庆来和杨武之。
回到1930年,由于清华算学系只录取了陈省身和他的同班同学吴大任两个人,而后者因为父亲失业不得不到广州中山大学先做了一名助教。系里因此决定缓招研究生,这样陈省身就在清华做了一年的助教。次年8月,正当陈省身开始读研究生之际,华罗庚来到了清华大学。
作为一名助理员,华罗庚的办公室就在系主任熊庆来的办公室外面,无论谁来找主任,都会见到他。华罗庚性格外向,说话风趣,很快他便与大家熟悉了,包括陈省身。华罗庚甚至自嘲自己是 “半时助理”,因为按照清华的规定,高中毕业的人才能当助理,而他只是初中毕业。
事实上,当时华罗庚的薪水只有助教的一半,约为四十元,略高于工友,与做研究生的陈省身所获的生活津贴(三十元)相差不多。华罗庚因为家里贫困,只身在清华园,他的家属仍留在老家金坛。那年夫人又生了一个孩子,这回是个儿子,清华五年,他只有在寒暑假才回到老家。王元在《华罗庚》里,记载了恩师晚年一次甜蜜的回忆,“每当我寒暑假回家乡探亲时,熊庆来先生总是依依不舍,他生怕我嫌钱少不肯再回来了。他哪里知道,清华给我的钱比金坛中学给我的钱优厚多了,清华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虽然华罗庚来清华那年,借着成名作的光在《科学》上一气发表了四篇论文,但那些工作都是原来在家乡完成的,属于低水平的初等数学。到清华以后,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高等数学,接下来的两年里没有发表论文,而是埋头自学和听课。
据前任四川大学校长、数学家柯召回忆,“(当时)陈省身与吴大任是研究生,我与许宝騄是转学的高年级学生,华罗庚是助理员。我们五个人在一个班里,教员就是熊庆来、杨武之与孙光远先生。由他们三个人给我们五个人上课。” 陈省身也曾写到,“这个时期是罗庚自学最主要和最成功的一段。在那几年里,他把大学的功课学完了,并开始做文章。”
在华罗庚听的课中,有杨武之先生开设的群论课,同时华罗庚还随他研习数论。杨武之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华林问题的各种推广》,其中最好的结果是证明了“每个正整数都可以表示成9个棱锥数之和”,此结果在世界上领先了二十多年。虽然杨武之回国后学问做得少了,却培养了华罗庚在数论方面的兴趣,晚年的华罗庚怀着感激之心回忆道,“引我走上数论道路的是杨武之教授”,“从英国回国,未经讲师、副教授,直接提升我为正教授的又是杨武之教授”。
从1934年开始,华罗庚的数学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每年都发表六至八篇论文,其中大多是在国外刊物,包括德国的权威杂志《数学年刊》,一时声誉雀起。这些论文大多是数论方面,也有的是代数和分析,显示了他多方面的兴趣和才华,这大大超出了包括熊庆来在内同事们的期望。来清华之前,华罗庚的英语尚未过关,凭着他自己独创的 “猜想法”,很快做到不仅可以用英文撰写数学论文,还能借助字典阅读德文和法文文献。他的方法是这样的,遇到不认识的单词时,先根据上下文猜测其意义,再查字典验证。这样一来,就会记忆深刻。

沉迷于数学王国里的华罗庚
正当华罗庚在清华开始大显身手的时候,自小目标远大的陈省身也已通过硕士学位答辩,准备出国留学了。1934年7月,清华大学的教授评议会通过派遣他去德国留学的议案,所用的款项仍然来自那笔 “庚子赔款”。参加会议的教授中既有他未来的岳父郑桐荪和 “媒人” 杨武之,也有校长梅贻琦、文学家朱自清等。月底,陈省身在上海坐船去欧洲,途经香港、印度、苏伊士运河到意大利北部的的里雅斯特,再从那里坐火车到汉堡,开始随先前在北京认识的汉堡大学布拉施克教授研究几何。
说到这位德国导师,陈省身与他的结识要归功于同城的北京大学。就在财源充足的清华修筑大楼、广招贤能的时候,历史悠久的北大却人心涣散、纪律松驰,经常拖欠教授薪水。待到文学院院长、国学大师胡适(此时校长是蒋梦麟)出任掌管 “庚子赔款” 退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之后,力促其通过了资助北大的 “特款办法”,情况才有了改变。
北大研究院也在清华研究院成立两年之后挂牌,同时开始邀请外国专家来校讲学。布拉施克便是最早来到北大的数学家之一,他的系列讲座题目是 “微分几何的拓扑问题”。在南开读书时,陈省身就随姜立夫先生学习过布拉施克的几何著作,因此很容易跟上,每次听课都没有拉下,得以结缘这位数学大家。
易北河与剑河之水
汉堡大学非常年轻,年轻得几乎难以置信,她与南开大学同一年(1919)创办。而在科学文化事业发达的德国有的是历史悠久的学府,比如洪堡大学(1810)、哥廷根大学(1737)、图宾根大学(1477)、海德堡大学(1386),尤其是哥廷根,因为希尔伯特的出现成为世界的数学中心。可是,陈省身首先考虑的是导师,那时假如他愿意,他还可以选择英法或美国的名校,就像其他留学生做的那样。

陈省身母校汉堡大学圆形主楼 | 作者摄
晚年的陈老谈到自己成功的秘诀时,认为一半是天份,一半是运气。可以说,陈省身最初的运气便是结识汉堡大学这位喜欢云游的布拉施克先生。他抵达汉堡是在1934年秋天,此时希特勒已经上台,所谓的 “公务员法”也已颁发,规定犹太人不能当大学教授,哥廷根这类名校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而汉堡这所新大学因为没有犹太教授相安无事,可以继续做学问。
等到1937年,“新公务员法” 颁布,连犹太人的配偶也不能当教授,汉堡大学三位数学教授中才有一人被迫移居美国。那时,陈省身早已获得博士学位,被导师推荐到塞纳河畔的巴黎跟大数学家嘉当深造去了。
陈省身之所以没有像其他数学家(包括华罗庚在内)那样,把勤奋视作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手段,是有他的原因的。他的小学只读了一天,中学又少读了两年,便以第二名的成绩按同等学历考取南开大学,拿到硕士学位的当年即出国留学,可谓是个天才和幸运儿。
由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给的奖学金比较高(即便四分之三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无法相比),陈省身始终自信满满,他经常下高级餐馆,邀请同乡吃饭,即使如此仍有许多积余,自费到巴黎继续深造(基金会自然又给予追加资助)。唯一辛苦的可能是过语言这一关,那时的欧洲大学不像现在通用英语,好在他在南开便上过德语和法语课,有一定基础,到汉堡以后去补习班恶补一下也就成了。
要说陈省身在汉堡的学术研究,他并没有埋头写论文,因此也没有发表许多论文,而是把重点放在学习和掌握最前沿、最先进的几何学进展和方法上,同时与一些大家建立起比较广泛的联系。除了布拉施克和嘉当以外,陈省身还与法国布尔巴基学派的代表人物韦伊、美国普林斯顿的维布伦等有了交流。这就像长距离的跑步或划船比赛,必须紧紧跟上第一梯队,才能伺机突破并超越。
必须提及的是,陈省身为人真诚,很善于交朋友,这里以他与嘉当的友谊为例。虽然陈省身的法语水平不高,与不会任何外语的嘉当无法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但在 “二战” 最困难的时期,他却从美国源源不断地给嘉当寄去食品包裹。
相比之下,自小苦出身、又缺乏家长和名师指点的华罗庚更多地依靠个人奋斗和自学,因此也特别刻苦。即使辍学在家替父亲小店做伙计,他也起早贪黑地看书,甚至比开豆腐店的邻居起床还早。因此,当华罗庚后来被清华破格聘为职位低下的助理员时,特别珍惜也更加努力地钻研学问,他在短时期里便在国内外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研究论文,这与 “名门出身” 的陈省身风格自然不同。不过,在布拉施克访问北大三年之后,清华也邀请到了两位级别更高的大数学家,那便是法国数学家阿达玛和美国数学家维纳,他们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也更久。
阿达玛在数学的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工作,其中在解析数论方面尤为出色,他率先证明了素数定理,那是 “数学王子” 高斯梦寐以求的结果。那项工作是在19世纪末完成的,即使半个世纪以后,因为这个定理的一个初等证明,又颁发了一枚菲尔兹奖和一枚沃尔夫奖。
遗憾的是,阿达玛来中国时年事已高,不在前沿做学问了。而维纳那时刚过40,可谓年富力强。作为控制论的发明人,维纳为数学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虽然研究方向不同,但维纳的函数论功底很好,他推荐华罗庚去了自己年轻时求学过的剑桥大学,跟随当年的老师哈代。不用说,华罗庚去英国的奖学金也来自那笔 “庚子赔款”。
如果今天有人做出华罗庚那样的成就(虽然那时远没有达到他的最高水平),早就有外国同行(比如美国的大学教授)
出钱邀请了。但在20世纪30年代,尤其像英国和剑桥那样的老牌帝国和学府,是非常吝啬的。即使是殖民地印度出来的数学天才拉曼纽扬,而且是哈代主动邀请来访的,也是由印度政府提供路费和生活费。
那次罗庚赴欧洲的旅途是选择陆路,即沿着西伯利亚铁路,今天的留学生是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当华罗庚与物理学家周培源做伴,经由莫斯科抵达柏林,陈省身也从汉堡赶来相聚。那会儿正逢夏季奥运会在柏林举行,陈省身陪华罗庚兴致盎然地一起观看比赛。
这不是华罗庚和陈省身在欧洲的唯一一次晤面,当年秋天,陈省身离开汉堡转道伦敦去巴黎时,也曾特意到剑桥看望了华罗庚。当然,从陈省身轻松面对学问这一点来看,他到柏林和剑桥并非单纯去见华罗庚,而是与他比较贪玩也有关系。毕竟,奥运会和牛顿的剑桥大学对每一个青年学子都有吸引力。
这里需要提一下,据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档案记载,在华罗庚到剑桥访学之前,曾两度获得该基金会资助,让他到汉堡大学研修,但不知何故,都没有成行。倘若那时华罗庚来汉堡,可能会随赫克或较为年轻的阿廷研究前途无量的代数数论,那样的话,后来中国数学的面貌将会有较大的不同。
当然,历史是无法改变的。华罗庚抵达剑河之滨时,哈代正在美国旅行讲学,行前他看过维纳的推荐信和华罗庚的论文,留了一封短函请系里同事转达。哈代在信中告诉华罗庚,他可以在两年之内拿到博士学位。可是,华罗庚为了节省学费和时间,放弃了攻读学位,他在剑桥期间,专心于听课、参加讨论班和做论文。

剑桥流水 | 作者摄
不难想象,像华罗庚那样的初中毕业生要获得申请博士的资格,需要补考多少门课,那无疑会成为他心理的一种折磨。而假如华罗庚真的读了博士,那今天剑桥的某所学院倒是多了一位来自中国的著名校友,就像与华罗庚同年同月出生的同乡钱锺书就读的牛津埃克塞特学院一样。
哈代那时已经年过花甲,当他一年后旅行归来,似乎也没有给华罗庚以指导,至少没有像当年拉曼纽扬来访时那样有合作。可以说,华罗庚又一次依靠自学,只不过这回从中国的最高学府转移到了世界一流的大学。他在剑桥的两年时间里,写出了十多篇堪称一流的论文,大大超出了以前的水准。用王元的话讲就是,“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成熟的数学家了。”
当然,这与剑桥拥有非常强的解析数论研究团队不无关系,这支团队以哈代为核心,他们与当时最顶尖的数论学家、苏联的维诺格拉朵夫联系密切。有时维氏会把一篇新获得的结果一页页地传真过来,剑桥这边随即加以讨论和研究。
两年以后,华罗庚启程回国,当他向哈代辞行时,大师问他在剑桥都做了哪些工作,华罗庚一一道来。惊讶之余,哈代告诉华罗庚自己正在写一本书,会把他的一些结果收录其中。这本书便是剑桥出版社出版的《数论导引》(1938),华罗庚的那些结果可能是近代中国数学家最早被外国名家引用的。
华罗庚在剑桥取得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完整三角和的估计、圆法和华林问题、布劳赫-塔内问题以及哥德巴赫猜想等方面。与此同时,华罗庚有了后来成为他代表作的《堆垒素数论》的腹稿,而他另一部相对通俗的数论名著与哈代的著作恰好同名。
值得一提的是,华罗庚在剑桥期间,并没有在美丽的剑河上学会传统的撑篙,或到苏格兰等地游览,却以不懈的毅力学会了骑自行车,这对患有腿疾的人可不容易。华罗庚学车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节省时间,因为在剑桥这座大学城里,租住的房子、办公室和图书馆通常离得比较远。华罗庚在剑桥的另一大收获是,他与苏联数学家维诺格拉朵夫建立了学术联系和友谊,这对他回国以后的研究尤其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以英国人的矜持和冷漠,华罗庚与哈代或剑桥的其他同事难以建立和保持陈省身与嘉当那样的友谊。(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蔡天新
浙江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求是特聘学者,近作有《小回忆》增订版、《我的大学》、《26城记》、《数学与艺术》、《经典数论的现代导引》(中、英文版)、《完美数与契波那契序列》(即出),主编《地铁之诗》、《高铁之诗》。
评论区点赞第一的读者将获赠蔡教授签名本《数学传奇》。

制版编辑 | 卢卡斯
启蒙·探索·创造
如果你拥有一颗好奇心
如果你渴求知识
如果你相信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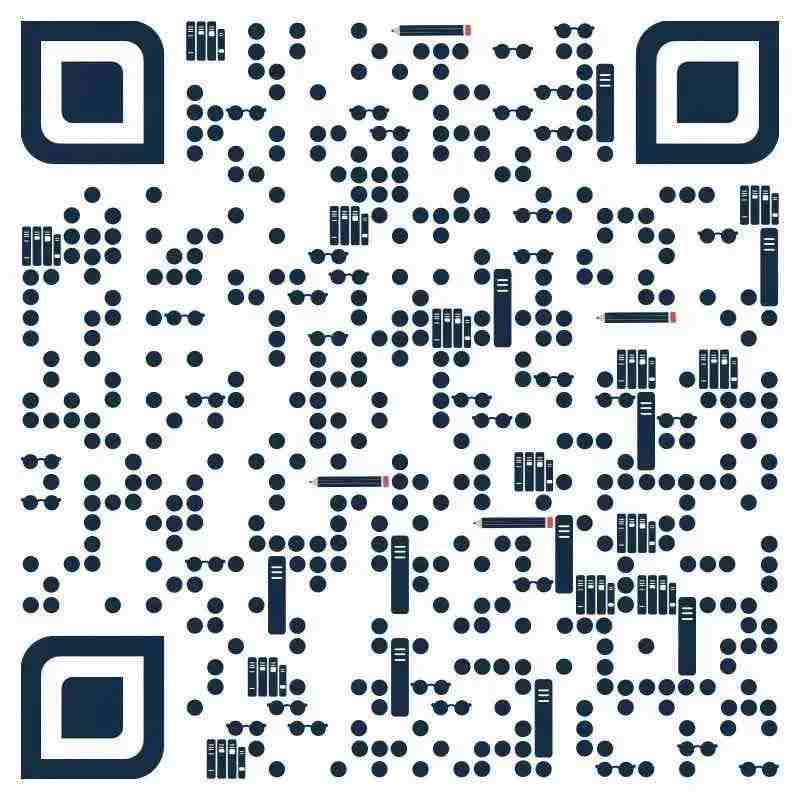

欢迎关注我们投稿、授权等请联系
关键词
数学
数学家
大学
数论
清华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