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何炳棣先生



何炳棣(1917年4月6日-2012年6月7日)
撰文|江才健
不记得确实是什么时候和何炳棣先生开始有了来往,但一定是在我1998年到美国开始写《杨振宁传》以前的事。何炳棣和杨振宁是1945年同船赴美留学,两人以后一直维持亲近的友谊,我写《杨振宁传》那一段时候,住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近,与何炳棣所在的尔湾相去不远,所以不时会与他见面谈话。
一般在谈论学术人物的时候,总喜欢说起他们的头衔,譬如说是博士、院士,还是什么奖的得主,但是和社会上任何一个领域是一样的,其实这些相同的头衔,多只是一个表象,内里也有三六九等之别。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识见,还需要有许多其他的评断标准。
我对何炳棣有较深刻的认识,应该是1996年以后的事。1996年6月间,杨振宁到台湾接受新竹清华和交通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当时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场座谈会,除杨先生外,另两位对谈者是何炳棣及陈之藩教授。
对谈后我替《中国时报》写的社论《科技与人文整合过程中的文化自信》,副题就是《由杨振宁、何炳棣两院士对谈谈起》,文中提到二人都触及为学方法论上所谓宏观和微观的问题。我记得当时的印象是,怎么何炳棣这个史学家,谈文论理似总不忘科学的方法,杨振宁是科学家,强调科学的方法不令人意外,何炳棣对于科学态度,似乎比另外一位学电机的陈之藩更为固置其事。
会有那样的想法,实出于对何炳棣在史学工作认知的浅薄。何炳棣1950年代完成英国土地改革博士论文之后,很快决定转入中国史的研究,而奠定他史学研究地位的明清人口论巨著,正是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数以千计地方志资料,以及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大量资料,以扎实社会科学资料佐证完成。他不止「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爬梳浩瀚资料,更能够以透视眼光撷取资料里隐含的深意,他尝谓自己的史学研究不是「发现」,是「发明」,显现对于自己学术识见的一种自许和傲气。
证诸他在明清社会阶级流动研究,所提出「丁」和「亩」在文献中代表意义的创新看法,对于当时西方对中国历史研究主流观点带来的挑战,他的自许和傲气,可说并非过甚其辞。
1996年以后我与何炳棣便有较频繁的联络, 1997年1月他替我在《中国时报》负责主编的「时报科学」版写了一篇专文,分两个礼拜刊出。文章的题目是《由科学训诂互证看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
何炳棣之所以会写这样一篇文章,主要源于他自1968年起开始对中国农业起源独力攻关,并且不得不「孤军奋战」面对海外相关学科专家的「围攻」,他反对当时史学界认定稻作农业起源于西亚两河流域的主流看法,并提出论据由概念上批驳他们所谓的游耕法农耕。
另外,是因为当时何炳棣看到《洛杉矶时报》才刊出美国著名农业考古学家一篇专访,说前几年中美两国50位考古及相关学科专家的考古重要成果,证实长江流域是世界栽培稻作物的摇篮,时间有九千年之久。
我猜想,何炳棣一定乐于他的这篇文章刊登在一个科学版上,原因是他在2004年出版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就写道,他在开始向农业史进军之时,便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一生中至少能有一篇文章刊登于真正科学的期刊中。当然,在那之前,他的文章《美洲作物传华考》早已刊登在《美国人类学家》那一本声望甚高的科学期刊之上,能够再刊登在一个科学版上,应该也是欣然以对。

何炳棣先生的学术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
1998年我到洛杉矶长住一年,开始杨振宁传记的访谈和资料收集工作,便不时到何炳棣居住所在的Turtle Rock,他称之为龟岩村,看望他。
何炳棣的住家是一栋白色,相当有现代风格的独立家屋,后面还有一个相当大的院子,头一回去的时候,他特别带我在院子里看一些花木。整体来说,在南加州那个经常阳光普照的环境中,那样一栋透着新潮小巧的房子,其实并不很容易将之与身形高大的何炳棣连在一起。
我大多数和何炳棣见面,都是早上十点多到他的家里,我们会在家里谈话约两个小时,然后开车到住家附近一个小商场的一家中国餐馆吃午饭。何炳棣总是去同样的一家,餐馆老板也很认识他,通常会点几个菜,何炳棣并不特别节制,有海鲜也有肉类,通常我吃一碗饭,他有时要吃上三碗,后几年他还可以吃两碗饭,「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总出现在我的脑海。
由于我们和杨振宁的熟识,谈话也难免多次的谈到杨振宁。何炳棣好几次提到杨振宁的《读书教学四十年》,说他非常欣赏那一本书,也承认受该书影响,后来自己的回忆录也就用了《读史阅世六十年》那样一个类似的书名。
他也很喜欢说,杨振宁比他幸运,因为科学界有一个清楚明白的标准,不像人文学界,自己受到许多无稽的攻击和委屈,言下颇有「瓦釜雷鸣」之意。何炳棣和杨振宁同在1944年考上第六届的庚款公费留美,他常说自己的平均分数是78.5分,比杨振宁多了7分。
2000年我到洛杉矶,和由华府到那里采访民主党大会的《中国时报》同事老友傅建中会合,一同去拜访何炳棣。傅建中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脑中有一本清帐,而且记忆力过人,与何炳棣大有谈头,两人声音都很大,你来我往,那时候何炳棣的夫人邵景洛身体已经不好,通常不大出来见客,那一天居然走到客厅来张望,大概想不知来的是什么人,比家里的大声公声音还要大。
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对太太著墨不多,不过他回忆录中,有他老师雷海宗的专节,其中雷师母张景茀对雷老师的回忆,说出雷海宗是一个多么体贴的丈夫。以何炳棣对于雷老师的敬和佩,他回忆录中的这一段文字,恐怕多少有自况心境的味道。我有不少机会观察何炳棣和邵景洛相处的情形,予外人严厉刚烈形象的何炳棣,与太太相处,虽不能说铁汉柔情,但是对太太的体恤,确实是自然流露的。
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出版后,当然引起许多的注意,但是有没有洛阳纸贵,以及他自己对于社会反应是否满意,我有些观察,对于何炳棣的心境也有些了解。我看《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谈论他最先拒绝芝加哥大学历史系邀请他去担任访问教授,但是接受到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访问几天的一段,印象特别深刻。
1962年6月何炳棣由温哥华到美东访问途中,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停留访问几天。当时的系主任,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acNeil)在他到达当晚,就设家宴款待。第二天早上,在芝大历史系一批赫赫有名历史学家近乎口试的会面,何炳棣以他过去十多年扎实研究的根底,以对中西文化深广的涉猎,加以对英语驾驭的自负,使举座学者皆惊讶于他在完全没有讲稿情况下,居然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出入东西、博引旁征的深刻谈话,而大为叹服。
何炳棣自己也认为那是自己一生最成功的学术谈话之一。第二天麦克尼尔在办公室拿出一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聘约,请何炳棣签字,他说自己心无二念的欣然同意。他后来引述著名史学家刘广京教授来信说,「此邦中国史,均势一变矣!」,可看出他自1950年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皓首穷经,并发出「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的狮吼以降,对于自己学术工作的自信和自负。由这个观点来看,他对于《读史阅世六十年》获得的反应,或许是有些失望的。
如果说得严格一点,何炳棣成功学术生涯背后的一个悲剧,是他始终认为,自己未能「名称于世」。造成他有这样感受的原因,其实并不全然是他自己也承认的「个性上的缺陷」、「不能容忍愚蠢」,以及与中外学术人物相处不和睦,更多的是对于学术有一种过于执著的单纯,不肯认识那不只是智力的较量,也充满了人性的算计。
何炳棣除《明清人口论》及《明清社会史论》奠定他史学地位,晚年更投入中国上古思想史研究,他所提出的孙子思想是中国上古思想根源的论点,可以说颠覆了过去许多主流研究的基本看法。他曾经将一篇文章《从爱的理论评价<红楼梦>》示我,文章以《失乐园》和《红楼梦》作一对比,探讨东西方文化中对爱情态度以及价值的不同。这些作品可看出他不仅思想深刻,而且涉猎广泛,也终生服膺「绝不做二流题目」的自我期许。
他的这种「横空出世」自许,虽说其来有自,但是也给他带来许多不愉快甚至痛苦。何炳棣1974年就当选了美国亚洲历史学会的会长,亚洲历史学会在美国之所以地位崇隆,有著中国长久积弱,中国历史解释权旁落「番邦」的时代因素。何炳棣以他扎实数据为本的史学创见,并具备「出入无不自得」的英语能力,以及「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斗志,舌战也笔战群雄,虽然赢得他应有的地位,但内心想必依然是感慨深重的。
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对于另一位史学思想家余英时获得「克鲁吉奖」(Kluge Prize)耿耿于怀,原因是余英时在1990年代曾争取亚洲历史学会会长,却败于一位日裔的女历史学家罗友枝(Evelyn Rawski)。1996年罗友枝就任亚洲学会会长演说中,公开就汉化议题向前任会长何炳棣挑战,何炳棣立时强烈回应,引起学界重视,汉化议题也再度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罗友枝后无回应,似乎是默尔认输。
因为杨振宁的缘故,何炳棣待我以忘年之谊,对于杨振宁和李政道的不睦,他未多置其辞。何炳棣与李政道亦有私谊,李政道儿子李中清是他少有的得意弟子之一。何炳棣称赞李政道的艺术收藏品味,但是他与杨振宁一直是惺惺相惜的好友,他过世之后,他的儿子曾经发电子邮件给杨振宁,说父亲最后告诉他,杨振宁是他最好的朋友。
最后一次看到何先生是2009年,那时夫人已故世,他也曾经小恙,家里有儿子回来陪同。那回我特别给他在家门口照了几张像,已显著暮年的苍老,后来我们出外吃饭,注意到他只吃了一碗饭,真「廉颇老矣」。
后来两年多,有两次机会经过洛杉矶,却没有时间去探望他,2012年6月传出他去世的消息,不免怅然。
何炳棣常常说,他黄昏时分会在住家附近急走几英里,我可以想像他那高大身影,急行在龟岩村的夕阳裡,或在家里绕室而行的景象,有时觉得他像一只被困的猛虎蛟龙,心中有许多别人不能了解的感情,以及一些无法畅然而吐的块垒。

注:本文原载于《观察》2014年6月,作者系科学文化工作者,赛先生获授权转发。
制版编辑 | Morgan
启蒙·探索·创造
如果你拥有一颗好奇心
如果你渴求知识
如果你相信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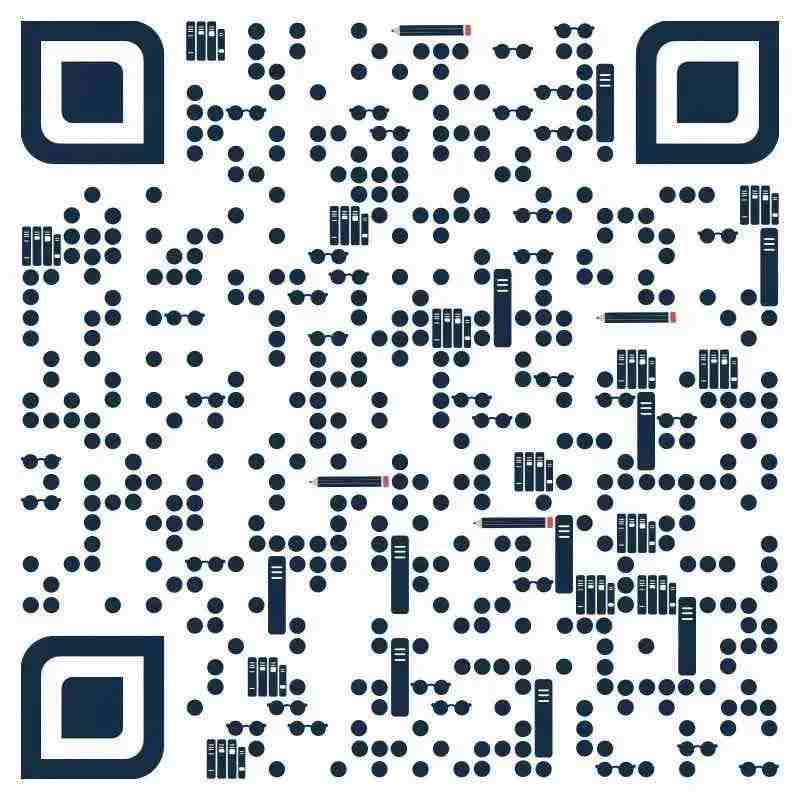

欢迎关注我们投稿、授权等请联系
关键词
史学
图书馆
学术
先生
地位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