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大师樊畿:只要醒着,你就必须思考数学
平均阅读时长为 3分钟



樊畿先生在课堂上。
撰文 | 么 辰
责编 | 叶水送
数学家中的数学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樊畿先生视数学为自己一生的职志,甚至将其作为唯一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的存在形态,他是一位天才的数学家,一位“纯粹”的数学家,一位数学家中的数学家。
最能体现先生这一特点的,是他在UCSB对着全系研究生说过的一句被广为传颂的名言:“你们现在已经是职业数学家了,只要醒着(EVERY WAKING MOMENT),你就必须思考数学!”
伯父回忆,和樊畿先生谈话,他绝对是三句话离不开数学,或者可以说,数学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他曾经对伯父坦承:“不论我遇到什么烦心的事情,在心情很坏的时候,我就看数学,想数学,心绪马上就平静下来了。”

1996年,樊先生夫妇来伯父家中小聚。
1996年,樊先生夫妇来伯父家中小聚。伯父清楚地记得,那天在客厅里,已是82岁高龄的樊畿先生随手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他最近证明的一条关于“在局部紧致拓扑群上一类重要影射的表示”的定理,随后还为伯父条分缕析地叙述了这条定理的条件和结论。
因为腿疾的缘故,此时的樊畿先生已不良于行,无儿无女的他,只能与年逾古稀、同样因疾病而腿脚不便的夫人相濡以沫。面对着两位白发老人,伯父本想劝老师找一家条件好一些的养老院颐养天年,可当他看到眼前兴致勃勃地谈论数学问题的老师时,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伯父忽然觉得,一位具有如此清晰的数学思维与活跃创造性的杰出数学家,根本不可能栖身于养老院!
可以说,在现实世界中,此时的樊畿先生或许已经不再年轻,但在数学世界中,他仍然和年轻时一样,可以毫无阻碍地驰骋遨游,并且乐在其中,就像《庄子·逍遥游》中扶摇万里的鲲鹏,真正做到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师长:“半亩方塘长流水,呕心沥血育新苗”
樊先生执教逾40年,教过的本科生不计其数,带过22名博士生,指导过89位来自各个国家的访问学者。可以说,樊先生是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这一方讲台是他永恒的人生舞台。
在北大读书时,伯父就通过樊畿先生翻译的《解析几何与代数》而与先生神交已久,对先生的学术成就非常仰慕。这本书是樊先生早年根据德国施佩纳教授和施赖埃尔教授合著的《解析几何与代数引论》和《矩阵讲义》译出,1935年商务印书馆作为“大学丛书”出版。
1983年春季,也就是伯父在UCSB的第二个学期,樊畿先生开始给数学系高年级学生讲授“高等线性代数”一课。人生的机缘实在神奇,从樊畿先生当年在北京大学翻译这门课的教材,到如今伯父在美国听他讲授,时间已过去了半个世纪,空间上跨越了半个地球,而距离伯父在北大第一次读到《解析几何与代数》,时间也已经过去了20多年。数学系安排伯父给樊先生当助教,他怎能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伯父开始以助教身份随堂听讲。
虽然“高等线性代数”仅是数学系高年级学生的一门基础课,但在伯父的记忆中,樊畿先生依然认真对待每一节课,整个授课过程中,他不仅表达叙述非常讲究,每一个概念、原理的来龙去脉都讲授得清清楚楚、透彻深刻,而且板书也写得一丝不苟,尽显大师风范。
更为难得的是,樊先生还能自出机杼,把自己对于“线性代数”的独特看法完美地表达出来,把“线性算子”的某些背景和理论在有限维空间里展现给学生,如果台下的学生日后继续学习“线性算子理论”,他们一定会心中有“例”——有很多简单而具体的例子,而这对于学习抽象数学是极其重要的。
樊畿先生风趣幽默、豪爽傲岸的性格,对数学的“痴迷”“倔强”和“较真”,这一切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对学生近乎苛刻的要求上。
他对学生的严格程度远远超过美国教授的通常做法和标准,即使是在中国,也很难找到像他那样严格要求学生的教授。这一点给伯父留下了深刻印象。
首先,樊先生决不允许课堂上出现“不带脑子的学生”。
在美国大学课堂上,学习气氛一般是非常自由的,学生可以随时打断教授讲课,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是愚蠢可笑的问题,而大多数教授也不以为忤。但在樊先生的课堂上,如果学生问出不长脑子的愚蠢问题,樊先生会非常生气,一定会对其严厉训斥。
伯父记得,有一次,樊先生在课堂上提问某个“子空间”的“维数”是什么,一个学生答非所问地回答那个“子空间”是什么。樊先生把粉笔往桌子上一拍,走下讲台指着那个学生的鼻子训斥道:“我问的是‘你的年龄’,不是‘你’!”
除了决不允许出现“不带脑子的学生”,樊先生还决不允许“只带着脑子来的学生”进入他的课堂。
樊先生要求学生上课时必须认真做笔记,他坚信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决不允许只听课却不做笔记的学生出现,即“只带着脑子来的学生”,如果学生做不到这一点,他还要亲自管教一番。
有一次,他注意到有个学生不做笔记,当即停止讲课,对那个学生大发脾气,质问他:“你不做笔记,是否能把我的讲课内容记住?”学生回答:“不能完全记住。”樊先生更加生气,问:“那你为什么不做笔记?”学生无言以对。樊先生又严厉地训斥道:“你不是来好好学习数学的,而是来我的课堂里看热闹的。我强烈建议你出去!”那个学生没有出去,只得乖乖拿出纸笔来做笔记。
伯父有位一起攻读博士学位、很是自命不凡的美国同学。他上任何课都不做笔记,可这种学习习惯在樊先生的课堂上却完全行不通,得到了和以上那位学生相同的“待遇”,从此之后,他也开始规规矩矩地做起了笔记。
伯父曾问过樊先生,做不做笔记是学生的自由,何必如此认真呢?樊先生给出了他逻辑缜密的回答:“首先,我的讲课内容不在任何一本现成的书里;其次,我也不相信有任何人能光凭脑袋就可以记住我的讲课内容。不做笔记是懒惰的表现,懒惰的人可以学数学吗?我的课堂上没有‘自由’,要‘自由’,就别来上我的课!所以我建议这种学生出去,别在我的课堂上‘受罪’!”
除了以上两者,樊先生还决不允许课堂上出现他认为的“滥竽充数”的旁听者。
70岁的樊先生在退休前给博士生讲授的最后一门课程是“拓扑群”,这是他数学教学生涯的收官之作,同时也是樊先生最喜欢讲的一门课。伯父有幸聆听了这门课程。
大数学家樊先生要开讲“拓扑群”了,这不仅吸引大部分数学系研究生来听课,就连不少物理系理论物理的博士生也慕名前来。更为难得一见的是,教室的后排竟也坐满了数学系的中青年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像这样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盛况”,是伯父生平所仅见。
如果是一般的教授,遇到这样的“大阵势”,会感到受宠若惊,而樊先生却恰恰相反,他似乎非常不喜欢这种“盛况”。在正式讲课之前,他首先宣布:“来看热闹的人下次就不要再来了,我不是动物园里的!”随后他给大家解释说,要想听懂这门课,必须学习过研究生水平的“分析”“代数”和“拓扑”。他随即点名查问学生的数学基础,并建议那些低年级的研究生,下次也不要再来了。他又严厉批评了研究生顾问不尽责,放任学生任意选课。
第二次上课,教室里的人数果然减少许多,但好像依然没有达到樊先生心中设定的标准,他在课堂上又训斥了一位不做笔记的学生。
第三次上课,樊先生干脆开列了30多本参考书和文献,这些书目由英文、法文、德文和俄文等语言写就。数学系规定,申请博士学位者必须掌握两门外语。有一位学生举手告诉樊先生自己看不懂俄文和德文。先生一听,当即发起了脾气:“法国、德国和俄国有那么多好的数学家,他们不一定非要用英文写作,你看不看?你不看他们的文章,怎么能成为好的数学家?!数学和音乐一样,各国的数学家心灵相通,不论用什么语言表达。你以为只懂英文就够了吗?”
最后,樊先生干脆把矛头对准坐在后排的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美国年轻一代的数学家,只懂英文,只看英文文章,其他国家数学家们写的文章,完全不管。这就是美国的数学越来越糟糕,美国出不来大数学家的原因!”
就这样,在“拓扑群”开讲第一周的三堂课里,樊先生堂堂训人、次次发火,终于,在第二周上课时,课堂上就只剩下包括伯父在内的六个“正经”学生了。伯父记得,那天樊先生精神抖擞地登上讲台,环顾冷冷清清的教室,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说:“这个班就应该是这么多人。”就这样,樊先生面对着这“硕果仅存”的六名学生,讲了整整三个学期的“拓扑群”。
樊先生对于授课的严苛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他将“拓扑群”作为自己的收官之作。因为这门课程在他心目中占据着极其特殊的地位——“拓扑群”熔“分析”“代数”和“拓扑”于一炉,综合了数学三大基础学科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包含了许多近代数学的思想、方法和结果,包括樊先生在内的众多世界级大数学家都对其有颇多建树。他之所以对“拓扑群”有如此执念,目的是要在退休前留给UCSB数学系一个课程样本,一个数学系高班博士生课程的标准,一个绝不允许被降低的标准。
游子:“尘世百年双鬓改,乡关万里一身遥。”
对于祖国,对于母校北京大学,樊畿先生始终都是一位游子,而他的返国之路,却走了整整50年……
面对关山千万重的故土,樊畿先生不可能不惦念祖国和母校。但祖国和母校之于他,并不只有空间上的距离阻隔,他之所以迟迟不回国,更多还是出于其他难以言说的隐情,樊畿先生曾经多次和伯父谈到其中的原委。
第一个原因是,樊先生和夫人燕又芬女士的身体可能难以适应中美间的长途旅行,同时,考虑到踏上故地,看到亲友,想起往事,樊先生说:“我担心内人和我能否面对,能否承受!”
第二个原因是,这片故土曾发生过令樊先生夫妇不堪回首的过往。抗战期间,他先后失去了三个儿子和自己的老父亲,这成为先生心中永远无法治愈的伤痛。原本打算只在美国逗留一段时间的他,随即赶上中美断交,两国顿成两个阵营、两个世界。身在美国的樊先生得到的家乡的第一个消息,竟是老父老母都已凄凉离世的噩耗。每念及此,他都会不能自制地号啕大哭。
第三个原因是,樊先生因其巨大的学术成就,早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又连续两届出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樊畿先生认为自己不懂政治,不搞政治,也不愿参与政治,他曾对伯父坦承:“当所长,也仅仅是为提升台湾数学研究的水准尽尽力,那里毕竟也是中国人的地方。”“是否回国看看,完全没有政治因素才好。我不懂政治上的事情,但我不能不顾钱思亮。”(作者注:钱思亮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我们是老朋友,我去大陆要不要跟他打个招呼?如果事先问他,他一定会叫我‘不要去’;如果不管他,我径自跑去大陆,不仅他这个院长没面子,难免有人还要找他的麻烦!他不像我,我是美国籍,我不必看人家的脸色!”樊先生托伯父把这个意思转告给一直期望他回来的北大江泽涵教授,并明确表示:“一旦卸任所长,当尽快回国。”江教授听完后说:“樊畿还是不改脾气啊,我记忆中他从来没有做过沽名钓誉的事情,他不做损人利己的事。”
1989年5月,樊畿先生接受国内北大、清华、北师大和中国科学院的联合邀请,在去国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回到北京,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同事、老同学,并分别在以上四所院校进行了精彩的学术演讲。在北大访问期间,丁石孙校长代表北京大学热烈欢迎樊先生,专门为他隆重举行“名誉教授授予仪式”,亲自为他颁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证书,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樊先生随后进行了关于“算子函数”的学术报告,而那也是伯父第一次听到樊先生用他的母语中文进行学术演讲。樊畿先生的返国之旅成为了当年中国学术界的一件盛事。

返国期间,樊先生、樊师母与伯父、伯母以及樊先生的学弟、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前系主任栾汝书先生(左二)在一起。
在北京停留的数日,樊先生见到了与自己情同父子的江泽涵教授,访问清华大学期间,先生的老同事、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赵访熊教授和先生在北大时的学弟、曾任清华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的栾汝书教授等学界耆宿,率应用数学系的部分师生,以座谈会的形式欢迎他。
樊先生特别钟情于颐和园的山水,于是伯父和众多亲友专门在颐和园听鹂馆为樊先生夫妇接风洗尘,并陪伴二人畅游颐和园。他兴致勃勃地对大家谈到了回国后的观感:“常言道‘十年河西,十年河东’,我离开祖国时间太久了,到处变化之大,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师生情深:“我再来时人已去”
樊先生对于没有才能又不用功的学生毫不客气,但面对聪明用功的好学生,樊先生却是很偏爱的。在樊先生眼中,伯父是一个勤奋用功的好学生,所以,在高标准、严要求之外,樊先生对伯父展现出了如慈母一般的关爱与呵护,一位师长对于一位学生的浓浓温情渗透进了二人近三十年的交往之中。
即使在伯父毕业多年后,樊先生都始终关注着伯父的学术发展,他不但会仔细阅读伯父发表的每一篇文章,还格外留意其他数学家对于文章的反应,甚至比伯父自己还要认真细心。只要他看到有数学家发表的文章中谈到了伯父做过的工作,或者把他的某篇文章列为“参考文献”,樊先生就一定要把该文带到数学系办公室复印相关内容,然后专门寄给伯父。
要知道,20世纪90年代,樊先生家里没有复印机、传真机,也未使用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手段,樊先生就完全通过这种最为传统的“手工操作”,给伯父寄送自己制作的“手工业制品”。伯父实在不忍心麻烦老师,却屡劝不止。伯父说,他一共收到过樊先生寄来的36件“手工业制品”,每一件都饱含和承载了恩师对于学生的浓浓温情和栽培之恩,成为今天伯父最为珍贵的收藏。

樊先生给伯父寄来的“手工业制品”,上面有数学家谈到伯父做过的工作。
1989年,樊先生回国期间,专门从美国带来新书送给伯父,(其作者分别是英国数学家Alan Paterson和卢森堡数学家Jean-Paul Pier),因为书里有章节介绍了伯父的研究工作。

樊先生回国期间专门送给伯父的两本书之一,作者为英国数学家Alan Paterson,书中有介绍伯父研究工作的章节。
1994年,伯父协助友人在美国创办了一所新型的小大学——国际科技大学(International Tech. Univ.),创业之初,举步维艰。谁知华人在美创办大学的消息不胫而走,跨越了半个地球传到台湾,樊先生当时正好在台湾讲学,在当地一份名叫《海外学人》的刊物上读到一篇相关报道。
先生虽然专精于数学,却不囿于数学,视野与心胸都极其开阔,他深知华人在美创业艰难,而创办教育事业更是难上加难。在当年圣诞节前,伯父收到了由樊先生和樊师母寄来的联名贺卡,那是一张极不寻常的圣诞贺卡,因为那里面没有一般贺卡上写的客套话,有的是对于伯父参与创业的肯定和勉励。同时,樊先生依然保留着民国时期恩师对于爱徒的称呼——用“您”来称呼伯父。这张贺卡,伯父后来从不轻易翻看,因为只要看到,涌上心头的往事就会让他潸然泪下。

樊先生专门给伯父寄来的贺卡,内容全文如下:传宽,凤琪:数月前在台湾的《海外学人》杂志上,看到您荣任International Tech. Univ. 的系主任,现在又知道贵校要在香港、深圳设分校,足见发展很快。可喜可贺!这次香港大陆之行,收获定多,我深知您创业的精神和能力,相信此途前程似锦,一切进行必能顺利成功!祝圣诞快乐!樊畿燕又芬同贺
2007年,伯父来到加州看望因中风而长期卧床的樊畿先生。伯父向他详细报告了自己的近况,师生二人长时间紧握双手、相视无语。眼前这位曾经独领风骚的一代数学大师,在课堂上意气风发的亲切师长,“望极天涯不见家”的思乡游子,此时已是一位身体虚弱、思维缓慢的垂暮老人。伯父无从知道,此刻的恩师是否仍在践行着他在UCSB说过的那句名言——“EVERY WAKING MOMENT”,是不是还在思考着数学问题。
次年,伯父再次去探视恩师,在北京还受丁石孙先生之托,为樊先生带去丁先生的两本新著。伯父看到樊先生的身体比去年略有起色,认为来年还会再见恩师。但谁曾想,那次见面竟成为师生二人的最后一面。再次相见时,两人竟已是天人永隔——伯父赶回母校加州大学参加恩师的葬仪。
2010年3月22日,樊畿先生在美国家中去世。
樊先生逝世后,亲属们打算为其出版著作全集,先生第二任夫人王晓霞女士也很赞成此事,北京科学出版社同样有意出版发行,并组成了以丁石孙先生为主编的编委会,由伯父承担具体的编辑任务。伯父专程来到先生府上清点、整理先生一生中发表在世界各地数学刊物上的论文副本。

樊先生逝世后,伯父在恩师生前工作过的书房夜以继日地清点、整理他的遗著,以备日后学术机构善加利用。
当时,先生的大部分遗物已被转移到车库。在车库里,伯父找齐了先生自己保存的所有论文副本,并一件件搬回书房,按时间顺序分门别类,保存在档案柜里,开列清单后,交付并嘱托樊夫人对其妥善保管。伯父认为,即使不能如愿结集成书(后来果真出现意外曲折,未能如愿以偿),起码日后可供学术机构善加利用。因为这是凝结了樊畿先生毕生心血精力的宝贵成果,万万不可随着先生的离世而散失!
在一张几乎与房间进深等长的桌子上,摆满了先生的著作。为老师整理遗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那间明亮宽敞的书房,伯父曾经多么熟悉!那是伯父当年向先生求教,受先生教诲,讨论数学问题的地方。如今,面对着先生留下的数量巨大的精神遗产,伯父睹物思人,物是人非之感油然而生。
“我再来时人已去,涉江谁为采芙蓉?”道出了人世间的多少离合悲欢!
樊畿先生是一位有着诸多学术成就的数学大师,对于伯父而言,又有知遇之恩、培育之情。樊先生爱生如子,伯父尊师重道。二人之间长达30年的交往,才酿就出这样一份醇厚的师生之谊!但两人的感情又不止于此,在师生情中还夹杂着友情甚至父子情。中国古人讲“死生契阔”,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可以超越生与死的界限,在生命中结识过这样一位“死生契阔”的好老师、好朋友,这是伯父一生的幸运。

制版编辑 | Morgan
启蒙·探索·创造
如果你拥有一颗好奇心
如果你渴求知识
如果你相信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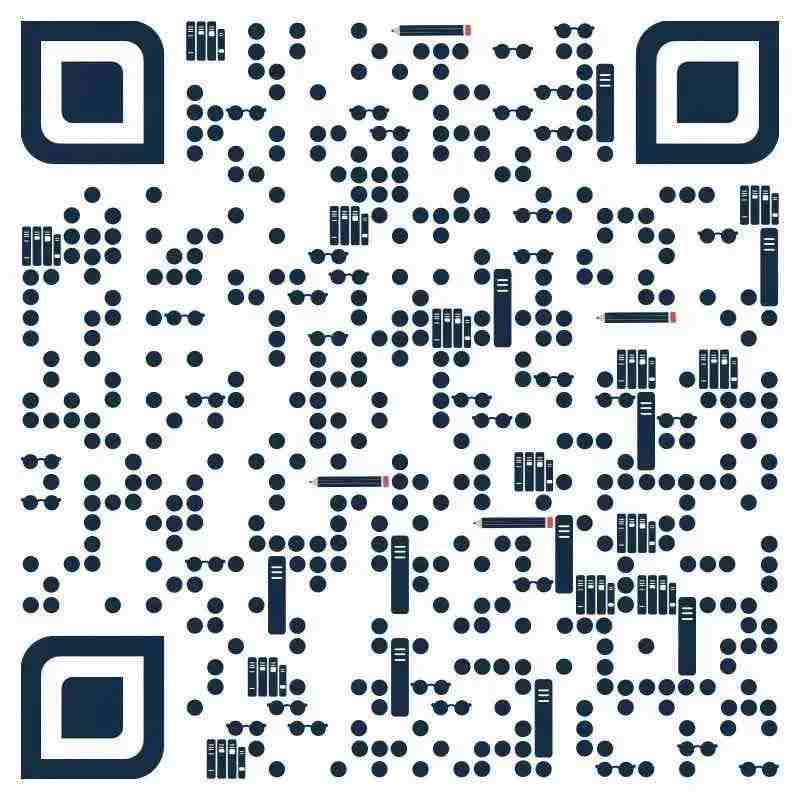

欢迎关注我们投稿、授权等请联系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