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来的那一天|谷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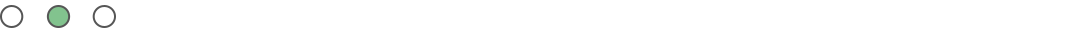
撰文丨韦洛昔
编辑丨张瑞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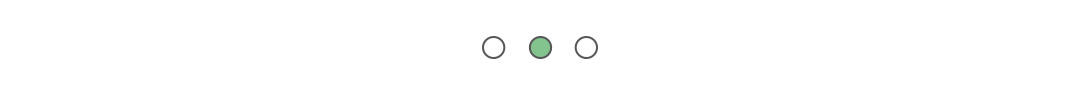
断鼻家族
十五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是这个初夏全中国最知名的动物明星,因其中一头断掉一截鼻子的幼象,象群被命名为“断鼻家族”。熟知的情况是,中国仅存的野生象群只生活于云南的西双版纳、临沧和普洱。换而言之,从未有象群进行长距离的北迁, 北上造访过红河州、玉溪市和昆明市。但如今,它们来了。
6月2日,关于象群的新闻一波三折:先有“云南野象群一路向北,快到昆明了”,然后“野象群没进昆明,转弯了”,最终“野象群连夜进昆明”。次日,昆明市委书记作出指示:要做好象群进入昆明主城区的应急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亚洲象群安全。
“不可能进城的”,昆明市民很是自信领导不会让大象任意而为,“昆明是省会,这么多车这么多人,不可能让大象进城的。”
象群确实没能越过滇池进入昆明城。在逗留的一周里,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省级指挥部每天都要投喂2吨以上的象食,试图引导大象向南行进,再每天出动60辆以上的渣土车,截断它们的北行之路。
没人能断言断鼻家族是否是因为渣土车和玉米棒而改变了向北的路线。此前指挥部也有多次这样的尝试,多以失败告终。
影响动物迁徙路线的主要因素是气候,大象来到昆明后,就遇上了阴雨绵绵的湿冷天气,海拔也上升了至少五百米,这不是他们喜欢的热带气候。或许是想告别凉丝丝的天气,断鼻家族离开昆明,重回玉溪——那天,指挥部出动了渣土车和应急车辆329辆,疏散了11071名群众。

6月1日,亚洲象群过河继续北上,30多辆渣土车集结待命©人民视觉
“你来晚了,你要是早两天在玉溪,就能看到大象。现在看不着了。”我和象群同天到达昆明,刚出机场,出租司机就已经对我的此行做出了预言。他的玉溪朋友开车去路边看过大象,还录下了几段小视频:象群们踩着敦实的步伐,在马路上晃着鼻子,扬起一阵灰。“他们现在在料草坝附近”,料草坝是一片连绵的青山,但他告诉我,“不让过去看的。”
在料草坝,兴奋的村民等待了一天,却在傍晚时从法古甸村民那儿得知,大象已经走去法古甸那儿了,“不会来啦,”他们坐在路边大声说。
有一个村民昨天在山上望见了在水库玩水的大象,手机里的视频足以证明他所言非虚。他向一位记者开价两百元,带他去昨儿看到大象的位置——并不保证今日能看到大象。这笔私下交易被一位前来拍大象的摄影师打断。“去林子里面找大象是非常危险的,”他有过拍摄野生象群的经验,“你和大象至少保持好几百米以上的距离,要是迎面遇上,太危险了。” 成年亚洲象体重在2吨到7吨不等,跑起来的速度可以到四十公里每小时,两百米的距离,飞人博尔特也跑不过亚洲象。

这场罕见的亚洲象北迁已经开始了十五个月。去年3月15日,16头野生亚洲象从云南西双版纳州进入普洱,缓缓北上。多数时候,象群穿梭在山林之间,偶尔闯入一些自然村落,踩坏庄稼,吃掉玉米。5月24日,断鼻家族进入玉溪市峨山县城。在人类操纵的无人机和天眼监控的关注之下,你能看到象群晃悠悠地走在马路上,也能看到几头象闯入修车行,接近峨山一中,撞坏居民的铁门和吓懵一只大黄狗。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中,长期监测亚洲象的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所所长郭贤明说,断鼻家族在去年十月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尽管版纳的亚洲象常有北移,但他们总是往返于版纳和普洱之间。当断鼻家族走到普洱中部时,郭贤明已经感到有些紧张:过去,只有独象曾走到这么北的方位。
2018年,一头独行的公象在夜晚从森林闯入普洱市区。普洱市疏散了群众和车辆,独留这只公象缓慢地行走在空荡荡的路灯下。五个小时里,它路过了六个小区,也踩坏了六个小区的栅栏和道路基建,最终被食物引导离开城区。
郭贤明没想到的是,断鼻家族越走越北,从普洱中部,走到普洱北部,再入玉溪。一头象宝宝在途中出生,两头成年象在四月下旬从玉溪折返回普洱。余下的十五头继续北行,越走越快。在半个月的时间里,由玉溪经红河州,再入玉溪,直至走入昆明地界。
昆明飘起连绵的阴雨,在向北行走了四百公里后,从热带雨林走上了云贵高原的“断鼻家族”, 就像没人说得清北上的原因一样,又开始了一样说不清原因的南下归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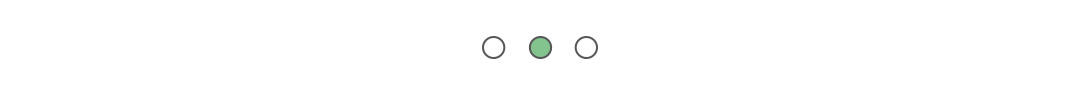
闯入者
省级指挥部每天都会出动十台以上的无人机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监测象群,在网络上,这成为一段段冲上热搜的视频,画外音的解说有时就像看欧洲杯那样紧张,比如当画面中出现了一只掉落水塘的小象,几乎淹没在泥水中,正在努力爬出水塘。
“它爬上去了,爬在大象的身上了。千万不要再滑下来了!千万不要!” 无人机屏幕前的人类喊道。画面中,一只大象在岸边用鼻子拖住小象的身体,另一只大象下到水塘中,用鼻子顶着小象的屁股,而小象,在无人机的俯拍中,显得短胳膊短腿(当然事实不是这样),还有点笨笨的。
“哎!又滑下去了。大象应该拦着它一点啊。”
尽管社交网络上的断鼻家族憨厚可爱,是能用鼻子拧开村民家水龙头的聪明动物,各地政府部门和亚洲象研究专家都处在严阵以待的工作状态,每日以“严防安全风险”、“强化安全防范”、“人象平安”作为新闻通稿的收尾。一个少被提及的细节是,去年7月,断鼻家族在普洱市思茅区南屏镇大开河村造成了一名村民死亡——它们庞大身躯蕴涵的力量,让这轻而易举。
亚洲象不仅有力量,还具有一些哺乳动物中最为高级的社会结构。它们是母系群居动物,寿命接近人类,大约在60-70岁,家族里包括一头母象和她的象崽们。公象到了十二岁左右便离开家族独自行动,寻找配偶。家族中留下母象和幼象,关系紧密,彼此忠诚。相比较敏感易怒的独象,群象往往性情温和,他们的重任是保护幼象。如果它们与人类发生冲突,一般都是因为幼象。

在西双版纳州勐阿镇,有一群国内攻击性最强的亚洲象。十四年前,这些象群从勐养的森林里逛到了勐阿。澜沧江上水电站的修建,抬高了水位,象群被挡在了江南岸的勐阿。头几年,象群常常走在村民耕种好的田地上,偷吃香蕉、甘蔗和苞谷。
直到有一天,一头小象因为误食了村民的农药而亡。一位曾经在勐阿进行亚洲象保护工作的志愿者同我讲述了这个故事:
“2015年,有个农户打完农药,习惯性留在甘蔗地里。小象去甘蔗地时,就把那两三袋农药卷出来,吃到肚子里。”幼象死了,象群围拢在它们的孩子身边,从这点看,象群有着如人一般的情感,那是它们的哀悼方式。但因为大象是一级保护动物,要解剖知道死因,人们就用催泪弹把象群赶走了。
“象群就站在山坡上,站下来一排,就在远处望着人类解剖小象。当时的林业站站长跟我说,那是很壮观很肃穆的一个景象。”
“这之后,那群母象看到人就要杀。我和很多村民都聊过,大家都一致认为是因为解剖,让母象以为是人类杀了小象,要报复。”
另一位在勐阿做过野外考察的亚洲象研究者姜志诚描述了象群杀人的惨烈:“大象造成的人员伤亡,最后尸体都是不完整。有的身体看上去还是人形,但是内脏已经碎裂,内出血。有一对夫妻上山采茶,遇到了大象,妻子被象鼻子撞了一下,盆骨碎了,肝脏也内出血。如果大象要追人,他会鼻子把人碰倒,然后用鼻子和上颚这一块的,把人摁在地上压,把人往角落挤。大象还会用脚把人摁在地上搓来搓去。”
即使在“万物之灵”的人类面前,大象也是深具威严感的,而某种程度上,当我们说一种动物深具“威严感”,多半是因为它们深具“威胁”的能力。

五月中旬,当断鼻家族进入红河州境内时,石屏县岔河村村委会还只是通知大象在附近山林间游荡,大家注意安全。在界面新闻的报道中,一周后,5月23日凌晨3点24分,岔河村村民戎桂芳在自家床上一睁眼,大象就站在她面前。大象撞开了她的家门,走入客厅,轻轻左转,又撞开了她的卧室门。一睁眼,大象的鼻尖就落在她的眼前。她缩在被窝里,不敢发出声响,等待大象转入另一间房,等待大象微微屈腿离开家门。
一天后,断鼻家族走入玉溪市峨山县大维堵村,从这时开始,在所有断鼻家族沿途可能经过的村庄,村民们都会收到预警信息,被要求临时转移。多数村民并不会看到大象进村的景象,但他们有时得承受大象的肇事后果:大维堵村村民石金明家两大包玉米干被大象吃了,大练庄村村民徐航家的1600斤玉米和100斤酒糟被吃了,峨山县县城一些汽车修理厂的大门被撞怀。北迁途中,仅在玉溪市活动的41天里,断鼻家族就造成了400多户群众财产受损,主要以经济农作物受损为主。北迁亚洲象沿途造成的群众经济财产损失,云南省都将进行定损赔付。
而省级指挥部的层层防范,不仅是防范大象的闯入,也防范那些从各地赶来热衷找大象的人——早已与野生动物隔绝的城市人,往往不明白遭遇一头野象意味着多可怕的命运。
大象进入昆明的第一日,指挥部劝返车辆530余辆次,包括记者和从市区前来看大象的市民。出租师傅望着警戒线外一溜儿的外地车辆,问我:“你们做新闻是不是特别难,一个事情要全国各地都来?”
一位同行告诉了我能看到大象的唯一方法:提前预判大象可能的路线,在拉起警戒线之前先进山,然后在山上架起相机。他等了两天,拍到了八秒钟的大象。
“进山之后住哪里呢?”我问他。
“睡车上啊。妈的,昨天差点把我冻感冒。”他说。
一位65岁奶奶也来找大象,她从未亲眼见过大象,但这几天在儿子手机上看到了不少大象的视频。在晋宁区的山路绕了七个小时后,她与儿子被拦在了警戒线外。奶奶在村外的田地了兜了一圈,听说这两天大象在这儿没有踩坏太多烟叶,连连感叹:“大象真是很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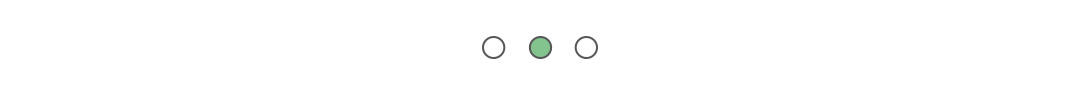
大象的退却
“为什么不把大象麻醉了,再送回保护区?”红星新闻曾经问专家郭贤明。
“不能麻醉。如果能麻醉了搬回来,我们早就做这个事了。我们过去考虑过,一旦有落单的,看时机成熟,就麻醉拉回来,但象群一直不分离,这个方案就不现实。这群象非常团结,哪怕有一头象被麻醉,其它象是绝不会离开的。特别是有小象,如果小象有了危险,其它象会把小象围在中间。”
这将造成玉石俱焚的局面。而相对于人类拥有的科技手段,威严的大象又是脆弱的。麻醉剂量一旦过量,大象就会醒不来,麻醉时间稍微长一点,倒下的大象,由于内部器官长时间挤压,造成器官破裂,也会很快死亡。
如今,大象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了。
一万多年前,与现代大象拥有共同祖先的猛犸象灭绝。第四纪冰川时期结束后——就是那个以刃齿虎、猛犸象为主角的动画片《冰河时代》发生时——地球上的陆地巨兽已经所剩无几。又过了几千年,大地懒、天山副巨犀,这些体型大约是大象六七倍的巨兽也先后灭绝,大象成了陆地之王。
不,不对,陆地之王是人类。多位研究者都认为,大象在地球上的天敌只有人类。
四千年前,大象出没于今天的北京以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等到公元一千年以后,淮河以北的气候变冷,大象因为无法越冬而南迁。但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的研究指出,即使在稍暖些的时候,中国的大象种群也没有恢复,“一定有其他力量在起作用,最明显的解释即是,大象在与人类持久争战之后败阵下来。可以说,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上退却的模式,反过来即是中国人定居的扩散与强化的反映。这表明,中国的农夫和大象无法共处。”伊懋可写道。
人与大象的争战持续千年:为了占据更多的耕地;为了保护庄稼免遭侵害;为了昂贵的象牙和可食用的象鼻。早在明代,村民们就知道驱赶大象至木栏之中,四周都是河沟,大象无法离开,正午时以火攻之,大象畏热,然后暴毙而亡。
后来,有了火药和猎枪,大象的威胁也就不值一提。
在中国,大象逐渐退居到没有人类活动的版纳密林里。1957年,中科院云南科考队经过野外考察,确证云南境内确实有野生亚洲象。此后,国家在西双版纳建立了自然保护区。

2017年,一位原武警森林战士在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看望曾救助过的野象 ©视觉中国
生态学学者何謦成对保护区境内的村民进行访谈和调研后认为,在版纳保护区,人象曾经互不侵犯,但一次外来人的“合法捕象”成为了当地偷猎大象的起点:当地数千年来崇敬大象的传统信仰被摧毁。
1971年,上海动物园想要一头大象。在征得国家林业局的同意后,上海动物园组织人员前往西双版纳的勐养子保护区寻捕野生亚洲象,便于运输和驯养的小象被定为捕猎的目标。为了射穿大象厚实的皮,上海气枪长设计出了长针头的麻醉弹,上海医工院研制出了麻醉时间更长的麻醉剂。在一年的捕杀行动后,一头七岁的小象被抓住,五头成年象被杀死。
这头小象被起名为“版纳”,来自一个有二十多头象的族群。“就在版纳被捕获后的连续几个晚上,丛林里大象的嘶吼声在山谷里回荡。”当年跟拍捕象全过程的纪录片《捕象记》解说道。
版纳的形象成了上海动物园的园标。在上海生活的46年里,版纳创造了亚洲象在国内动物园繁殖数量最多的记录,一共生养8头小象——母象通常一生中只生育三到四头小象。

七十年代之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景伞村、大和村等村落都陆续参与到偷猎亚洲象的生意中,最多的时候,景伞近半数村民都在捕杀亚洲象。
直到1994年,震惊世界的连环猎杀二十头亚洲象事件发生后,云南当地以判处主犯死刑的方式警告了所有的民间偷猎者,并再次清缴村庄里的猎枪。这之后,当地居民偷猎率下降了八成。最近一次被公开报道的亚洲象被偷猎新闻发生在2014年,一头雄性亚洲象在勐腊子保护区森林内被枪支射杀,象牙被取走。被村民发现时,大象尸体已经腐败。
到今天,在直面亚洲象时,村民往往束手无策。烧火、放鞭炮等炸出声响的方式已经恐吓不了聪明的大象。
因为人类小小的退让,亚洲象获得了更多生存的可能性。偷猎已经不是亚洲象保护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成了栖息地的不足。一方面,人类活动愈发侵占雨林,另一方面,对大象的保护,又让种群数量增加,导致对栖息地的更多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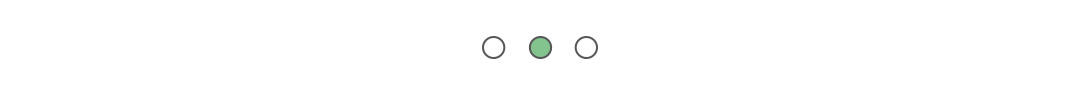
现有的亚洲象栖息地肯定是出了问题
断鼻家族逼近昆明地界时,一位热心市民给云南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发了微信,热心建议地处昆明郊区的野生动物园接下这十五头野生亚洲象,善待他们,进一步繁荣昆明的旅游业。半日过去后,他得到了答复:云南野生动物园最多只能再接收5头亚洲象,15头实在是太多了。
连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面积都不足以承载三百头亚洲象了。“‘大象数量超出原有栖息地承载力’这个说法,我们是认可的。”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版纳自然保护区管护区的高级工程师王巧燕说。早在2004年,前任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园长许再富即指出,通过对亚洲象采食范围计算,当时勐养片区的大象已经达到了150头,尚勇片约60头,均两倍超过这两个片断保护区的承载能力。
大象的数量在增多,而灌木、竹阔混交林覆盖的大象栖息地,在三十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二。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着适宜气候的西双版纳被定为我国重要的橡胶种植基地,先是国家种植,再是私人承包种植——橡胶有很好的经济收益,能让贫困的西双版纳村民填饱肚子。
北师大张立团队、王宏新团队及何謦成等人的研究指出,橡胶与茶叶等经济林的迅速扩张严重挤占亚洲象栖息地,亚洲象分布区域内的天然林地面积占比在三十年间从70%下降到了57%,橡胶林和茶叶种植面积则分别增加了23倍和2倍。

小伊是云南农民的儿子,也是一名云南生态保护的工作者。他说,人们常常只会指责当地的村民破坏了原始深林,却看不到这其实是一场“合谋”,“我们种了这么多东西,不都是卖到城里么?那些极端动物保护主义者来了就说当地人这不对那不对,把大象的地方都占了。可当地人如果没有把栖息地给占了,你们城里人是没有那么好生活的。农村环境的破坏,城里人都是有责任的。”
还有些改变是从顶端设计开始的。景洪水电站和勐海高速公路的建设都影响了象群之间交流和移动,各保护区之间也没有建立方便象群迁徙的生态走廊。保护区片断化的弊端日益凸显。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象群沿着公路网络进行移动时,也就逐渐走出了保护林,走到了村庄中,进入农田觅食玉米、甘蔗、香蕉等农作物。
“勐阿的村民被大象吃了很多农作物,他们也很无奈。我和勐阿村民交流过很多次,他们受到了损失,但他们觉得大象也很可怜。他们说有什么办法呢,大象也回不去了,也没有吃的,只能来吃庄稼。他们问我有什么办法把大象弄走,如果实在没有办法,那就在这里留着吧。这是村民的原话,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非常善良的人。”云南省林业厅保护处处长钟明川告诉我。

©视觉中国
对于断鼻家族出走的原因,各路专家已经讨论了一月有余。最喧嚣的推测莫过于,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太阳活动周期,太阳的异常活动诱发了地磁暴,而地磁暴以某种方式激活了大象的迁徙本能。
“怎么地磁暴就影响了这群大象,其他大象都不长距离北迁?” 这种推测遭到了多位云南省内专家的激烈反对。“此次15头亚洲象的长距离北迁超出了正常范围,可能有着复杂的背景和现实的内外因素,原因会比较复杂,不宜过度解读或早下论断,也不应过度炒作或娱乐化。”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教授杨宇明说。
“总体而言,现有的亚洲象栖息地肯定是出了问题。”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家孙全辉说。
尽管西双版纳保护区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88%提高到了现在的95%以上,但森林保护力度增大同时带来的是高大乔木,这从来不是大象的食物。“大象会本能地推倒几十厘米高的树木,不让这块地成林,但随着我们森林保护力度的加强,保护区里的荒地、次生林越来越少,郁闭度较高的林下草本植物减少,大象食物就减少了。”王巧燕说。
动物迁徙从来都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之地。充沛的水源,肥沃的草地,温柔的气候,或是安全的领地。尽管,从西双版纳向北,适合亚洲象的食物只会越来越少,气候也越来越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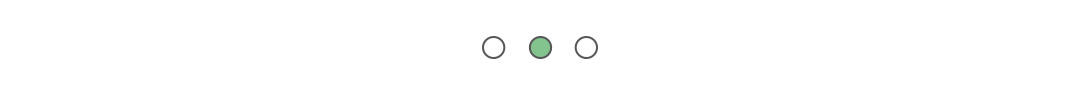
大象来的那一天
我常会问参与亚洲象北迁沿途防范的工作人员,你们是什么时候成立工作组的?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调配渣土车的?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监测亚洲象的?
“大象来的那一天。”他们都这样回答。就好像大象的远道而来,开启了一段历史。
在昆明,“大象”散落在各个角落:地铁站里禁止象牙交易的宣传画、绿化带里的大象形草丛、饭店门口的大像雕塑等等。尽管多数昆明人都没有亲眼见过大象,也无法区分亚洲象和非洲象的区别,他们都对大象抱有一种浪漫的亲切。
“他们可能就是想出来看看。”我许多云南朋友都这么说,他们好像不认为大象只能生活在西双版纳,“你没听说过那个笑话么,传说我们云南人都是骑着大象上学呢。”

《亚洲象保护校园宣教作文、绘画精选》中的一篇作文
从大象来的那一天开始,社交媒体上涌起了追踪大象最新动态的热潮,人们津津乐道大象的可爱,似乎还有一点蠢萌,将它们的北行看作一次愉悦的郊游,而不曾想过这可能是一次对象群生死攸关的求生之旅。
一个与断鼻家族几乎同时出走勐养保护区的象群,被监测员命名为“小缺耳家族”。小缺耳家族一路南下,从亚洲象保护区走入了热带植物保护区。今年春天,小缺耳家族几番试图走回勐养,但南班江上涨的江水阻碍了它们。“象群几次尝试过江,但因为里面有一头今年才出生的小象,小象几次被江水冲跑,所以它们至今未能过江。”在春城晚报的采访中,郭贤明说。
郭贤明也不知道大象在想什么。明明南班江上有几座石桥,大象却从未走上过桥。看样子,小缺耳家族打算在植物园里度过丰水期,即使这一带的食物也不足以支撑象群长期停留。
82岁的许再富有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里面记录着“小缺耳家族”的出现:
“关于勐养保护区大象出走的调研。大象进‘植物园’时间:2020年11月26日晚上11:30至凌晨1时左右。
当时两夫妇外出散步回家不久,遇大象三头(一公一母一小象)。因为他们站楼上,看得清楚。大象是从影视城经一斜坡路,从植物园的后门进入植物园,在餐厅及停车场停了约一个小时,吃了三个菠萝,也进到餐厅楼下。它们往内走动,吼声很大。他们养了两条狗,开始吠叫,后来不敢叫。后来三头象沿着斜坡道路走……途中大谷库的道路竹林旁有一黄色的狗窝,狗狂叫,被大象以鼻子抛死。”
“我们那儿附近有个影视城,砍了个五百亩橡胶地搞得一个皇宫,又搞了几只恐龙雕塑。大象经过恐龙的时候,把恐龙的一只脚和尾巴都撞掉了。”许再富捡了一小块恐龙尾巴放在家里,作为大象破坏的证据。
断鼻家族来到昆明夕阳乡的第二天,我在警戒线外遇到了七个村民。他们热情地带我去看了大象刚刚踩过的田地,“你看,这里一脚,这里还有一脚。它从哪里走下来,一屁股就把这个棕树撞倒,然后又来吃了这个棕叶。”他们指了指了山里,说:“现在大象就在前面七八百米的一个水塘那里喝水,大象天性喜欢水。”
他们向我介绍了半小时,才坦言自己不是当地人,而是从隔壁易门县驱车俩小时过来看大象的。已经花了一整个白天,从夕阳乡的村民口中,了解了大象来的那一天发生的所有事。
“大象可能走到易门的,你要不要跟我们去易门?”他们发出邀请。他们的期待没有落空,五日后,大象走到了玉溪市易门县。
日本朝日新闻在六月初连播了三天云南亚洲象北迁的新闻,派出了三名记者前去探访大象造访过的峨山县。“云南北迁象群意外走红日本”,微博出现了这样的话题。我询问了朝日新闻北京站的记者小张,追踪北迁象群的动力是什么,“可爱的动物不是新闻第一热点嘛,还是成群的”,小张说。
6月12日,中宣部新闻局组织中央媒体赴云南开展为期一周集中采访,以“云南亚洲象北迁”为契机,深入宣传中国及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
“大象的心思你别猜”,在云南,常有人这样说。晋宁区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曾以为大象拐弯了就不会进入晋宁,不需要成立工作组应对,“想着它不会晃到这儿,在昆明外面转一圈就走了的,没想到晚上突然又走进来了”,他们说,“大象太自由了,我们也没办法控制。”
有一位记者,在村里等大象两天无果,哪知道刚撤离大象就走来了,“他们在别的地方玩了两天,然后才走过来,我以为他们不会过来了。”他的语气有些失落。
大象来的那一天,姜志诚从红外线监测器中看到了象群经过之后,森林发生的变化:“一条路,大象走过后,紧接着就会有赤麂、水鹿,甚至印度野牛这样的大型兽类跟着通过。再然后,野鸡、白鹇也会跟着过,紧接着就是一些猫科的肉食动物,比如金钱豹之类的。”
大象是雨林的工程师。它用肥厚的大掌在密榛丛莽中踩出一条坦途,其他兽类就会紧随其后。在雨天,大象的一个个脚印还会积成水洼,昆虫从中冒头,又为野鸡、白鹇提供了食物,然后肉食的猫科动物又会来捕食野鸡、白鹇,一条绵密的生物链随之诞生。
“如果你去野外,那就能看到大象的粑粑里会长出很多蘑菇,那是一个天然的培养皿。大象的粑粑也是很多昆虫的栖息地,比如屎壳郎。”姜志诚补充道。
就是这样,在大象来的这一天,所谓的历史是,我们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它们,于是将“可爱”的蠢萌语言投射到大象身上,如果语言也是一种暴力,那这就是我们的又一次暴力相待。只是,在大象来的这一天,我们不得不明白,它们和我们一样共享着地球,象群也是这片土地的主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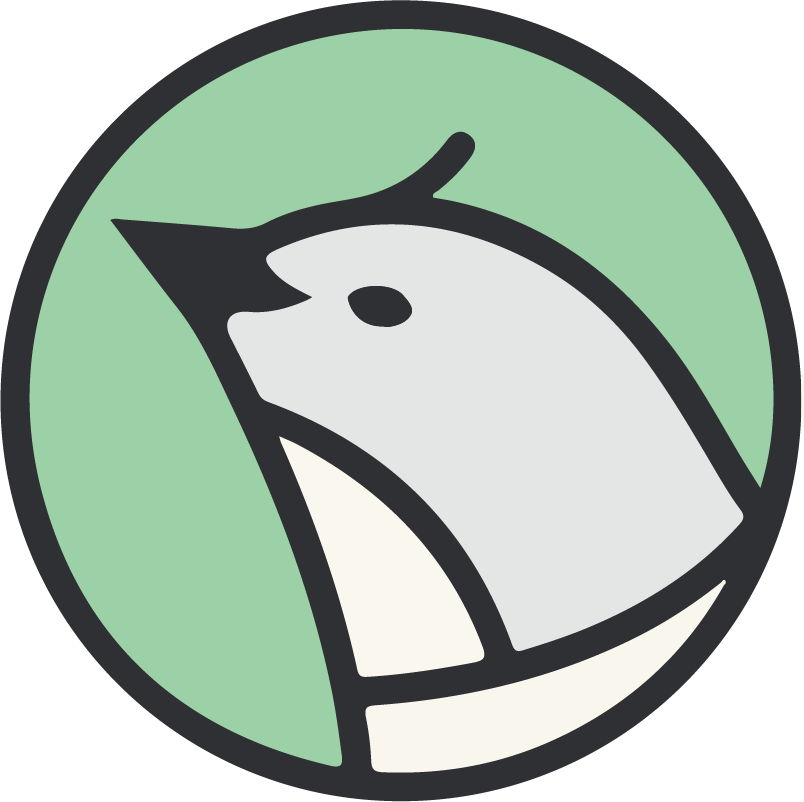 (来源:腾讯新闻)
(来源:腾讯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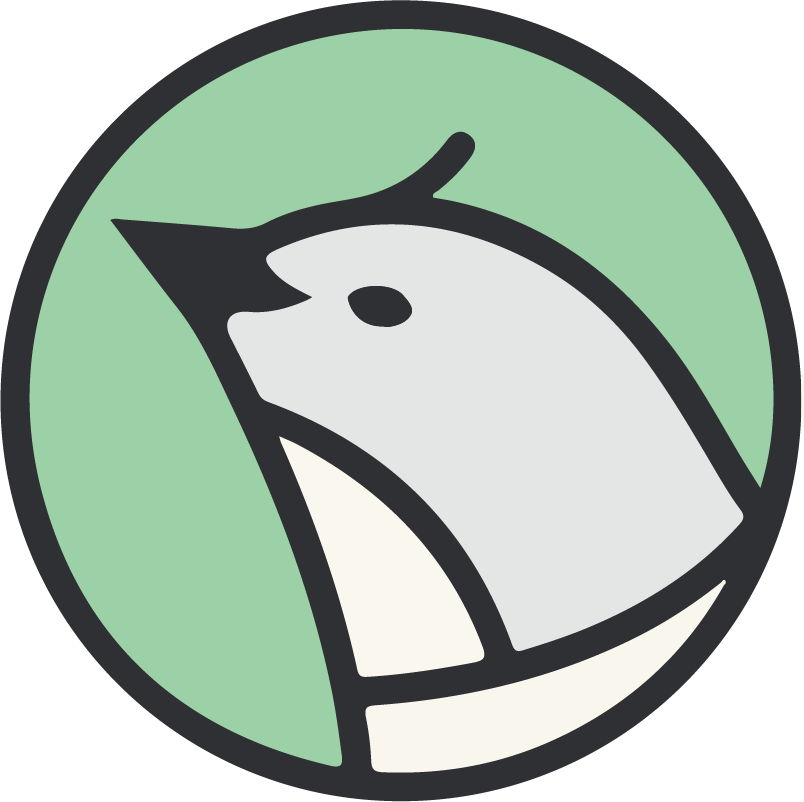
1.红星新闻:《深度专访:亚洲象北上是整体趋势,长期投喂或致野象生病》
2.中国新闻周刊:《西双版纳保护区专家: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建设“亚洲象国家公园”》
3.开屏新闻:《17头南下亚洲象:正尝试投食引导它们过江或绕路回保护区》
4.极目新闻:《麻醉遣返象群太难,优化原有栖息地才是最终方案》
5.界面新闻:《大象推门而入》
6.三联生活周刊:《追象狂欢之外,“断鼻家族”的真实悲喜》
◦ 感谢阿拉善西南项目中心对采访的大力帮助。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