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后》:中国群星为何闪耀?



· 这是第3921篇原创首发文章 字数 3k+·
· 鲁舒天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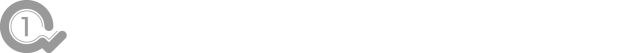
一方代表是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将军有次去大学演讲,对台下的流亡学生道:“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去服务,躲在这里干么?”
另一方则是将“有怀投笔者”看作国宝的陈诚:“国家虽在危难之中,但青年完成学业,极为重要,因为战后重建的责任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
最终结果,是后者结论压倒了前者,即“战时需作平时看”,不因为大敌压境就将“每一万国民中仅有一人”的大学生无条件地从课堂、实验室、研究室里拉到战壕填坑。这种指导思想延续了国家教育,不致使得人才断层,于多难之际为全民族的生存与复兴留下了血脉。
假设是前者意见盖过后者,历史便会改写,仅供追忆的西南联大,或许从一开始就沦为泡影。
故而我认为,以联大师生作为叙述对象的纪录片《九零后》,不以更具辨识性的“西南联大”而以平均年龄96岁以上的主人公为标题,非但不是拙计,反而十分恰当。

原因有三:
其一,导演徐蓓拍过《大后方》,也拍过《西南联大》,欲观详情可参前作;
其二,110分钟的时长装不下联大全史,例如上述弦外之音就不在成片取材之列;
其三,以《九零后》来展现战火中闪耀的中国群星,即规避了“标题党”,同时也提醒观者——真正好看的历史,从来都与人相关。
如同学者吕芳上在《战争、西南联大与历史遗产》一文所述:
“如果把大学校史写成一部革命史,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失败;要是把充满活力的校史,写成光有组织、只有制度,看不到灵魂、看不到人的历史,也同样不会讨好。大学本来就是活生生的一群人,聚在一块共同耕耘、切磋知识学问的学术乐园。
战争时期或许外在环境险恶,但教师埋头著述、勤快解惑,学生好像永远有填不满的求知欲望,师生交流绵密,知识火花热闹迸放、如响斯应,此所谓弦歌不辍。既是浩劫,也是风云际会,更是因缘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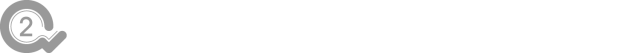
在《九零后》之前,同题材还有口碑出圈的《无问西东》。如果说《无问西东》的重心是人生理想的选择,那么《九零后》的切入角度,则更多聚焦于教育本源的追问:
为何在战乱频仍的抗战期间,国人尚能理解教育的真谛,在后方扎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在经济建设与科技水平已经取得巨大进步的和平时期,我们却只能在影像资料中回顾先哲?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所以被称为“教育界的珠穆朗玛峰”,因其于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社会秩序极为紊乱、政治局势极为动荡的上世纪30、40年代,历时短短八年,便开创了中国近代以来人才辈出的鼎盛局面。在西南联大师生中,共有2位诺贝尔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元勋、170多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以及100多位人文社科领域的泰斗。
换言之,如果没有这所由北大、清华、南开并校而来的学府以及它所孕育的知识精英,中国近现代的教育史恐怕都会黯淡无光。
评价一个教育体系是否成功,主要看它是否能够产生人才与新知识。要产生此二者,除了财力、物力这些硬件,更仰仗教育体制的设计这项软实力,其核心在于教育家和教育管理体制。
学者郑永年说过,从中外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来看,良育构建之要务,是政治家与教育家的分工。官僚除了为教学提供一个外部制度环境,其余事务均交给教育家与教授这等专业人才去做。只有教育家办学与教授治学,才能保证学校生产出合格乃至卓越的“产品”。
在这个问题上,前段时间热播的《觉醒年代》恰好可视为《九零后》的前传,五四以降的文化旗手,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与南开校长张伯苓,从平津流亡到长沙,再由长沙迁往昆明,一路颠沛,却未损知识分子自由独立的风骨。在他们周围,还聚拢着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钱穆、钱钟书、费孝通、朱光潜等一大批造诣非凡的学者。

《九零后》有段高光时刻,翻译家许渊冲与物理学家杨振宁各自回忆联大国文系的“轮流教授法”,闻一多的狂放狷介、陈寅恪的超然物外、罗庸的神思悠扬,皆令观者身不能至心向往之。
许渊冲惊叹于这些教授的写意与奔放,杨振宁则对不够系统的授课方式略有微词,但可以确定的一点在于,那时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教什么、怎么教,都由教授说了算;谁来教、教多久,则取决于教育家的判断。
比如文学院的教授陈铨,是留德归来的剧作家,在联大教授英国与德国文学。陈教授才华横溢、著作等身,但所持“历史是由英雄而非平民百姓创造的”的观点及英雄崇拜的相关理论,则使他成为了联大教员中唯一一位法西斯主义者,即便联大秉持兼容并包的学风,这样的观点也很难得到同行的接受,以至于他不得不辞去教授职务。

而在此之外,来自上位者的约束,则会激起联大师生的一致抵抗。比如CC系的陈果夫,30年代初就以“需要人力”为借口,建议停办所有文学院和法学院,把学生引向“更实用”的学科。
针对这类提议,联大文学教授朱自清反驳道——“大学教育应该注重通才而不应该一味注重专家”;联大社会学教授潘光旦指出,即便是工科生也要博采众长,以期成为该领域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而不是只有一艺之专的匠人;联大法学教授钱端升则直接回怼,大学本就是学习与研究学问的地方,一般不讲授实用知识。
而率领教务组与上位者斡旋的联大校长梅贻琦,则直接反馈:为了实用牺牲人文学科的做法是错误的,并主张政府允许联大执行规章时充分享有“回旋之自由”。
西南联大的教育家们非常清楚,所谓通才专才、文科理科、虚学实学,表面看是教育思路之辩,其本质关乎学校自治,一旦失去这一基础,无论人才培养还是知识创新,都会无从谈起。
在发布于1943年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伍斯特理工学院电机系毕业的梅贻琦甚至表示,真正的工业组织人才,对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学科、文化背景,都应当有充分了解。人文与社会科学涉及越多,受教之人便越博洽,越能帮助其在将来的物力与人力的组织方面排除万难。

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也认为:“出于实用目的而对科技产生的兴趣,非但不能保证科技成果的进步与维持,反倒可能使之倒退……技术的关键内核是纯粹科学,而技术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和纯粹科学得以繁荣兴盛的条件是水乳交融的。”
《九零后》的细节也验证了这一点。
联大机械系的学生吴大昌在参加“湘黔滇步行团”的途中,看到西南人民的水车灌溉,颇感好奇。他土木系的同学李鄂鼎也回忆,正是看到贫困山区缺少水力发电设备,才在三四年级的时候选择了水力发电专业。
故事值得玩味的地方绝非“学以致用”,而是一群流亡中的知识青年对纯粹科学所表露出旺盛的求知欲,这很可能是在硬件设施齐全、治学环境良好的今天,应试教育的佼佼者们所不具备的。而滋养了这种钻研精神的教育,一定不来源于某种注重现世回报的单一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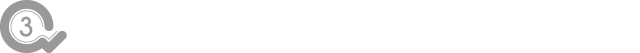
让人动容的是联大师生的悲愤,如罗庸所作校歌《满江红》中“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如沈从文在跑警报后把酒杯放下,哭着说“国家到这种样子”;又如“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的查良铮(穆旦)与缪弘。
外文系的诗人查良铮,是抗战期间联大834名从军学生中的一位,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中国远征军的身份入缅作战,并参与了凶险异常的野人山大撤退。在抗日名将戴安澜埋骨异乡的山野,诗人亲历了战争、历史与人心的残酷,促成了他那不忍卒读的名篇: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如果说这首《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还有《我的团长我的团》可以背书,那么在翻译官任上牺牲的联大学生缪弘,事迹则鲜为人知得多。
“进攻时,与他同组的美国兵怕死,都退到山下去了。作为翻译官,缪弘也可以跟着下去,但他没有临阵退缩,而是同战士们一起冲锋,结果被敌人的狙击手击中要害。”
缪弘做了一个盟军翻译官的分外之事,却也做了一个中国人在那个年代应该做的事。
如此种种,与朱光亚、邓稼先、巫宁坤等人后来的回国联系起来,完全无违和感,与王希季执念于科技建设和富国强军对照起来看,也不显突兀。一切后来的选项,都与这批人求学时经历的大轰炸有关,与其感受到的国家因工业落后而满目疮痍也有关。
《九零后》的抒情,并非某种理念或主义,而是家国命运与个人命运交汇之实际。

- 作者:鲁舒天,专栏写作者,独立评论人。公众号:鲁舒天小站。
「 图片 | 视觉中国 」


内容合作、投稿交流:[email protected]
阅读原文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