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一段长征路: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



· 张宇伟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字数 4k+·
2017年11月1日,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那天,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返校校友嘉宾的接待工作。在贵宾休息室,我向在西南联大学习了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请教:“杨先生,联大办学条件简陋,为什么出了那么多的栋梁之才?”
杨先生说,是“一股劲”,什么劲?它从哪里来?如何形成的?文化学术为国之一脉,史学家总结的“欲灭其国,先灭其史”“亡其国,亡其种,必先亡其魂”,其中的“史”和“魂”便是由文化学术所铸成。
抗战时期最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的南迁之路,就是“续华夏史,扬民族魂”的保有中华文明文脉延绵不断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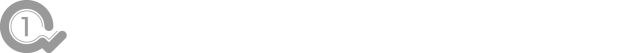
1937年北平卢沟桥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29日,北平沦陷。天津日军轰炸八里台,南开大学校舍大部毁于战火,天津随即沦陷。位于平津的三所名校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马上陷入无学可上、无教室可去的境遇。
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正式宣布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由三校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指定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常务委员,杨振声(教育部代表)任秘书主任。筹备委员会设主席一人,由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兼任。
1937年9月28日第2次常务委员会决定,三校旧生于10月18日开始报到,11月1日上课。之后,在京、沪、汉、粤、浙、湘、鲁、豫各地登报公告,同时通过电台广播、私人通信等多种形式,传出限期报到的消息。
这一消息让平津师生欢呼雀跃。然而从平津到长沙约有1500公里,学生老师要想方设法通过封锁线,通过沦陷区到达长沙,有的地方交通阻断,学生必须步行并自担行李,艰苦情况可想而知。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兼秘书长郑天挺在日记中写道:“始于十一月十七日离北平,经天津,至香港,入梧州,取道贵县、柳州、桂林、衡阳而达长沙,吾以十二月十四日抵长沙。”现在高铁5个半小时的路程,那时却需要25天。
截至1937年11月20日,旧生报到者1120人,其中:北大342人,清华631人,南开147人。加上借读生和新招学生,合计学生总数1496人。全校报到教师共148人,其中:北大55人,清华73人,南开20人。长沙临大设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共四院17个学系。

长沙临时大学确实是“临时”,教室、图书馆、餐厅、宿舍、实验室、办公楼等全部都是租用,校本部租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土木系也在该处上课。
宿舍一部分作为办公室,一部分供单身教职员住宿。另附近租下四十九标营营房三座,作为男生宿舍。又在涵德女校借用楼房一座,作为女生宿舍。工学院电机系和机械系全部寄宿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校内,借用该校设备和大教室上课。航空工程研究班在南昌航空机械学校借读。由于长沙校舍不足,文学院设在了离长沙160公里外的衡阳南岳圣经学校,也称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
突发的战争使第一次南迁之旅是仓促而煎熬的。但在这样简陋和临时的条件下,一些学者依然奉献出传世的学术成果,冯友兰书写了《新理学》,金岳霖完成了《论道》,汤用彤写就《中国佛教史》,钱穆先生开始书写《国史大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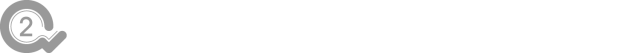
1937年11月1日(这一天后来成为校庆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没有开学典礼,没有开学仪式。上午9点多,忽然响起空袭警报,日本飞机来袭。11月24日,日机轰炸长沙小吴门火车站,伤亡惨重。12月13日,南京陷落,武汉告急。武汉离长沙只有300多公里,再次搬迁又被提上日程。
校常委会经反复研究,决定迁往云南省会昆明。主要的考虑是,昆明离敌占区足够远,另外,可以通过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的交通便利,在海外购买书籍、设备和办学仪器,与国外保持联系。
1938年1月20日,第43次常委会作出即日开始放假,下学期在昆明上课的决议。
从长沙到昆明南迁的第二次迁徙,是经过周密计划而实施的,校方做了三条南迁昆明的路线安排:
第一条是陆海并用。从长沙沿粤汉铁路至广州,到香港乘船至越南海防,再由滇越铁路到云南蒙自、昆明。大部分教师及其眷属,一部分体弱的男生和全部女生走这条路线。
第二条是陈岱孙、冯友兰、朱自清等教授坐汽车沿湘桂公路经广西桂林、南宁、镇南关(今友谊关)到越南河内,再由滇越铁路进入昆明。
第三条就是让人最感钦佩也最难忘怀的湘黔滇旅行团路线。
1938年2月4日,学校发出关于迁校步行昆明计划的布告,强调此次步行迁校的目的和要求:“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就是教育。步行时概适用军队组织。步行队到昆明后得将沿途调查或采集所得作成旅行报告书,其成绩特佳者学校予以奖励。”

学校发给学生的旅费是每人20元,发给教授的是每人65元,全校有51位教职员自愿将自己的旅费捐助给寒苦体弱不适于长途步行的男生和女生,条件是家境贫寒、家在战区、成绩优良、年级较高。
为保障路途安全,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专门派资深的军官黄师嶽中将担任湘黔滇旅行团团长。旅行团实行军事管理,共分成两个大队,每个大队有三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个小队,共计18个小队,中队长和小队长由同学担任。
张治中将军安排,给每位学生配备黄色制服一套、黑色棉大衣一件、绑腿一副、草鞋一双、旅行袋、水壶、搪瓷饭碗各一件、油布雨伞一个等装备。让南迁的学生队伍,远远看去,就是一个部队。近处一看,除了没有带枪,没有军衔之外,其他与部队一模一样。
经查档案材料,实际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学生有290人,此外还有11位教师辅导团,加上带队的军官。每个大队有一个厨师班(在长沙雇请了20位炊事工,自带行军锅灶),有两位校医,购买了三辆卡车(一辆运炊事工和炊具、两辆运行李)。
1938年2月19日,学生着军队黄色制服、戴软沿军帽,军训教官穿正式军官戎装,35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从长沙出发,进军昆明。
在出发仪式上,旅行团团长黄师嶽作动员讲话,他把此次南迁称作为中国第四次文化大迁移。第一次是张骞通西域,第二次是唐三藏取经,第三次是郑和下西洋。他讲到:“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为保存国粹,为保留文化。”鼓励大家维护神圣的教育事业,把抗战进行到底,努力完成这次南迁的历史壮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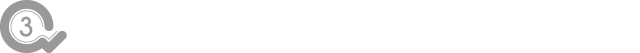
从长沙到昆明,需要穿越湘、黔、滇三省。原计划是步行加船,但计划赶不上变化,计划中的船只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起到大的作用,原来的船路也经常改为步行。
从2月19日出发,经68天长途跋涉,历3500里路,于4月28日抵达昆明。旅行团穿过湘西土家族、贵州苗族、侗族、布依族、云南彝族等各少数民族所在地,这既是考验,又是难得的了解民情,考察采风、收集资料的机会。
教育哲学系学生刘兆吉是山东青州人,他在闻一多教授的启发和鼓励下,沿途收集山歌民谣,克服了语言障碍、民众的猜疑和旅途的劳顿,一路采集了两千多首少数民族的民歌,平均每天采集三十多首。抵达昆明后,他将采集到的民歌编辑成《西南采风录》一书出版。

一位学生回忆道:“闻一多先生给我们更多的感觉是一个诗人、画家,一路上他老背着一个画板,还带上一个小板凳,走到风景优美的地方,就坐下来,用笔在纸上画起来。他画得很好,步行的学生经过都会停下来看一看他画的画。休息时,闻先生还会引吭高歌,更显得精神抖擞。”
政治系学生钱能欣将旅行的见闻感受记成日记,到达昆明后不久就出版了《西南三千五百里》一书,将近距离观察到少数民族语言风俗、婚姻民俗和社会风情,跃然纸上。
在旅行团中,有中国文学系、外语系、历史社会系、政治系学生50多人,各少数民族的习俗、语言、服饰及山歌民谣,成了他们研究考察的对象。每到一个山寨,大家顾不得旅程劳累,往往先要走家串户,在破旧不堪的茅舍与村民长谈。
当时还是助教的生物学家吴征镒回忆时说,李继侗教授带着他考察植物,指导两位研究昆虫的助教毛应斗和郭海峰观察昆虫。沿途中,吴征镒背着一个硬纸小盒,沿路采集了大量标本,并对沿途植物做了详尽记录。
地质组有14位学生,他们在袁复礼教授、王钟山助教的指导下,科学地记载地名、高度、气候、地质构造及收集化石,并坚持每天写日记。袁复礼教授还结合湘西、黔东的地形地貌,将大地山河作为授课素材,为学生讲解河流、岩石的构造形成,以及黔西地区地貌和地质发育理论。
化学系曾昭抡教授是曾国藩后裔,走起路来一丝不苟,即使遇到有小路的地方,他也必沿着公路走之字形,因此被人称为全团走路最多的人。

对大多数旅行团学生而言,他们第一次目睹了中国基层社会的落后,一些村民仍供奉神像和“皇帝万岁”的牌位,很多地方连小学都没有,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都极差,地方病、传染病(麻风病)常见,吸食鸦片现象司空见惯,红的、白的、粉红色的罂粟就种在离马路不到一里的地方。沿线常听民众对苛捐杂税和抽壮丁的抱怨。
在旅行途中,一些地方官民的热情接待,也让旅行团学生们感到温暖和受到鼓励。如3月17日,旅行团离开湘西进入贵州玉屏县。玉屏县小,无宽大旅舍容纳这么多的师生,县里由县长(刘开彝)具名贴出布告,“本县无宽大旅店,兹指定城厢内外商民住宅,概为各大学生住宿之所”,“对此振兴民族领导者——各大学生,务请爱护借重,将房屋腾出,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读到这样的布告,看到自己被称为未来的“振兴民族领导者”,旅行团师生感到无比振奋。
临大中文系向长清同学在巴金主编的《烽火》杂志上发表了全面记录这次徒步远征情况的文章,他回忆道:“行军是不分天晴和落雨的,除了好些人多了一副眼镜之外,我们的外表简直就和大兵一样。奇怪的是到了第十天之后,哪怕是最差劲的人,也能毫不费力地走四五十里。三千多里的行程中,我们的宿营地只是学校、客栈,以及破旧的古庙。有时候你的床位边也许会陈列一只褐色的棺材;有时候也许是猪陪着你睡,发出一阵阵难闻的腥臭气。无论白天怎样感觉到那地方的肮脏,一到晚上稻草铺平之后,你就会觉得这就是天堂,放倒头去做你那甜蜜的梦。”
闻一多后来反思道:“我虽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得很少,国难当头,应该认识祖国了。”旅行团学生“亲身走入社会,用‘灵魂之窗’实际去观察,比看死书深刻,且应有尽有,取之不竭。‘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皆哉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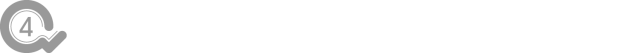
1938年4月28日,旅行团到达昆明,此前在4月2日,教育部转行政院令,“长沙临大”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隆重的入城仪式和欢迎大会上,湘黔滇旅行团团长黄师嶽将军作最后一次点名,点名毕,他向前来迎接的梅贻琦校长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然后庄重地说:“我把你的学生都给带来了,一个都不多,一个都不少,我交给你了!”
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总务长郑天挺在《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一文中写道:“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三千五百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的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此。”

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学生熠熠生辉,许多人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如“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屠守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吴征镒,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著名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唐敖庆、严志达、洪朝生、沈元、宋叔和、张炳熹、杨起、陈庆宣、申泮文,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力为、黄培云、李鹦鼎等。
1946年11月,胡适在西南联合大学9周年校庆纪念大会上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68天之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步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联大长征,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他们以天地做课堂,以人民做老师,到真实世界来学习、思考和做学问,成为接地气的书生。在他们身上,“刚毅坚卓”的联大校训卓然生辉。

-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 图片 | 视觉中国 」


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开白名单:duanyu_H
商务合作:[email protected]
内容合作、投稿交流:[email protected]
阅读原文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