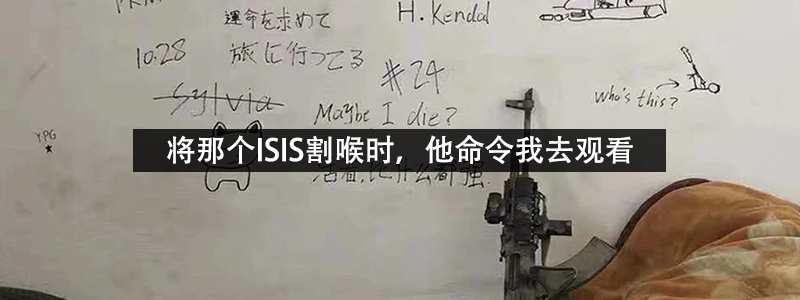我举报了那个作弊的北大学生


一
考场内,满是齐刷刷书写考卷的声音。
放眼望去,除了低头写字的学生们,还有桌上堆满的空咖啡罐。这是一门绩点分数不算高的学科,但对于我眼前的北大学生们来说,考试季中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是无比重要的。
2020年由于疫情关系,我所带班级的考试,全部都在返校后进行,本该8月份完成的考试季,由于返校的一再推迟被迫从8月底才陆续开始。这是考试季的倒数第二门考试,再坚持几天,长达两个月的考试季就要结束了。
考试季的疲惫写在了考场上时不时传来的哈欠声里,作为监考官的我踱步走在考场过道上。开考后约半小时,学生S举手示意想要上厕所,他坐在考场中间的倒数第三排,开考后他时不时地停下笔头,看起来卷子有些难。
看着学生S扬起的胳膊,我走过去,心里迟疑了一下,毕竟开考前他刚去过厕所。
“去吧”,我对他点头示意。
S匆匆跑向男厕,有些迫不及待的感觉。
过了10分钟,仍未见S回到座位,我走向男厕的门口,S匆忙走了出来,我看着S走回课桌,书写速度明显加快,我感觉有些不对劲,随后进入到了男厕蹲位。一个黑色的书包赫然挂在厕所内挂钩上,我深吸了一口气,战战兢兢地打开书包拉链。课本、考试复习资料、显示有着S姓名的临床实习记录本塞在了书包里。
“我终于抓到了”,我兴奋地拎着书包出了厕所,告知另一名监考老师刚才的经历。监考同事示意我不要惊扰考试,她继续监考。
同时我致电北大教务部门,告知了这一切。
就当我信心满满地以为抓到S作弊的证据之时,北大教务的老师告诉我,由于我并没有亲眼见证S在厕所内翻看考试相关资料,所以我的证据不足,不能以此作为S的舞弊证据。
那一刻,我气愤又失望。
眼前已经被我拿出厕所蹲位的黑色书包只能就此复位,考试时间到,S若无其事地离开了考场,第一时间走向厕所,取回了他的书包。
这一次,S顺利通过了考试。
二
抓住S作弊证据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这一切要从考试前的学生举报事件开始。
我所在的单位是北京大学的一所临床教学医院,按照北大的相关安排,S所在的专业在大三到大四期间,需要在我院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临床课程学习。2019年开始,我被安排接手我院的医学教育工作,也成了北大医学部的一名本科班主任。除了负责近90名学生的日常生活,还要负责他们的一切考试、学习安排。
进入考试季后不久,我就接到了两起学生举报,举报内容为,S在考试期间偷看他人的考试试卷;不久后我再次接到举报,举报内容为,S在考卷阅卷过程中篡改了自己的考试答案。
对于这些举报内容,我并无多少怀疑,因为就在进入考试季后不久,我意外接到了领导的一条询问短信,大意是S正在面试海外一所名校的研究生,但有一门考试的分数不够学校绩点,询问是否可能改动S的考试成绩。
“这个分数不可能改动,他的成绩距离他需要的绩点分数太远了,何况成绩我早就给了学校”,我几乎是有些发怒地对领导说。那种事情让人很愤懑,“就算是院长的儿子,我也不可能这么去改动成绩,这怎么对得起那些彻夜不归睡在教室复习的学生们?”我扭头对同事说。
第一次对S产生印象,是我前往北大医学部交接学生情况。“S,嗯,慢慢接触你就会懂的,一个比较难相处,很自我的学生。”学院老师们脸上一言难尽的表情,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开学后,我和班上每个同学进行视频谈话,S全程几乎不和我对视,期间还拒绝我的几次提问,他似乎迫切想要结束谈话,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我的问题。那种让我觉得丝毫没有得到尊重的感觉,甚至让我有些害怕起来。而那一次对话也让我开始明白学院老师们的评价。
自从第一次取证失败,坦言我有些想要放弃,毕竟我手握的证据,我认为足以将S定位作弊,书包是S的,里面也是S的相关书籍,“作为一个女老师,怎么可能入男厕所啊”,想到北大教务因为我未亲眼目击S翻看考试资料而认为证据不足时,这个理由让我有些难以接受。
事后,我将此事告知了我的领导A与领导B,领导A听后有些惊讶,他似乎从没想过S会是这样一名学生,“小心一点,S父母在我们单位有不少人脉关系”。“背后有人那又怎么样呢,已经不是第一次考试作弊了,我就是无法容忍”,我内心嘀咕。而领导B作为我的直系领导,他表示支持我再次取证,但一定要谨慎行事。
从考试季开始,我几乎每天傍晚下班都要去学生们的复习教室走一圈,学委告诉我,不少学生开始通宵复习不回宿舍了。其他人告诉我,S差不多晚上10点多就会返回宿舍,第二天一早来到教室翻看大家辛苦整理的考试笔记。
“不能放弃,S的行为是对那些辛苦复习的同学们的极大不公平”。我告诉我自己。学生们彻夜复习的画面像是一个打气筒,将我内心那个已经快要瘪掉的气球一点一点地鼓起来。
作为班主任,我需要定期向S所在的学院老师汇报班级的异常情况。对方说:“我们全力支持您取证,不过S比较固执,别让同学们与他起冲突,小心大家受伤,还是多先教育教育”。
过去两年,我带过近200名的学生。
在我屡次强调考试纪律,S仍然铤而走险;想到S修改考试成绩的行为是在他的家长的助力下时,我并不认为对于他,可以通过我那些简单的说教而实现教育的目的。比起对他进行教育,我认为只有进行一定的处分,才可能维护班级其它80多名同学的公平。何况是在北大这样的高校,学术端正更应该是业内的标杆。
三
“你们班上的同学对S的评价如何?”
在一次学生聚餐中,我问那些学生们。
J和几名同学相视一笑。
他说:“班上在每次奖学金评定时,其实一般同学,大家在互相评价时都不怎么扣分,但是对S,不论如何也要给他扣掉一些。”
“我们平时不怎么爱和他交往”,T随后补充。
在第一次取证后的近一周里,我找了不下十名同学谈话,了解S平日的情况:“偷拿老师的科研成果”、“小组讨论窃取他人成果”等。
S几乎没有多少正面的学生评价。
班上陆续有几名同学告诉我,S在过去的小组讨论中曾偷用其他小组成员的成果,并表态很支持我找到证据将S交给校方。自从第一次我信心十足地取证但仍失败后,我其实一直不确定我是否一定可以找到S作弊的证据。试图举证S的过程似乎像我过去跑过的马拉松,异常漫长、也充满艰难,但是我仍然不想放弃,除了我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同学告诉我,S的“罪证”不止如此,而且过去学院曾想对他进行处理,但是几乎没有办法。
上一次考试后便是N学科的考试,这是本学期考试季的最后一门考试,也意味着,这几乎是最后一次能抓住S的作弊证据的机会。
医学的考试,记忆内容颇多,自从难度最大的内科学拉开了划重点的序幕后,几乎每门考试,班委总会从我这里打探一些考试重点。
而在考试的前两日,学生W跑来告诉我,建议我不要再给大家划重点了,他说,不划重点,考试难度必然增大,那么S作弊的机会也就越大,越能够露出马脚, “虽然我很想要考试重点,但比起考试,我觉得抓住S更重要。”
一向有些嬉皮笑脸的W,似乎从没这么严肃过。我思考了些许,最终还是拒绝了晚上9点还蹲在办公室门外找我问考试重点的班委们。
那段日子,我每天都很忐忑。“老师,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就写联名信,不就是怕S背后有家庭撑腰受到报复吗,集体联名,写到北大BBS论坛上去,投给校长信箱,他总不能把我们所有班级同学都报复一遍吧”。W对我说。
很难想象,S和W成长在同一个班级,他们所在的专业在我们医院进行临床实习了24年,上一次联名信行动的发起,还是在大约20年前。
接触他们的这几年,我很欣赏北大学生身上的“自我意识”,总让人相信有人性自我崛起的一面,我想这是生而为北大人,该有的样子。
比起可能上北大BBS十大的舆论新闻,我更期待客观的证据,我不愿意解决S的问题只能采用舆论这最后一条途径。为了更加谨慎,我专门咨询了律师朋友,我们的监控只可在公共区域,也就是教室进行。而年初,为了教室安全性等考虑,医院特意在教室前后装了监控摄像头。考虑到大家的自觉性,那些摄像头一直用得不多,为了获得最佳证据,我将希望全部押在了教室内的监控上,给工程师致电了解监控设备使用,自费购买开通实时远程查看服务,考察监控环境,解决监控死角。
我不知道S是否一定会露出马脚,但我希望自己作为一名班主任,可以尽力而为。
四
最后一门N学科的考试是周二。
进入秋季的北京,天高气爽。
我对那天的印象很深,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除了努力,我还祈祷多一丝运气,如果可以拿到证据,我想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日礼物了。
那天上午8点半,N学科开考。我像往常一样提前10分钟到达考场,强调了考试记录。我观察到S像往常一样坐在中间的倒数第三排。
为了认真监考,我像对待高考考场一样,全程没有一丝分神。S除了偶尔看看后排的钟表,一直低着头。表面上看,他似乎没什么异常。我脑补过很多种可能的舞弊场景,去厕所翻看夹带,在衣服中的小抄,掏手机查看复习资料,这一切预计中的舞弊行为都没有发生。
眼看考试接近尾声,取证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S的异常动作,我最后一直站在最后一排,紧紧盯着他。
时间到,S交卷,归位,一切都很正常,突然,S拿起手上的口罩,左右环顾了一周,确认没人,快速用手指拿着口罩擦拭着桌面。
擦完之后,他一溜烟地跑了。
眼前的一切,我既害怕又兴奋。
我走向在场的另外一位监考老师X,她与我一起走到S的考试课桌,作为授课教师,她亲口告诉我,虽然字迹被擦拭模糊,但仍可以辨认,那就是N学科考试的相关内容。我快速打开手机查看监控录像,S拿着口罩擦拭桌面字迹的关键画面被全程记录下来,而且开考前的一小时,监控记录了S在桌面抄小抄的过程。
我长嘘一口气,我终于做到了。
从考场回办公室,我将此事告知了其他同事,“咱们学院有处分过学生吗”,我问同事Y,“没有过,北大的同学考试一向很自觉,真是没想到”,Y唏嘘不已。“一个学生,算了呗,干嘛那么计较”,同事M说。“这已经是三番五次被举报,而且还一直舞弊,这件事情真的是太过分了,我无法坐视不管”,我反驳道。
当日,我将此事如实告知我的两位主管领导,领导B提醒我,让我赶紧联系另外一个监考教师X,找她签署一份字迹确认书,同时让我拷贝监控视频,做好资料整理让其过目。
我也第一时间告知了S所在的学院,校方一直询问我是否整理好了材料。为了更严谨,我再次确认所有的文字材料说明以及监控材料。
盯着监控视频缓慢上传,我既兴奋又紧张。
领导B嘱咐我,既然我踏出了这一步,就要想好后果,很多年前,他曾因为医疗官司去过法院,那是一个冗长而烦人的过程。他说,按照S的行为,整个事情一定不会简单地收场,S的母亲是北京的一所高校教师,父亲是一家图书出版公司的总编辑,S高中毕业于北京的市重点,这种高知家庭是难以接受这种利益损害的,他一再叮嘱我,要做好心理准备。
邮件附件上传结束,我按下发送键,“一切评判就交给学校吧”,我长叹了一口气。
五
事件发生大约一周后,S所在的学院告诉我,他们已经在跟进此事,并且特意通知我,在处分下达之前,需要找S进行一次谈话。
谈话的前一天,我告知S在教学楼等我,当日上午9点,北大相关学院的主管同事带着电脑进入我们的谈话会议室。谈话时间到,我招呼S进入教学楼,S从另外一个教室出来,手里拿着一箱牛奶,他似乎是打算找我私聊一些事情。
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看到我也没抬头,挥手说了一声“嗨”,然后往前走。当S见到会议室内等候的两位学院老师时,似乎有些惊讶。
该如何开始这个谈话呢,毕竟我从来没有进行过处分前的谈话,直接坦言自己的证据,还是如何目击了现场,还是……我内心焦躁不已。
“S,N学科考试是哪天进行的,你还记得吗?”正在我思考如何开始,S学院的主管同事D不慌不忙地开口问到,一边在电脑上记录。
“就上周吧,没多久,发生什么事了么?”
这时的S觉察到有些不对劲。
我们随后谈到考试现场发现的字迹,S表示是自己考前涂写,考后试图擦拭而没有擦拭干净。对于S的回答,我并不意外。另外一位在场的同事Z拿着北大学生管理手册,开始强调考试作弊处分。S之后不断重复桌面字迹是自己考前练习时涂写,考试后为了避免监考老师怀疑作弊,所以没有告知我们桌面的字迹现象。
谈话进行了不到半小时,S表示自己势单力薄,需要寻找家长帮忙,就急急忙忙地拿着手机走出会议室给父母打电话。之后他告诉我们,父母马上赶到医院,并且表示自己早晨还没有吃饭,要去购买早餐,需要暂停谈话。
四十分钟,S的父母赶到了会议室。
S的父亲,头发有一些发白,笔直的腰杆,立领的大衣,眉头一直皱着,看起来是位领导。S母亲的装扮相对朴素一些,话语不算强硬,谈话间他们一直强调S在家也喜欢在桌面涂涂画画,S其实一直很努力,我们有些误解了S。
而在S父母赶到后,S要求我们的谈话录音重新进行录制,虽然我们一再强调录音是为了方便记录并不作为断定作弊的客观证据。重启录音后,他多次表示自己拿过北大挑战杯特等奖,一等奖学金等个人荣誉,S说话时,多次遭到他父亲打断,他示意S不要再继续说了,皱着眉头的他似乎在寻找解决办法说服我们几位。
这是举证事件发生后,我们第一次,也是我唯一一次在场与S进行的谈话。
在那之后,北大表示他们会继续跟进这件事,S的学院偶尔会打听一些S在医院的实习表现,以及告知我一些大致进展。我从一些途径听说,S在事后给学院院长等写了不少信,说自己错了,为自己辩驳的同时也是在寻求同情。
那段时间,我也不好过。
S的事件还在持续调查中,当我告知我的父母,我已经举证了S的舞弊事实时,母亲说,如果学校问我的处罚态度,她劝我去对学校建议,做简单处理;父亲则强调,S背后有家庭关系背景,不要做得罪人的事,避免引火上身。
我的先生在知晓此事后,一直很坚定地支持我合法取证,让S的处分下达,他认为家庭的背后权力不能成为他猖狂的理由。我告诉我的大学导师我面对的处境,他说:“人都有各自利益判断,不用在意,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听到大学老师的这句话,我似乎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之后,我拒绝了父母的建议,想到那些为了考试彻夜通宵的学生,以及S的“劣迹”,我不愿意让我的学生们冲在前面。如果我不做些什么,我发现自己无法面对内心的良知。
2021年1月初,S所在的班级就要离开我们医院,返回北大医学部了。他们离开的前一日,北大校方告诉我,S的处分书下达了。
虽然S一再不愿意接受,最后还是在领取处分书上签了字。
那时距离S作弊事件的发生足足有2个月。
北京那阵子已经进入寒冬,听到这个消息的我特别开心,嘎吱嘎吱踩着路面的小碎冰,一路小跑,掏出手机,致电了我的领导B,电话这头我兴奋地说,“北大终于下处分了”。
然而处分下达后,S有10天左右的申诉期。
就在处分下达后不久,S所在的班级已经全部结束了在我院学习的课程,离开了我院。
在他们离院后不到一周,N学科考试的另外一位监考老师X告诉我,S穿着白大衣,利用手中还未消磁的门禁卡,来到病房找到她,要求她写下当日桌面考试字迹与考试内容无关的确认书,而且声称北大已放弃追究他的舞弊处分,同时提到整个事件是我在违规处理。
同事X还告诉我,S连续来到病房找了她两次,每次来都是拿着手机录音与录像,他似乎在寻找申诉的突破口,但她已经明确拒绝了S的不合理要求,并且坦言,如果写下当日桌面字迹与考试内容无关,简直就是打自己的脸。
过了几日,北大校方通知我,S已经向北大申诉委员会提交了他的申诉材料,开篇提到了考试当日是在我的强硬态度下,监考老师X才签下的考场记录。他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我。
我坐在电脑前,滑动鼠标,整整12页的辩驳,完全出自律师之手,“态度强硬,监考老师被迫签下考场记录”“刻意向校方隐瞒实情”“假借公权”“以欺诈的不正当手段,获取证据材料”,这些控诉我的字眼锐利,像是一把把刀子割在我心上。我一阵阵哆嗦,看着那些控诉字眼,我害怕得眼泪在眼眶打转,“你要坚强,不能退缩,你要勇敢”,我一直在心里默念。
后来,北大校方正式通知我,我需要前往北大的新太阳学生中心,参加S的申诉会。
担任北大班主任的两年,我前往北大参加过不少会议,但我从未如此紧张、忐忑过。“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他一定会想办法进行申辩的,而且会对你进行人身攻击,但你不要害怕,证据都是完整、客观的”,领导B安慰我。
其实,在S事件发生后,医院的同事、北大同行、家人都提醒过我,要保护好自己,小心报复。为了防止申诉会前可能遇到的意外,我将所有的证据全部采用电子传送方式给相关部门留存了一份备份,并且面对申诉控诉点,再次撰写了数千字的事实陈述材料,防止意外发生时,我不能到达现场进行材料陈述与提供。
S所在学院的同事也告诉我,十年前,曾经因为一名学生的退学事件,最后上诉到了法院,如果S坚持上诉,这可能是最坏的打算。
听证会这天,我提前到达会议候场区,校方告诉我说,看到申诉材料中对我的指责,本不想让我出席,担心我的个人安全。
我说我应当出席,因为我是第一当事人。当天还有其他听证会议,S事件的听证议题安排在第二个,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后,工作人员告诉我,我们可以进入会场进行事实陈述了。
会场内坐满了各方教师及学生代表,作为S事件的第一当事人,我陈述了我在我们医院处经历过的一切,看着申诉材料上并不真实的字迹确认材料,以及S声称考试桌面的字迹是其写下的圣经内容时,我发现我没有那么紧张了。
我经历的一切都是真实、客观发生的,
我没什么好怕S的。
听证会进行得很快,陈述完后,委员会对我的证据没有提出疑问,大家提了一些细节问题,我按照手里的客观材料也如实做了回答。
走出北大新太阳学生中心已近中午,我如释重负,看着眼前穿梭不息的学生们和头顶的太阳,我觉得北大校园从没如此明媚过。S学院的同事告诉我,如果申诉驳回,S可以继续申诉,下一步可以到达北京市教委,最后是法院。
我掏出手机,给先生打了电话,“结束了,我们这一次应该是赢了”,那一刻,我有些想哭,想着跨越重重困难进行举证,从接到申诉材料到举办听证会,我几乎每一天都很忐忑和害怕,特别是我脑海中浮现那些指责我的字眼。
当日下午,北大校方就来了通知。
校方坚持对S的作弊处分。
我知道S可能会继续上诉,但我告诉自己,坚持最初的那份信仰,做好配合学校进行下一步工作的准备,不论整个过程多漫长,自始至终,我不后悔按下那封举报邮件的发送键。
撰文 | 晴梓
编辑 | 蒲末释
▼
每周一三五 晚九点更新
也许你还想看
全民故事计划正在寻找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讲出你在乎的故事,投稿给
故事一经发布,将奉上1000元-3000元的稿酬

↙↙↙也可点击“阅读原文”,直接讲故事
阅读原文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