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住房到防御空间:建筑设计能解决社会问题吗?
平均阅读时长为 35分钟


和美国的环境大有不同,中国有着西方人难以想象的高密度和极速的城市扩张,不断造成着既非中心城市也非郊区乡镇的独特景观。这似乎是一种天然的、无法应用精英的建筑教条的环境——正如文中二十世纪初期的纽约,建筑在这里,正在同政治和社会问题纠葛着走向歧路。
作者 | 郑时翔
编辑 | 徐旭

乌托邦是黑色的
HBO在2015年播出的政治迷你剧《黑色乌托邦》(Show Me a Hero)由一本纪实小说改编。故事讲述了1987年,纽约扬克斯(Yonkers)市受到全国有色人种协会(NAACP)提起的诉讼,被司法部强制执行建造反种族隔离(desegregation)的公共住房(public housing)的历史事件。

▲《黑色乌托邦》海报
在美国,一个城市中的不同县、甚至同一县的不同街区都可能有着相当大的贫富差距。这种差距在八十年代更为显著。这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政府提供的老式公房一般都聚集在一个或几个连续的街区;并为了加大安置家庭的数量,通常采用中高层公寓的形制。这种方式从城市规划角度看显然十分高效,但却非常容易造成这个区域内部的衰退(urban decay)。故事中被要求整改的韦斯特切斯特县(Westchester County)就十分典型——老旧的高层楼房、残破的基础设施、遍地垃圾;居民生活质量极低:他们多为非裔或拉丁裔,很多人整日无所事事,整个街区充斥着毒品、卖淫、斗殴、和偷窃抢劫。

▲1965年纽约哈莱姆区的黑人公共住宅区。当时还未实行反种族隔离法,该区住的都是黑人居民
提起诉讼后,韦斯特切斯特县被强制整改,200户居民被要求迁出。当时负责主审的联邦法官要求杨克斯市采用较为新颖的“分散式选址”(scattered-site public housing,即SSPH)进行公屋建造。这种方式要求将这些公共住房建造在东部中产阶级的街区里,通过融入中产社区的方式达成文化共享、消除种族隔离。
这一切听着都是好事,但故事最为“美式”也最具戏剧性的部分就在这里:中产阶级民众自发组织的“救扬联盟”(Save Yonkers Federation)强烈反对联邦法院的整改案。他们游行示威、表达不愿意让社会底层人员入驻自己的社区。他们认为这些迁入者会带来原来社区的习气,对他们优质的社区造成冲击、产生混乱。

▲“救扬联盟”游行的照片,左边的抗议者手中的牌子写着“我们不是NAACP的孩子”
刚好时值市长选举,故事的主角、扬克斯市议员尼克·瓦西斯科(Nick Wasicsko,即海报上的人物)发表宣言,一定会代表民众积极上诉、阻止计划进行,因而大获民心,成为了纽约州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市长。
然而事情并不像尼克想象得那么顺利。尼克领导的上诉被认为理由不够充分,计划继续强制执行。由于上诉过程拖延了时间,联邦法院要求,如果扬克斯市继续不执行计划,会被判定藐视法庭(contempt),处以巨额罚款:从第一天罚款$100开始,每日加倍。扬克斯将在第22天全面破产,届时全市将没有警察、消防员、自来水,以及一切公共服务。民意和联邦旨意在这里剧烈冲突,尼克成了左右为难的角色。罚款开始没多久,他向上级妥协,在公众巨大压力下支持推进公房建设,同时也失去了整个市的支持。

▲右为尼克·瓦西斯科。照片左边是政治家特伦斯·泽拉斯基(Terence M. Zaleski),尼克当时的竞争对手,泽拉斯基当选市长后,瓦西斯科因仕途无望,在父亲墓前吞枪自杀
这显然是一个关于政治牺牲者的故事,但剧情也揭露了城市中不同居住空间的冲突和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有着复杂的成因:缘起于阶级、种族,外显在生活方式和公共秩序上,最终演化成了政治抉择的左右为难和公共项目推进的步履维艰。
但在这一团乱麻中,我们不妨思考,建筑师作为公共住房的项目的执行者之一,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能发挥什么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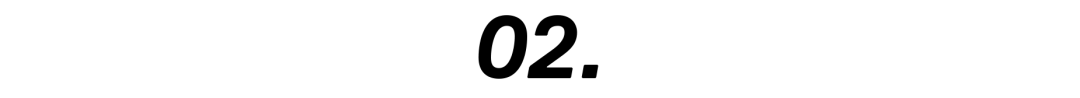
什么导致了现代建筑之死?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美国政府就开始介入贫民窟的整治。摄影记者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在1890年的影集《另一半人如何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记录了纽约贫民窟里的悲惨生活,并在当时引起全国对住房情况的关注。

▲《另一半人如何生活》中的一张摄影作品
然而,早期的住房改革企图用新的管理模式和设计规范(Building Code)来解决贫民窟的物质缺乏和因此产生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有点南辕北辙的意味。直到1910年,国家住房协会(National Housing Association,即NHA)成立,焦点才从单体建筑的规范转移到更大尺度的区域规划发展上去。接着,1949年住房法案(Housing Act of 1949)出台,加大了联邦政府对公共和私有住房的管控,同时扩大了政府在清理贫民窟方面权力和资金,并推行城市更新计划(Urban Redevelopment,后住房法案修订,改称Urban Renewal)。
这个如今仍有耳闻的概念,在当时的实行并不尽人意。因为对很多城市来说,城市更新过分专注于消除衰败,但没有好好设想如何建造新住房的任务。比如,在住房法案通过后的十年间,42.5万套住房被拆除,但新建造的仅12.5万套;许多贫穷的街区被连根拔除,让位给交通建设和现代主义风格的楼房,这种形式往往以柯布西耶首创的“公园中的塔楼”(towers in the park)样式出现:将塔楼安置在离人行道较远处,楼周围作为停车场、草坪、和景观带。塔楼通常是长方形或十字形的平面,除了砖饰面或简洁的立面外毫无装饰。

▲史岱文森镇(Stuyvesant Town)是美国纽约曼哈顿东区的一座大型私人社区,始建于1943年,典型的“公园中的塔楼”样式

▲史岱文森镇,近景
无独有偶,试图用建筑和景观设计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结果往往都不理想;政府的好意也经常造成难以预料的现实困境。“公园中的塔楼”是柯布在践行“光辉城市”(Ville Radieuse)理念时的实验,试图通过疏松城市网格、增加绿色空间的方式,找寻摆脱城市积垢和过度拥挤困境的策略。而事实是,在更为深层的社会问题面前,建筑手法的作用犹如杯水车薪——建筑师的美好设想往往基于对隐秘而关键问题的视而不见,因此宏大的理想会在盲目中进退失据。
比如,由山崎实(Minoru Yamazaki)设计,位于圣路易斯市恶名昭著的普鲁伊特-伊戈社区(Pruitt–Igoe)就是一个反面典型。建成于1956年,却在短短数年间迅速衰落。贫困、犯罪、种族冲突在其中肆虐;设计师刻意安排的公共空间,包括空中连廊、公共大厅和周围的公园绿地,成了帮派分子聚众斗殴、进行非法交易的场所。后期住房空置率极高,外墙失修破败,建筑设备也大量损坏,最后不得不在1972年将33幢楼全数爆破拆除。普鲁伊特-伊戈项目成了美国城市更新计划失败的缩影。

▲1972年4月,“普鲁伊特-伊戈”爆破拆除过程由电视台直播
甚至,后现代主义的推崇者,建筑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趁机在1977年的著作《后现代建筑语言》(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中宣布普鲁伊特-伊戈的爆破意味着“现代建筑已死”。(虽然他在几年后承认自己这么写是为造成“戏剧效果”)现代主义英雄式的理想在公共主房建设上的破灭,印证了简·雅各布(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提到的传统城市的危机。“好意的都市主义”着眼在为人们创造宽阔的绿色空间和优美的步道,但却天真地忽视了城市中的积疾。
一地鸡毛地来到八十年代,民众对公共住房的不满有增无减,政府和城市开发商开始寻找其他形式的低收入住房。于是,《黑色乌托邦》中提到的分散式选址项目应运而生,旨在将较小规模、更好地整合的公共住房单元,例如联排别墅(townhouse)、低层无电梯的公寓(walk-up),安置在现况良好的社区内,试图用优质的社区环境同化这些来自于较为落后区域的人口。

防御空间
开篇在讲述《黑色乌托邦》故事中提过,分散式选址并非一举解决了所有疑难杂症,种族歧视和阶级分化显然是社会结构性问题,因此新成员的加入必然引发原社区的震荡和排异。社区成员除了担心所在社区房价下降,最为担心他们的出现将造成社区犯罪率的上升,因而一度出现原社区居民因为害怕而搬离的情况,这种现象在当时被戏称为“白人逃亡”(white flight)。
各有所短的公共住房计划,与其说需要探索一个“完美”方案,倒不如说亟待整合出一套客观的理论体系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这时便需要提及规划师兼建筑设计师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有趣的是,他在这部迷你剧中也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角色,作为联邦政府聘请的设计顾问来到扬克斯市调查。

▲截图自《黑色乌托邦》片尾,左为角色,右为奥斯卡·纽曼照片
纽曼为人熟知是因为他1972年的著作《防御空间》(Defensible Space),书中提出了关于建筑和环境设计帮助预防犯罪和保障社区安全的理论。通过研究纽约住房部提供的数据,纽曼在开篇提出了最为核心的观点:相较于低矮的独栋住宅或连体住宅,高层公寓楼会造成更高的犯罪率。这是因为楼房内人数多,居民对楼内公共空间没有责任感,而这些空间又相对封闭,条件较差的廉租公寓也没有摄像头和安保人员,因而成为了犯罪的温床;与之相对,独栋住宅或连体住宅的前后区域都会被住户自发地认为是属于自己的空间,因此他们对社区更大的范围拥有归属感和领地意识(Territoriality)。

▲《创造防御空间的设计准则》(Design Guidelines for Creating Defensible Space)是纽曼继《防御空间》后,在1976年出的修改版。1996年他还为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编写过名为《创造防御空间》(Creating Defensible Space)的手册。
防御空间由五个主要因素构成,除了已经提及的领地性,还包括自然监视(Natural Surveillance,居民能够较为容易地观察住宅周围在发生的事),印象(Image,在住宅及周围设置产生安全感的象征性要素),周围环境(Milieu,可能影响安全性的周边特征,例如靠近警察局或繁忙的商业区)和安全的毗连区(Safe Adjoining Areas,提高周围区域的安全设计标准)。
仔细阅读《防御空间》一书,我们会发现纽曼并非空口大话。在这些总结性的理论指引下,他其实将设计手法描述得非常具体。例如书中提到在住宅入口处设置矮墙来暗示公共和半公共区域的分隔、在正门旁设计较大开窗来让住户和路人观察到室内外的情况等。更加重要的是,他提出的设计手法除了想要真实地降低犯罪率同时,还试图通过犯罪学和环境心理学的方式(例如“旁观者效应”和“破窗理论”)让居民在心理上获得安全感。这在当时的确成为了行之有效的设计策略。

▲摘自《防御空间》的分析图,表述了纽曼强调划分公共、半公共区域,并让私人区域对公共区域提供监视作用。

▲摘自《创造防御空间》的插图,讲述了单体建筑和联排别墅拥有半公共空间因而产生自然监视,高层公寓的走廊共同属于过多的住户,因此也是公共空间,并成为无归属感的危险区域。
直至今日,美国的住房设计仍受防御空间理论的影响,它也启发了“犯罪预防环境设计”(crime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即CPTED)的学说。这个新学说的内容经过长期发展,在纽曼理论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电子监控、门禁系统等新时代的内容,但其基本框架并未跳脱纽曼的设定。
同中国较多的封闭式小区和二十四小时安保不同,美国的住宅在强调开放性同时希望借助邻里之间的照应和社区印象来减少抢劫、偷窃等犯罪行为。而这些策略同防御空间和CPTED理论息息相关。“当一个区域中处处都有所属并有人负责照顾时,罪犯会被隔离,因为他的地盘没了”,纽曼这样解释自己的防御空间理论。
对纽曼的理论的批判并非没有。例如有评论指出,所谓的领地性和空间责任感在帮助减少犯罪率的同时,也会加大居民对犯罪行为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也许反而造成住户对邻里关系的质疑;另一个观点是,纽曼使用的心理学模型会在不断进行的社会变革中会变得不适用:如何提取一个更有概括性的模型?社会科学尚且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产生和收集证据,建筑师和管理者对其应用却操之过急。

什么都做不了的建筑师
显然,纽曼并未逃脱用建筑手法解决社会议题时面临的捉襟见肘。那么,建筑师对社会问题能做什么吗?自然灾难、社会不平等、资源枯竭和“新冠”,建筑师能做的,似乎什么都没有;他们能做的往往只是成为权力、资本的表达手段和执行方式。从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到库哈斯(Rem Koolhaas),那些著名的建筑师和评论家都认为建筑对于人的社会内涵毫无助益。不同之处在于塔夫里认为由此带来的异化(alienation)是悲观和不可避免的;而对于库哈斯而言,城市的本质就是“偶发”(chance-like)的,所以城市学不应该追求某一种既定的类型(typology)。

▲瓦赞规划(Plan Voisin)是一个巴黎市中心重新开发计划。于1952由柯布西耶提出,用十八座十字形平面的塔楼代替原有城市,是“光辉城市”理念的最佳展示之一。
或许,纽曼早已先见地看到这种社会问题导致的城市压力而产生不确定性,因此他不曾考量英雄的现代主义提出的“巨构式”策略,转而用极为细腻的手法去试图缝合城市中不断涌现的伤口。这使得当时过度精英化的建筑和城市理论,在另一个侧面多少能够成为一种为大众青睐的“政治偏方”。
同时,某种“建筑学式的自信”在纽曼身上也有体现。比如,在《黑色乌托邦》中有一幕,迫于“分散式选址”选出的其中一个社区反抗团体的巨大压力(这是一个宗教社区),扬克斯的议员们纷纷希望放弃该地点,将原本应该分散到8处的方案改为分散到7处。这受到了纽曼的严词拒绝。他搬出了自己防御空间的理论,告诉议员,他的调查数据表明,加大这些区域住房的密度会有犯罪率上升的风险。“你们究竟是只想建造这些房子,还是希望这个公屋项目真正成功?”他如此质问政治家们。
这种观法或许能成为我们思考建筑学对社会问题意义的一个陡峭但坚实的角度:纵然对大部分社会问题,建筑学一筹莫展,但在完成项目时,我们会实实在在地参与进政治活动和城市建设中。即使政策本身和资本走向已然决定了大方向,但当物质化(materialization)的过程开始、建筑学介入时,建筑师不得不用关切的心态、专业的自信,去试图用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解决问题。
如今,早已成气候的国内“快销”商品房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建筑学的无力感。高周转和模式化的生产方式压得建筑师无暇思考设计细节;同时,令一些开发商如痴如醉的、具有摧毁性的大规模建设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显而易见。和美国的环境大有不同,中国有着西方人难以想象的高密度和极速的城市扩张,不断造成着既非中心城市也非郊区乡镇的独特景观。这似乎是一种天然的、无法应用精英的建筑教条的环境——正如文中二十世纪初期的纽约,建筑在这里,正在同政治和社会问题纠葛着走向歧路。

▲张克纯摄影作品,《山水之间》
看似毫无可为的建筑师,似乎只有先踏入这样的歧路,才能真正反思自己的职业,并踩出一条新道。毕竟,丢失的已经来不及回味,宣言也来不及发表,似乎只有在不断增生的现实里颠簸才能达成这个时代真正的先锋性——也许建筑师什么也解决不了,但如果什么都不做,便会成为历史洪流中毫无紧要的背景音符。
| 参考资料 |
1. Jacob Rii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1890.
2. Bauman, John F.; Biles, Roger, eds. From Tenements to the Taylor Homes: In Search of an Urban Housing Polic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2000
3. Hays, R. Alle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Urban Housing: Ideology and Change in Public Policy. 1995
4.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1992
5. Charles Jencks. 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 1991
6. Oscar Newman. Creating Defensible Space. 1996
7. Oscar Newman. Community of Interest. 1981
8. Joy Knoblauch. Defensible Space and the Open Society. Aggregate, Volume 2, March 2015.
9. Rem Koolhaas. Delirious New York. 1978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同名原文发表于作者知乎。
| End |
| 文章作者 |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