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打工男孩,走进硅胶娃娃体验馆|谷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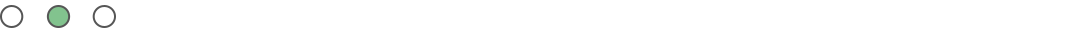
撰文丨吴呈杰
编辑丨张瑞
摄影丨冯海泳(像素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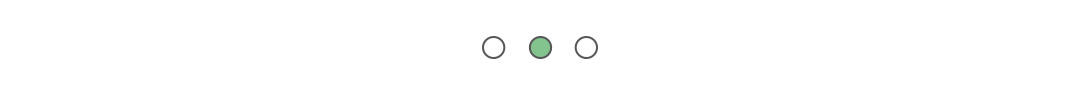
那些普普通通的男人
晚上9点,卞小飞送完了这天的最后一单外卖,到家脱下骑手服,刮了胡子,换上衬衫和牛仔裤(衬衫因常年叠放而布满恼人的褶印)。他再次跨上电动车,骑了15公里,来到他的目的地“爱爱乐体验馆”附近。出于一种他羞于表述的胆怯心理,他在街口的宠物店停了下来,假装端详了一会儿玻璃窗里那只胖乎乎的小博美,随后拨通了“爱爱乐体验馆”老板李博的电话。
半个月前,卞小飞在短视频上听一个大哥“教你怎么创业”。大哥顺口提到,在深圳的北缘、距离富士康观澜园区不到1公里的地方,开了全国第一家硅胶娃娃体验馆,取名“爱爱乐”。花上188元,就能拥有硅胶娃娃1小时。
卞小飞跟着老板李博走进“爱爱乐”。卞小飞长手长脚的,猫着腰进来的样子像上课铃响后才溜进教室的后排男生。他爬上霓虹灯带缠绕的旋转楼梯,二楼灯光昏暗,7个房门大开,光彩各异,7个硅胶娃娃正对房门,各坐在一张蹦床似的圆形弹簧床上。娃娃有的娇小,有的高挑,几乎都是大胸细腰,衣着轻薄,长了一张时兴的锐利脸孔;摸上去软软滑滑的,但又失了几分温度。房间里别无他物,粗大的水管悬于头顶,穿墙而过。后来卞小飞说,他当时脑袋嗡嗡的,来不及思考,胡乱指了房间靠里的一个。
45分钟后,卞小飞走出房间,鼻尖沁出了汗。李博邀他坐下喝茶,他小幅度地收束双腿。“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担心别人说什么。”李博递上一根烟,他爱笑,性格和脑袋一样圆圆的。
“有点,第一次有点。”卞小飞的肩膀松了下来。
“放开!”李博说,“为什么要放开?不违背法律,不违背道德,去搞真人,他妈违背法律,又违背道德,两个成鲜明的对比,是不是?正确地坦然面对。”
作为新生事物,硅胶娃娃体验馆仍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卢义杰认为,硅胶娃娃体验馆没有刑法层面的风险。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亮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硅胶娃娃体验馆的经营范围能否得到工商部门的许可仍有待观察,现在还没有一部明确的禁止性法律来规定其行为。西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张飞舟则认为可能在挑战公序良俗,“新生事物出现之后,过段时间可能会有新的道德标准,但在转换过程中是否合法还是有争论的”。这两年类似体验馆在各个城市源源冒出,其中一些又被陆续关停。前段时间,为了不触犯传播淫秽物品罪,李博将娃娃身上的声音开关撤去。

李博和“爱爱乐体验馆”
3年前,我曾拜访过一家硅胶娃娃工厂。工厂经理梳个大背头,指着面前挂着的一排排裸体娃娃说,这些娃娃售价都要上万,能定制面孔、身材和下体,每个都有个护士、空姐或是车模的“人设”。他们最新的研发方向是“智能的科技仿真人”。顾客通常财力雄厚,有的在客厅堆满高达模型,有的专门租个房安置娃娃。
看到“爱爱乐”的新闻,我想起了3年前的工厂之行。如果说定制硅胶娃娃是男人幻想的专属供应商,那“爱爱乐”简直就是性的共享经济。和那家工厂的娃娃相比,“爱爱乐”的娃娃没有名字、没有身份,如同工业流水线的产品,第一眼望过去,很难分出差别。“谈不上什么性幻想,”老板李博解释说,“因为我们的客户群体就是急需和必须的一个群体”。
第一次走进“爱爱乐”,会被一种说不上来的压抑氛围笼罩。后来我反应过来,是因为太安静了。大堂的水族箱里,一条硕大的清道夫鱼有时酣睡,有时幽灵般漫游。男人们用口罩将脸挡得严实,沉默地进来,沉默地出去。“爱爱乐”最火爆的时候,李博说,楼梯和大堂坐满等位的人,他们各自低头玩手机,只有头顶传来此起彼伏的、床脚和地板碰撞的声音。
我在“爱爱乐”的大堂坐了5天,和30多个男人交谈。有同宿舍的6个工人合资买过一个280块的最便宜的充气娃娃,轮流使用;也有在富士康打工3年,仍未凑够四分之一彩礼的渴婚之人;还有每月赚5000块,2000块寄回家,2000块寄给上大学的儿子,剩下的,除了烟钱,只够来一次“爱爱乐”的保安大哥。
“你到深圳的街上看看,全是单身男性在外面,”一个客人瞟了一眼“爱爱乐”的门外,“有钱的富二代他们开个跑车还会撩一些女人,像普普通通的那些——他们上哪里找?”他眼里的困惑很真诚。

晚上11点,深圳街头的年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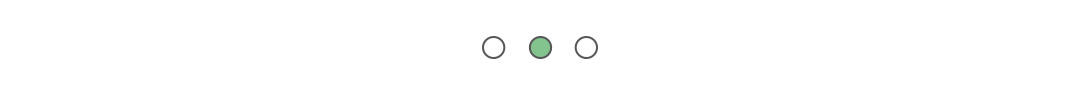
一些居无定所的人
34岁的湖北人李博先后创业三次,比萨店、手机店、中介公司,也失败三次。比萨店倒闭的时候,连转手都转不出去。等到2018年春天,合伙开公司的朋友卖了公司的车跑了,办公室房租交不起,全套家具家电都抵了进去,信用卡一天天发来逾期短信。妻子给他两套方案,回老家,或者回厂里打工,李博“不愿意接受这种现实”。他每天坐公交出去乱转,有天晚上坐到了富士康旁边,他爬上天桥,看到底下熙熙攘攘的人头,全是男的。
他想起来,自己小学毕业出门打工,一个宿舍住十五六人。一层楼只有一间厕所,老板把水管关掉,大便池一天冲一次,“手淫都没地方”。有天熄灯后,一个工友忽然拉开灯,把旁边男孩的被子掀开。李博看到,这个只比他大一岁的男孩的裤子褪了一半,手还呆呆地停在裆部。从此熄灯后,13岁的李博就借窗外月光,观察又有哪几床被子在上下耸动。
近20年后,站在天桥上,李博嗅到了欲望的气息,也嗅到了商机。他登上电商网站,看到硅胶娃娃单价大多上万,关注度很高,但成交量很小。他想,不如开一家硅胶娃娃体验馆,就开在富士康旁边,瞄准底层打工者的性需求。他在夜色中走回家,感到体内重又涨满年少时的激情。他没察觉自己走了整整20多公里。
妻子说他“死不正经”。上百个借款电话里,他“不敢说数,他能借多少给我,我都急需”。最初五个朋友投资,后三人退出,两人改为借款。没钱装修,他扛来水泥,砌了100天。第一批硅胶娃娃到店,他亲自试了个遍。开业那天,没有朋友到场,他独自搬了个沙发坐在外面。这是2018年的夏天。

李博
“走,带你逛一圈。”李博骑上电动车,载我在楼与楼之间穿行。正是下班高峰,电动车的车流涨了又退。没有落日,晚霞散淡,天空被城市切得破碎。偶尔能看到飞机。至少在车上的这一刻是自由的,亚热带的季风源源不断地经过我们。
“爱爱乐”收留过一些居无定所的人。第一个店员是前保安老蒋,老蒋本是来消费的,下了楼,对李博说,我刚失业,来您这儿上班吧。干了几个月,他常溜去对面的麻将馆赌钱,欠了老板娘几千块,跑了。有一个叫小龙的,在深圳最热的时候,他穿了件长袖来,没有行李,浑身散发酸臭。领到半个月工资后,他也跑了,还顺走了李博一台平板电脑。
之后是杨姐,写得一手好字,据她自己说,她是1970年代的大学生,因故被关进精神病院,出院后便在深圳流浪。李博留她下来做饭,手艺一般,能把饭做熟的水平。她偶尔发病,对着墙壁不停歇地骂下去。
一个店员临走时,对李博说,你这里好像是个难民营。
“不是他们本身的错,和他们从小的家庭环境、生活环境都息息相关的。”李博理解他们,也明白流浪的感觉,“有个地方躺下就已经很好了”。他失业过几个月,实在没钱,只能在广场上找张长椅睡。
他进过鞋厂,鞋面刷了胶从烤箱里出来,要用手往上按鞋底。高温下,手指排排起泡,要过十天——这十天里连筷子也没法拿——等上面一层皮脱完,起了老茧,他们才算是过关了,是个合格的螺丝钉了。
有次李博从福建的鞋厂离开,左手拎个桶,右手提个食品袋,再背了几件衣服。他到楼下便利店买瓶水,当地老板冲他冷笑,这就是你全部家当吧?
深圳不一样。以前,人们叫他打工仔,来到深圳,人们叫他靓仔。他是深圳的儿子。深圳人人都是外地人,于是人人平等了。
“不要歧视任何一个来‘爱爱乐’的客人”,李博教育店员们,“从他下楼的那一刻开始,我的烟已经递上去了,我的眼睛是看着他,不是假装的和蔼,不是强颜欢笑的和蔼,是眼神都要给他的和蔼。”李博看着来“爱爱乐”的男人们,像临水照见年轻时的自己。
“爱爱乐”来过一个瘸腿的男人。李博将他扶上楼梯,进房间享受属于你的东西吧,李博说。下了楼,男人握住了李博的手,说,我这半辈子没找到过这种尊严。他后来又来了一次。

顾客离开以后,员工重新整理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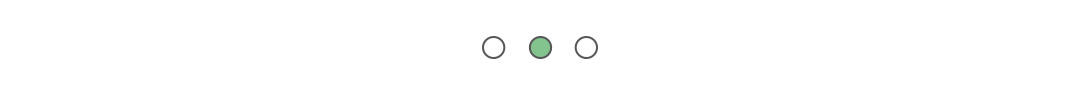
浪漫的权利
来“爱爱乐体验馆”之前,生性害羞的卞小飞其实用过三四个交友软件,都得充钱才能开启聊天。聊上了,对面也是一上来就要钱,裸聊200块,上门1400。他那时还不知道,聊天框另一侧的“小姐姐”多为敲诈团队,他们播放下载好的色情视频,诱导男人们脱下裤子,同时悄悄录像——敲诈男人交更多钱,或者将录像传至互联网。卞小飞退却的理由是,“她”只愿发来精修图,“照片都是照骗,都P图的”,他稀里糊涂地逃过一劫。
没要钱的,他只撞上过一次。凌晨两点,他给女孩发去自己的照片,正索要她的,女孩说,不如我们现在见一面?起初卞小飞担心是仙人跳,但他想到“自己什么也没有,死就死了”,横下心,电动车骑了十几公里到她家。
进门前,卞小飞特地给女孩买了一瓶水。他记得她家有大片大片的粉色,挺漂亮。
两人一起坐在沙发上,他右手点烟,左手慢慢搭到她肩上,小臂不自觉地抖了起来。
“你紧张吗?”女孩问。
“我紧张。”他如实回答。
“我有点胖。”女孩说。
“我不觉得你胖。”他连忙说,这话是真心实意。
如同爱情片的老套桥段,两人躺到了床上,先是亲吻,卞小飞将手伸进女孩衬衫里时,她也没有反对。可等他想再进一步时,女孩说,如果说我们今晚一定要发生关系,那你可以走了。卞小飞心有不甘,嘴上却说,不勉强。
他在女孩的床上躺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走时,他挫败地留下一句,真搞不懂你们女人怎么想的。女孩没回答,只是迅速删了他的微信。他翻来覆去地想,明明去之前,他还问她,套子有没有?她说有。明明女孩接过他的水时,还夸他体贴。
也许是进门不久,他脑袋一片空白,没话找话地说,我还是第一次约这个。他记得女孩垮了一下脸。他想这句话也许冒犯到了女孩,“那个什么反荡妇(羞辱),觉得自己是荡妇那种嘛,把她想成那么随便的人。”如果真的是这样,他说他也感到抱歉。
“没有了,自从那一次没有过了。”卞小飞担心自己患上了某种心理障碍。曾经,他认定自慰伤身,如今也不得不用手解决。只是每次自慰过后,他看着空荡的房间,“觉得自己越来越没用了”。
卞小飞刚过30岁生日,他认定22岁才是恋爱的黄金时代,当年他也有过一次恋爱,“嘴巴会说一点,胆子大一点,基本都找得到”。如今在他常刷的短视频里,他被告知,男人30岁以后,谈不上恋爱都是因为生活失败。“什么要有房啊,什么要有车啊”, 30岁没房没车、还在送外卖的他,似乎被剥夺了浪漫的权利。
没有其他路走了,深秋的这天晚上,卞小飞出现在“爱爱乐”的门口。

“爱爱乐”从下午2点营业到凌晨3点,天色刚擦黑,男人们如循火光而来。在深圳工厂区,夜晚是男性荷尔蒙最旺盛的时候。富士康门口,还没脱下制服的工人坐在台阶上玩手机,无处安放的双腿折叠起来,屏幕照亮一排排年轻男孩的脸。奶茶店也坐满男生,循环播放一首叫做《厮守天涯》的歌:“姑娘你可愿与我/一起浪迹天涯/姑娘天真无暇/他的承诺太假”。宿舍楼挨着宿舍楼,在某些路段,手机会被挤到没有信号。篮球场的照明灯未开,一旁厂房和宿舍的灯光遥遥地投过来,9个男孩在暗影里争夺同一个篮球架。
“网络征婚交友对象提出投资,小心是诈骗;视频裸聊风险大,偷拍录屏真可怕”,祷告般的广播男声盘旋在工厂的上空。

夜间的富士康集体宿舍楼
好几个来“爱爱乐”的男人都说起,深圳有个“光棍之城”的别名,年轻光棍们有时就会困惑,女孩们都去哪了?当然,如果愿意承认的话,女孩并非没有,只是没有选择他们。一个男孩在的公司有近百号员工,只有三四个女孩,名花皆有主,他听说她们嫁的人家都不错。
一位来到“爱爱乐”的模切工人说,当他终于在轮休那天走出工厂,走在姑娘们玉腿林立的路上,他会在头脑里“一件件脱掉她们的衣服”。他危险的念头旋即被“爱爱乐”掐灭,从面孔和身材的角度说,他承认,娃娃是某种终极的幻想。这位小臂爬满唬人纹身的工人说,现实中不会有这样的女人爱上他。
“爱爱乐”的房间贴着标牌:“娃娃虽好 建议五分饱”。李博会告诉常来的熟客,不要对娃娃产生情感寄托。一个小伙头天来玩了3个娃娃,第二天一早又来,被李博拒绝,说至少半个月后再来。小伙掐准了日子,半个月后准时打电话,我今天可以来了吧?
李博回复:你应该去找个女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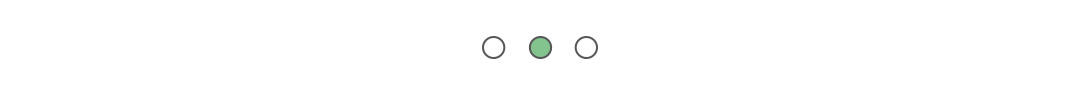
“那我图什么呢”
在卞小飞到达“爱爱乐”的5小时前,左鑫也走进了“爱爱乐”。他目标明确,一上去就选中了胸最大的娃娃,25分钟后便轻快地下了楼。“是不是可以弄一些铁架子,把娃娃放上面——架子一转动,娃娃多灵活啊。”左鑫留着长指甲,戴副眼镜,白白净净的,却持一种老成的口吻。“我们已经在这么做了,”李博眼睛亮了起来,“你是很爱动脑的人。”
我以为左鑫久经情场,后来才知道,“爱爱乐”那25分钟对他意义重大——倘若我们不那么原教旨主义,承认硅胶娃娃只是一类稍稍特殊的性爱对象——那么,这就是这个25岁男孩的“第一次”了。
在“爱爱乐”初次见面的3天后,我在30公里外的华强北又一次见到左鑫。他领我进了一座人声鼎沸的大厦,我们绕着一圈又一圈的扶梯上上下下。这是全国最大的手机市场,左鑫介绍说,不过我的公司不在这儿。
从大厦出来,绕进“某某村”的牌坊,再拐两次弯,这才到了左鑫的公司。说是公司,就是个6平米的小档口。这里是手机维修店的下游,鲜有人光顾。它和另外1万多个档口一起,共同组装起华强北的格子间世界。人声很远,“财源广进”的挂画下,三个男人座位相依,老板、左鑫和一位学徒,各自对着一台显微镜,伏于桌前。
左鑫留的长指甲,其实是用来扣屏和拆屏。18岁后,他的指甲长度就没变过。那年他没考上大学,大专一学期1万5,他交不起。59人的家族群里,他是唯一一个没念到大专的。他到上海做换屏的上门维修,定价120块,常有老头老太甩下一张百元钞,操着上海话讲,就这么多了。修一单挣30块,但一旦公司认定某一单有问题,就要罚五六百。他接过奉贤的一单,来回路程花了7个小时。为了犒劳一下自己,他顺道去了上海中产度假胜地“碧海金沙”,见到的那一刻就失望了,“看湖也是一样的,有的湖够大你一眼也是看不到边的”。
全国电子产品市场的中心在华强北,左鑫朝圣一般地过来。没来多久,订单因疫情锐减,为了争夺生意、抢在第二天一早将手机交还顾客,他被安排上夜班。他没和父母说夜班的事,白天睡觉时,妈妈打来的电话总是接不到,只能轮番用“手机坏了”“手机没电了”搪塞过去。他早上9点下班,昏昏沉沉地走进地铁口,看到衣着簇新的、上班的人潮从地下升上来。人潮很快淹没他,他独自逆流而下。

在富士康周边生活区散步的打工者
一个从工厂出来的男人,在“爱爱乐”说起那段打工经历,用的是一种劫后余生的语气,“你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做了为什么,你就知道要这样做,就知道一定要重复这个工作。”
忙起来,有同事连续上了24小时班。加班费自然多,可“挣那么多没命花啊”,很快,左鑫感到胸闷、头疼。两个月后,他辞了职,降薪来到这个小档口。
维修有维修的规矩,左鑫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修过最高档的机子是iPhone 8p,更贵的属于老板。他是个脑袋里装满奇妙念头的年轻人,却对这份工作的未来茫无头绪。“职业目标?修上一台iPhone X吧。”
在左鑫独居的20平米单间里,厨卫割据半壁江山,双人床又侵占了剩下的一半。有天他想在家做几个俯卧撑,发现身体没地方展开。有时候,他会想起自己在安徽农村度过的青春期,家里没装电脑,少年左鑫的性幻想素材来自国产剧里隐晦的对话。他一边想象一边自慰,为自己的“创作”沾沾自喜。如今他熟稔通往黄色网站的条条大道,但那种压抑的快乐,和快乐过后的失落,和14岁的时候是一样的。
他当然有过喜欢的人,高中前桌,他在她身上觉察到一种和他相似的东西——那时他父母在上海打工,班上组织收费的集体补课,他是唯一没报名的那个——女孩呢,也不爱说话,调侃她两句、脸一下就红了的那种。他们都是被摈除的人。
他拖到高考前一天才向她表白,送她一条手链和一盒心形巧克力,女孩收下手链,退回了巧克力,安慰他说,谢谢你,但我这辈子都不会恋爱了。左鑫被这句话吓坏了,以为她受过天大的情伤。直到两年前加上微信,见她发和男朋友的甜蜜合照,他才明白过来:也许人家当年那句话,只是为了不让他难受而编出的理由。
有朋友靠王者荣耀谈了三个女朋友,左鑫不为所动,每晚11:45到家后,他在电脑上打两个小时“硬核的动作游戏”。有个大怪他打了整整一周,并未在中途沮丧。他知道自己一定会赢。
“要不然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上班,感觉人生太没意思了,心里就没个念想了,那我图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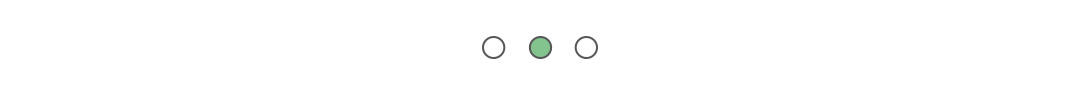
“慢慢这样子老下去”
这天的2号客人满头大汗地坐下了。“想玩第二个,”他羞涩地笑了,眼角纹路泛起波澜,“玩不动。”他把婚戒掏出来,重新戴上。2号客人臧国伟今年38岁,自称是婚姻制度的忠实拥趸。女儿刚出生那会儿,一家人曾在深圳短暂团聚。等到女儿上了幼儿园,6000多块一个学期,妻子只能带女儿回老家广东湛江,过年他才能见上妻女一面。他和同事住双人间,上下班同步,想“放松一下”也无处容身。
但臧国伟也没有像他的同事一样,在深圳随便找个女人搭伙做“临时夫妻”。他认为忠贞几乎是婚姻的全部,复杂的情爱关系一不小心就会逾越他这个老实人的掌控范围。最逼近红线的一次,臧国伟说,是和女同事单独喝了顿茶。不知是茶多酚还是愧疚起了作用,那晚他没有睡着。

打工者经常光顾的酒吧
今年4月,他看到“爱爱乐”的新闻,经过7个月的心理斗争,终于说服自己和硅胶娃娃做爱难以达到出轨的标准。只是他还没做好准备告知“思想比较封建”的妻子。
臧国伟在一家椰子鸡餐厅做厨师,身为广东人做的却是海南菜,他自己都觉得怪怪的。“我们最有名的是湛江白切鸡”,他讲起白切鸡比椰子鸡还要来劲。每当别人问他你做的椰子鸡好吃吗,他其实不知道答案,他说做得太多了,他的舌头再也分辨不出椰子鸡的好坏。
他的一位同事创业上瘾,打两年工攒够了本,先后出去开了早茶店、烧鸡店、猪脚饭店,每回都灰头土脸地回来。“讲创业好都是骗人的”,国庆节去看创业题材的电影《一点就到家》时,臧国伟差点在影院里骂了脏话。
和臧国伟的同事一样,那位容易紧张的外卖骑手卞小飞,也想要逃离一种被驯服的生活。在丘陵环抱的岭南小镇,他从16岁起日复一日地做着皮蛋酥——不是因为他拿手,只是因为这是店家的招牌。恐慌是在快30岁的时候追上他的,“再不出来拼一下就老了”。
初到深圳,卞小飞干劲挺足,在微信签名里写:“不自律,无法逆袭,只能过重复浑噩的日子!”最烈的日头下,他一天能接四十单,月入七八千。他从原先住的五人一间的青年旅社搬出来,搬进了月租1300块的一室一厅。他本以为自己将很快找到女朋友,甚至提前买了一双女士拖鞋,摆在他的那双的旁边。
那双女士拖鞋至今没人穿过。连工作也开始辜负他。他原想努努力,争取一年做上站长,直到有天站长跑来问他借1000块,他意识到生活并不会因为他当上站长而变得更好。前些天,按照城市规定,他给电动车上了牌,绑定个人信息,罚单开到他的手机。平台要求快,市政要求慢,他觉得骑电动车像踩晃晃悠悠快要跌倒的高跷。
从专送跳出来做众包的时候,他原意是接单自由,多劳多得。现在呢,下午他坐在快餐店,刷短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一天送的外卖降到30单,再到20,前些天,第一次出现了个位数。
回家,他一个人喝酒,然后宿醉,“慢慢这样子老下去”。他始终不能理解那次功败垂成的约炮,和接下来一连串的打击是怎么回事。坐在“爱爱乐”大堂的两小时里,卞小飞6次谈到“失败”。他莫名其妙地、宿命般地失败了。“一个死循环,就好像你走不出来一样。”他抹了把眼睛,失焦的眼神迎向我,“有什么办法呢,真的有神来搭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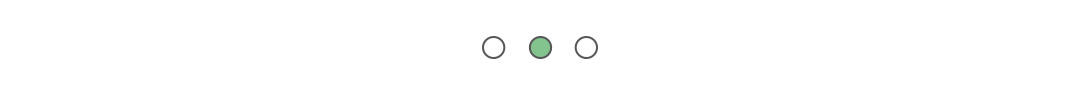
在世界上很少被看到的地方
“爱爱乐”属于这样一些男人,他们当然要承受“物化女性”的指责,但人人都害怕孤独、渴望亲密,他们可能是没恋爱的天赋,缺乏必要的运气,可能是没钱,也可能是没钱兼没胆。在这座生机勃勃之城,他们就像匍匐在地的小动物。
他们抱着体验“真正的”、“美妙的”性爱的憧憬来到“爱爱乐”,有时因所抱憧憬之大,失望就越大。很多人会在下楼后抱怨,娃娃太笨重,完全比不上真人。有人说他做到一半,触到娃娃冰凉的皮肤,忽然意识到面对的是个假人,觉得自己有点可笑。卞小飞期待娃娃能帮助他克服心理障碍,任务倒是圆满完成了,只是,他垂头丧气地说,“和打飞机一样的”。他好像比来之前更空虚了。
来“爱爱乐”前,那位和妻子分居的厨师臧国伟看了一部叫《空气人偶》的电影,日本导演是枝裕和拍的。他能清晰回忆起电影的开头:前一晚,男人和娃娃做爱,对它说,“你真美。”清晨起来,娃娃看到阳台上滴下的露水,回想起那句“真美”,它在那一刻变成了人。
在广州性博览会上,臧国伟也曾见过一个“好漂亮好漂亮”的娃娃,个子高挑,长了一张眉目柔和的东方脸。他在橱窗前看了又看。电影里的魔法当然没有发生,他和这个娃娃的结局是,他看到了它的标价——10万块。

被反复使用后,娃娃的手臂出现破损
和左鑫分别前,我和他到一家海鲜粥店吃饭。他正专注和面前的大虾斗争,闲谈里聊到越南,忽然郑重地落下筷子。我的梦想是去越南,左鑫说。起因是他看央视新闻时发现,“它说美国啊、欧洲啊,有时还说非洲,但它说东南亚吗?”他被这个“在世界上很少被看到”的地方迷住了,独自埋头研究起来。他说东莞本来有世界第一大鞋厂,一下班,整个镇上都是厂里的人,最近鞋厂搬去了越南,镇子一夜之间都空了。他的声音沾上海鲜粥的热气,听上去有些迷离。
那个鞋厂在越南会变得怎样呢?他想去看看。今年夏天,他总算下定了决心,为此申请了他的第一本护照。两天后,工作人员打电话说,疫情去不了,我这边先给你取消了。
父母劝左鑫回老家。他的高中同学很多都回去了,有关系的都当上了老师或公务员,他呢,在县城开一家手机店也可以。老家在哪?地铁坐到深圳东站,火车18个小时,下来坐大巴四五个小时,再转公交才能到。老家是另一个世界。
眼下左鑫仍在抗争,但他心里清楚,人生不是游戏,现实里的大怪有的一辈子都死磕不下来。那晚坐公交来“爱爱乐”的路上,他其实想的是,“假如过两年我回老家了、结婚了,我这辈子可能都体验不到了”。他的“第一次”没有想象中完美,他说他也知足了。

11月了,人们还穿着裤衩踩着拖鞋,在深圳的街上游荡。有天晚上,卞小飞送餐到商业街旁。行道树灯光闪烁,绿叶在晚风里荡漾,像是永远都不会枯萎。一个乐队在树下弹吉他、打架子鼓,唱一首他没听过的粤语歌。他停下来看了好久,录下视频。
“美团众包来新订单啦”,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爱爱乐”鲜有回头客,某段时间内常来的,会在几个月后忽然消失。有时候,卞小飞觉得在深圳是做了一场梦,醒来,或许他还是老家那个做皮蛋酥的点心师傅。无论如何,来深圳是个勇敢的决定,虽说没让他捞到什么好处,不过像个胆小鬼停在原地就更差劲了。他看《唐人街探案》,王宝强说,牛逼都已经吹出去了,人家都以为你在外面混得风生水起,其实,牙掉了咽肚里,苦只有自己知道。“死我也死在外面”,他发了一条朋友圈。
“送外卖靠自己的手在吃饭,没去偷,没去抢,没去骗人,”坐在“爱爱乐”大堂,李博安慰卞小飞,“我现在本身就很穷,大不了拼得更穷咯。”李博讲起,三年级布置作文《我的理想》,他还没见过花花世界,只写“将来我要开车”。出了社会,欲望跟着眼界一点点膨胀起来。这是他来深圳的第15年,不给人打工了,但仍和妻女挤在出租房,“爱爱乐”遭疫情重创,肩上也多了30万的债务要扛。
暖风沉醉的夜里,李博给几位客人各添上一根烟。众人静默,屋里烟火缭绕,他独自浸泡在旧日的情绪里头:
“我出来还是个小孩子,我就想着,这么高的楼啊,假如有一套我的房子就好了。一直就那么想,一直就那么想。到现在这些梦想都没有磨灭——虽然现在离梦想好像越来越远了。到老了,我会证明一下我在深圳来过,不是穿个拖鞋来,穿个拖鞋走。”
年轻的听众们入定似的点点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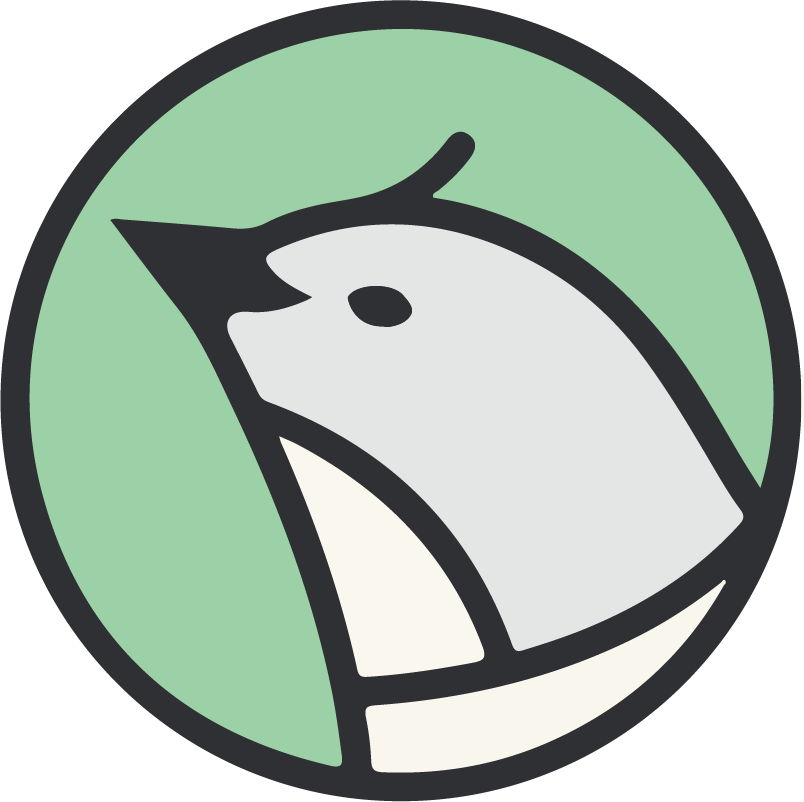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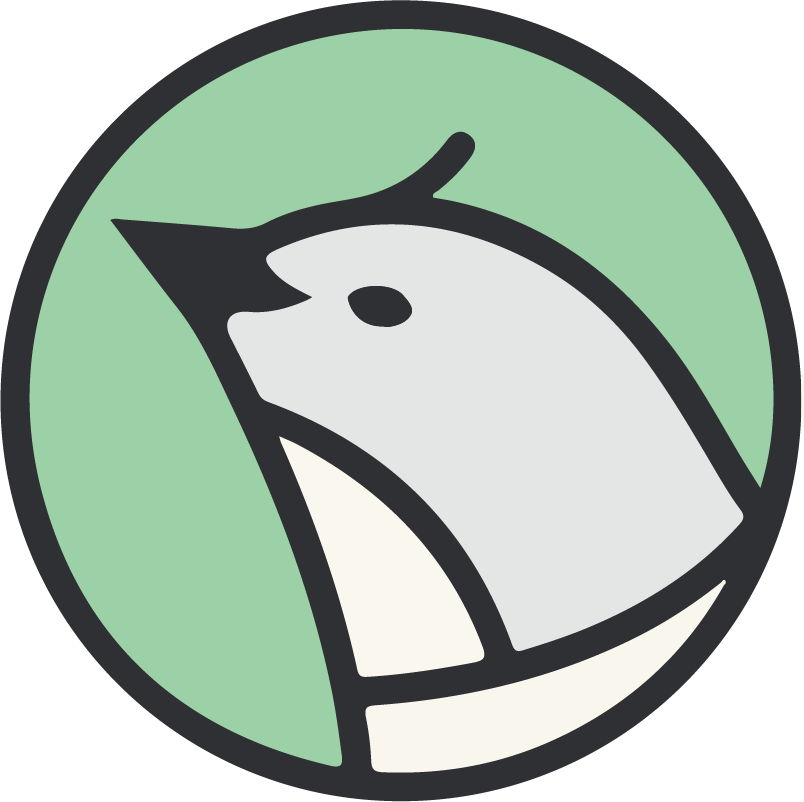
◦ 除李博外,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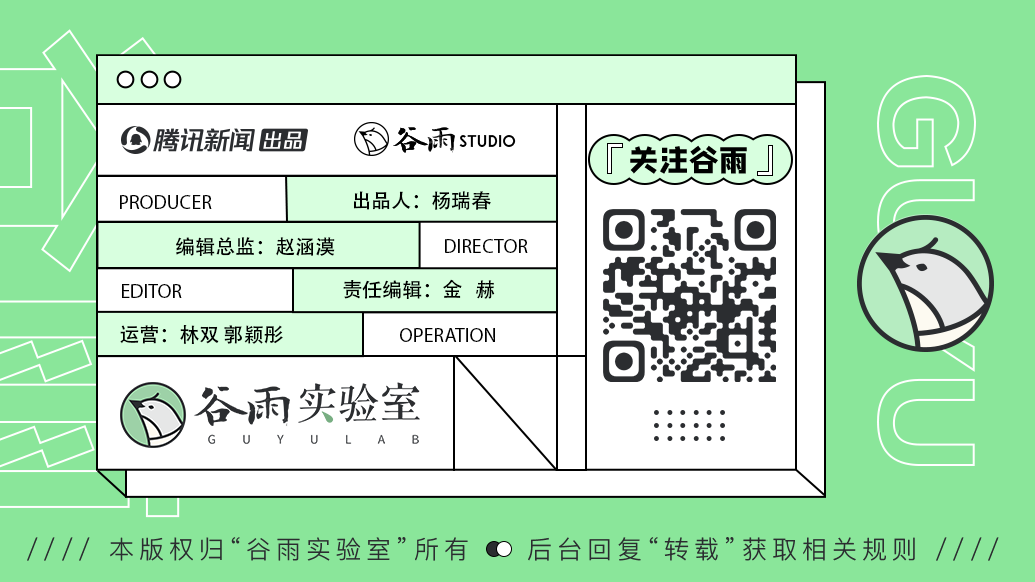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