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农奴:中国的户口本历史


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对欧洲中世纪的农奴有着极大偏见。认为在黑暗、封闭、愚昧的中世纪中,农奴的日子一定是浑浑噩噩。哪里能和我天朝上国治下丰衣足食的农户相提并论。可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首先,我们要明确下什么是农奴。想当然的人可能觉得,农奴就是领主的私人奴隶。其实这错的相当离谱,奴隶在法律意义上是财产(在很多城邦律法上他们只能算是半个人),主人只要乐意随时都能卖掉他们。虽然也有奴隶仍保有部分权利,但是理论上,只要主人想要,他们就必须交出所有的财富。当然实际生活中主人一般不会这么做,毕竟这会挫伤奴隶工作的积极性。而农奴虽然地位低下,最大的区别就是农奴是不能被买卖的,并且在权利是上有着比奴隶更全面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相应的,农奴需要交纳大量赋税给他们的主公。

农奴和奴隶的一个相同点是:不能随意迁徙。领主通过法律将农奴束缚在了土地上,迫使其依附于土地拥有者。最典型的莫过于中世纪前期的欧洲。比如诺曼征服后的英国,其社会构成即是大量的维兰(农奴)依附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塞恩(领主)。维兰们出于生存或安全等原因,将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人身自由一并献给领主们,然后以“农奴份地”的方式收回。这也是非常典型的封建庄园制度。作为庇护人的军事贵族保护农奴的安全,而作为回报农奴献上自己的部分权利和土地利益。
是不是听起来很可怜?没关系,因为中国的更可怜。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形成了户籍制度。秦朝统一六国以后,更是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管理。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法律尚答》筒退提到: “甲徙居,徙数褐吏,吏瑕,弗焉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可论?耐以上,当赀二甲。”

这一段主要的意思是,当时普通人如果需要迁徙,应先向官府提交手续报备。这也不难理解,因为秦朝法律中有严格的连坐制度,早在其一统中国之前就规定了"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既然都将平民管起来彼此监视,让你们随意迁徙的话,还怎么监视呢?更可怜的是,当时人们要离开自己所在地,哪怕不迁徙户口也需要“符传”(类似介绍信)才能畅游各种关口。可平民百姓怎么能随便去开“符传”呢?没有熟人,没有门路的情况下,手续就算能过也会经过多道程序,等到了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至于原因其实也和欧洲类似:方便收税。另一点则是方便征兵,在征兵时可以轻松把兵役人口统计到个位数。历朝历代希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有为”之君无不是此套制度的忠实拥趸。毕竟通过该套体制可以轻松从民间抽取大量资源用于战争或者大工程之中。

(游侠郭解)
所以说到头来,农奴制和户籍制非常接近属于大哥二哥的关系。其区别是由于集权和封建的不同,依附的对象也不同罢了。但是由于欧洲常年处于割据状态。没有哪个领主或者国王能够一扫六合,从而废除封建体制,再把整个系统重新格式化、原子化。
在“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封臣”的系统下,国王也罢,领主也罢,其所作所为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在英国的习惯法中,一个维兰需要给自己的领主在一周内服务三天,具体哪三天由领主决定,这称之为“周工”(week-works)。除了周工之外还有领主随时征调的“布恩工”(boon-works)。但小领主也不可能坐拥数千万人口的中原帝王一样拥有“大作为”,农奴日子虽然同样悲惨,但还无需斩断自己的手脚去逃避沉重的徭役。

在赋税上,随着货币地租的实行,一个佃户的地租往往长达200到250年不变。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足够让生产力得到巨大的发展,原本压得农奴透不过气的地租渐渐变得不那么沉重了。地租的比例从过去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再到八分之一留在农奴手中的越来越多。他们就可以将剩余产品卖到市场上去,甚至将其中一部分扩大再生产。这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农奴制在西欧是一个很复杂的制度。如上文所述,农奴制是农民希望获得庇护和领主签订契约而形成的。而且它的法律根据主要是当时的日耳曼习惯法,习惯法因地而异,标准不一,即使什么是农奴也各地所见不同。经过多年的研究,现在的学术观点是:西欧的农奴制并没有19 世纪时的史学家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农奴的数目不太多,在农奴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半自由农民和自由农民。农奴制作为主流存在的时间也并不太长,只在封建的高峰期比较普遍,而且过得更有人样。

以农奴制较为严重而统计又较明确的英国为例,它形成于12 世纪,到15 世纪或更早时即已经瓦解。在英国农奴制极盛时期的13 世纪,农奴约占农村人口户数的3/5 ,全国人口户数的1/3(《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反观中国,是个人就得有户口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皇帝直接控制,除非你是逃亡的黑户否则就肯定要被皇权束缚。只要皇帝一想要“大有作为”,全体人民都得替帝皇的“宏图霸业”添砖加瓦。
现在我们可以做出对比了。相对于中国全民都是皇帝的农奴,西欧的农奴不但相对人口比例较小,生活环境也普遍比中国更加稳定和良好。更重要的是农奴是自愿和领主签订契约交出自己的人身自由和土地获取领主的庇护。而中国的一出生一上户口就没有任何的回报,生而就是皇帝的仆从。双方高下已经可以判定了。

(全体的中国农民都是皇帝的私人农奴)
不过历史是公平的,中国也自然不会一成不变,这个机会出现在唐代。在安史之乱之后,随着藩镇割据的扩大,皇帝也无法像过去直接控制到每个户口。同时战乱也引发了比过去任何一次规模都大的人口迁徙。时人评价“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这导致过去那套把人直接束缚在土地上让皇帝“予取予求”的方式已经无法再使用了。唐朝共有三次由中央专使负责的人口检查,最后一次发生在天宝年间。而在安史之乱后,中央彻底将人口户籍的普查权利下放到了地方上。这样一来归属中央直接掌握的户籍数量就大幅度降低了。天宝十四年中央统计的户籍数量为8914709户,总人口为52913900人。而到了乾元三年只剩下了1933147户,总人口仅为16990386人。没了人口就没办法像过去那样直接对个体户籍征收人头税了,怎么办?两税法就应运而生了。

两税法很重要的一个改革就是分离出了“地税”。这套系统后来被五代军阀和两宋继承。过去是将人口束缚在土地上吃“存量”。既然现在人口流动了,那没有 “存量”吃的政府只好改吃土地。至于这块地属于谁,是自己来种植还是地主雇佣别人来,国家不管。同时两税法还改变了过去的实物税,大量发行货币取而代之。过去可以说,脱了衣服就是山顶洞人,现在随着货币的大规模使用,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脱离原始模板走向文明。在政府发行货币、放开人口控制之后,各行各业迅速成长起来了,政府再从流动的商贩手中收取货币税。这样,政府的收税方式就彻底从吃“存量”变成了吃“流量”。随着宋朝统一国家结束了战乱,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景象就呈现了出来。

不过随着女真、蒙古入侵,新到的征服者对南朝这一套不感冒。相对于人口大量流动从而“吃流量”。秦汉模板的“吃存量”无疑简单粗暴更符合胃口。于是这一过程就被打断了。一直到清末,中国农民都没能够像中唐和宋朝那样流动,又一次成为了“帝皇的农奴”。
而欧洲原本就是封建割据,所以不需要像中国那样将原本的系统打碎,从而迫使皇帝改变原本的路线。和中国相反欧洲的国王们是城市化的坚定支持者。无他,因为军事贵族的力量来自土地,通过封建采邑制度领主才能拥有自己的骑士。如果消减领主麾下农奴的数量,那么就意味着消弱了领主的根基。而没有一个国王不想扩大自己的王权的。

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就曾颁布过这样一份王室公告:“凡是愿意成为不动产接受者和经营者的村民,可到赫福德索尔茨博里的王室官吏处登记。至于那些愿意得到土地的人,同时要求得到城市安全的人,可到切斯特大法官及其同僚处提出申请,大法官以及他的同僚有权为所有愿意从国王那里接受土地,及希望国王保护之人在鲁德兰指定地方”。而根据中世纪的法律,一个农奴如在城市里住满一百零一天,而又未被指控那么就宣告自由。当时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人自由”(《英国庄园生活》 p268)
历史发展的结果就是:在西欧,由于人口往城市迁徙,农奴这一阶级迅速消亡,同时涌入城市的人口给近代的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的基础。一个则没能跳出数千年的死结。双方谁更加高明,谁有资格嘲笑谁,恐怕读者们已经有结论了。
本文来源丨网易号之三桂历史

《天涯连线》本期热帖

深度阅读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天涯连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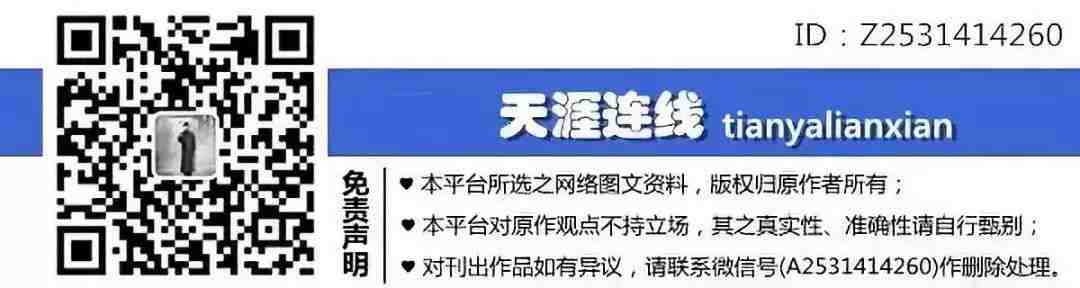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