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新伟丨从维熙、施康强与他们写作的公心



本文原标题:
从维熙、施康强与他们的时代特色
一片秋阳中,在朋友圈刷出了两条消息:作家从维熙于今日(10月29日)早上去世,终年86岁;翻译家施康强于27日去世,终年77岁。
多少年来,我们对文化名人远去,已经熟悉了两套八股悼文——“世上已无×××”,或“中国最后一位×××”。这次不知道类似擅讣者如何下断语,但我觉得这两位文化名人,似乎都有远较这两个空头谥号更为复杂的一面,尤其值得有所探讨。
在媒体工作近20年,作为编者,与这两位前辈素无交往,作为读者,他们的小说和文章,我却一点也不陌生。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冬天,在四川惯有的茫茫白雾里,从一个书摊上买了两本书:从维熙的《走向混沌》(第一部)和郑逸梅的《近代名人丛话》,小地方乏善可陈,这两本书倒是启我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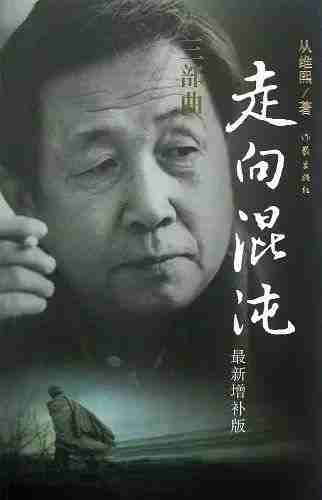

从维熙的《走向混沌》(2012年增补版)
首先是从维熙的姓氏少见,丛姓多,从姓少。再者,在当年的纪实风气中,这部关于牢狱生活的亲身经历,实在不是所谓的纪实可以笼括的。上世纪50年代的运动中从维熙被打入另册,他是和刘绍棠、王蒙、邓友梅齐名的“黑天鹅”,历经磨难,直到70年代末才重返文坛,他最著名的小说是《大墙下的红玉兰》,后来担任过作家出版社的领导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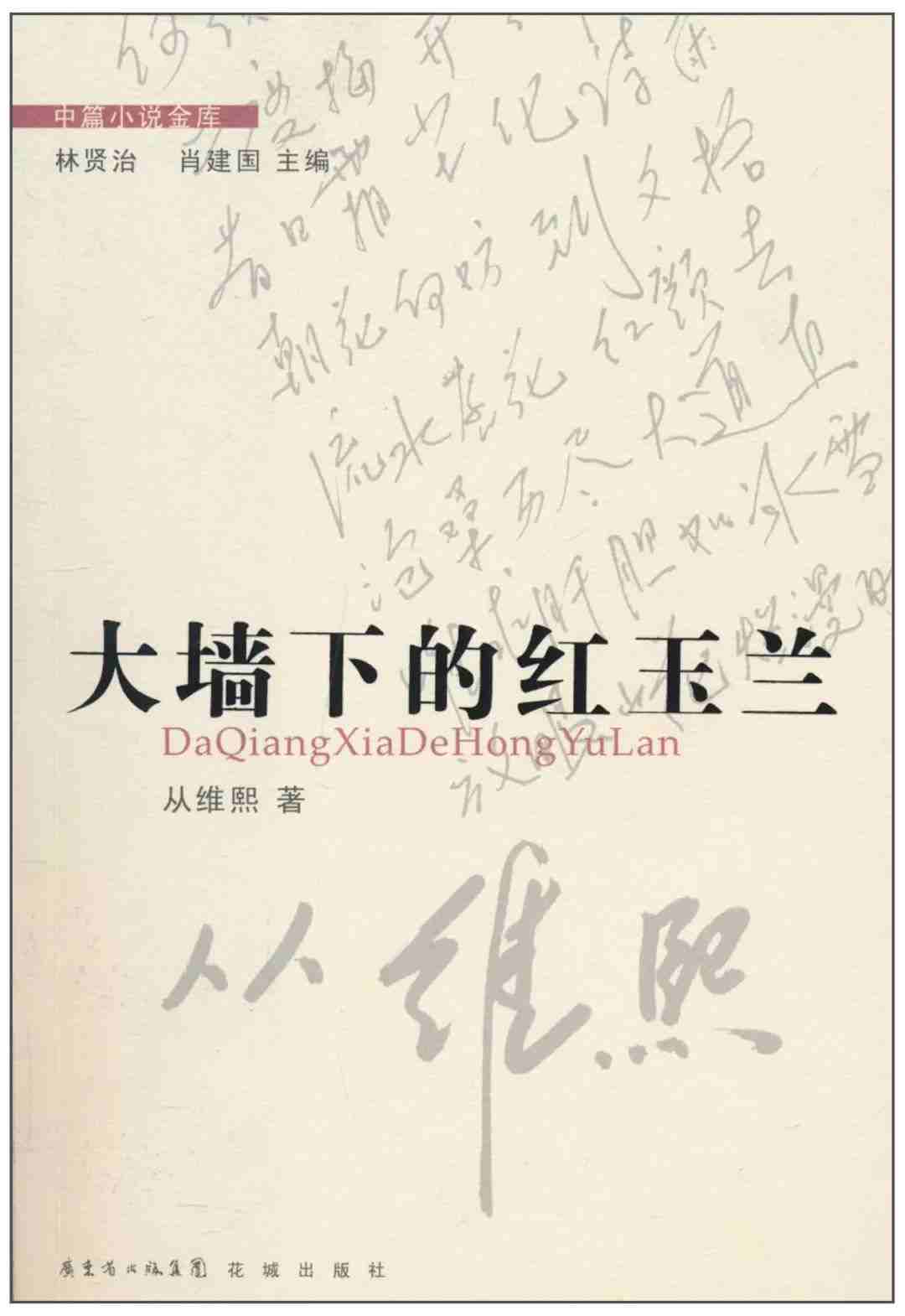

《大墙下的红玉兰》(2010年版)
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的反思,如“伤痕文学”是一大主流。不过相比之下《走向混沌》自传色彩更强烈,对于人性的裸露,也更为直接。初读此书时,少不更事,对历史、对社会、人人情世故皆少了解,可想而知面对这部小说时的冲击有多强烈。那是一个可以称为历史标本的世界,也是足以成为后世训诫的世界。对今天的人而言,似乎反思历史已经不足为训了,似乎反思本身也不大受欢迎。这时候读一读从维熙《走向混沌》前言里说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有着牛的坚韧,龟的沉默,以及风云时代的虎啸龙吟,但他们也是肉体凡胎,历史的胎记以及中国古老文化负面影响注入的生命残缺,是无法回避的。
则不能不敬佩他“供爬过历史溶洞的知识分子回审自识”的写作初心,虽然在那个时候,从维熙也不是唯一的。去年我为巴金故居纪念馆的一个展览抄录了60条巴金语录,大部分是从他上世纪80年代写的《随想录》等书里摘选的。抄书过程中,使我深深感受到巴金的伟大:他的语言没有什么文采,却质朴有力,堪称时代的强音,因为他的每一句陈述、追问、反问,都是对刚刚结束的动乱的深刻反思,其思想力度之入木三分。即使是在30年后这样一次偶然的抄写,也不能不受其感触、愈发敬佩他的思想深度和为社会、为后人负责的情怀。


巴金的《随想录》(1980年版)
值得一提的是,巴金也是极受从维熙推崇的作家,从维熙的名作《远去的白帆》刊发于《收获》杂志,“讲真话”是他们的精神纽带。
在我读过的一些名作,如宗璞的《三生石》、李国文的《花园街5号》、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王蒙的《相见时难》、孔捷生的《南方的岸》、李杭育李庆西的《白栎树沙沙响》等,偶然回想起来,颇令人有“含咏再三”之感,但《走向混沌》却是——“千万不要再看这样的小说了”,虽然主题、写法不同,但大抵因为前面数种小说有展现社会生活的一面,故容易让人亲近,有所寄托,而从维熙笔下——就像他的小说一度被称为“大墙文学”一样,场景与故事都限定在牢狱这一空间,故给人的刺激也特别大。在前者中,有令人愉悦的小确幸,有光明的尾巴,而在《走向混沌》里紧扣的是个人的湮灭。这当然是值得我们一读再读从维熙作品的原因。
另一位逝者施康强先生,是资深的法语文学专家,翻译过巴尔扎克的《都兰趣话》、阿兰的《幸福散论》等,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史学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他是中译者之一。不过,他更为读书人所知,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读书》杂志、《文汇读书周报》、《万象》杂志上撰文谈法国文学,也谈上海逸事掌故(他生于上海),其随笔文字,也兼具这种文学趣味和地域趣味,娓娓道来,读来令人忘倦,后来结集出版过一部随笔集《都市的茶客》。


施康强的《都市的茶客》(1995年版)
施康强的文章,能体现出以钱钟书为代表的学者文风,文章有知识,然而又不仅仅如此。记得我当时接触到他的这些短文,都是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后来又从旧刊《读书》杂志读到一些。总体而言,施康强与他“同台献艺”的撰稿人,如《读书》的吴岳添、卢岚、李长声(仅大致年龄而论)等,《文汇读书周报》的恺蒂、梁治平等,同为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报刊文化人,这类人的文章多见趣味,于文化理念的普及亦最为深远。记得黄裳先生曾经评论前后《读书》风格,有“文苑、儒林”的区别,可以说是相当老辣的断语。
今天来论及当年的撰稿人群体,无意于重述他们的辉煌——当年我在乡间千方百计才能读到的书,今天只要有手机,在任何地方都能读到。但这两种阅读生态值得比较,载体不同,时间地点不同,呈现的结果也大可深思。如果“流量为王”也是一种结果,那至少也该知道它的前身是何种形态。曾经是《读书》主编的沈昌文在回忆文章里几次提及当年办刊的点滴,其中语言学家吕叔湘的一条意见是“不拿十亿人的共同语言开玩笑”,这句话有人认为是强调语言规范,但我们联系这二三十年来报刊媒体的发展、特别是现在新媒体的状态,再来体会这句话,可以有太多的感触:无论是办刊还是下笔,能有一种有所负责的公心是何等的可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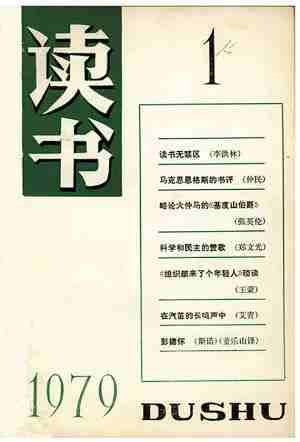

《读书》杂志创刊号
将近100年前,一位年青诗人弗兰斯·克萨危尔·卡卜斯在里尔克给他的十封信引言里说:“一个伟大的人、旷百世而一遇的人说话的地方,小人物必须沉默。”是否该将从维熙、施康强两位置于这样的地位并不重要,但就我们的文化而言,一些人所做的力所能及的事值得我们倾听,不论那是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时期,而受到过他们点滴影响的人,更不应该保持沉默,否则就太冷漠懦弱了。

逝者

从维熙(1933-2019),作家。河北玉田人,曾任教师,做过记者、编辑。1956年开始专业创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重返文坛后,率先发表了十几部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因而被文坛誉为“大墙文学”之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长篇创作《北国草》、《走向混沌》等。

施康强(1942-2019),著名翻译家。上海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国语言文学专业。退休前,任中央编译局译审。译有《萨特文论选》、巴尔扎克《都兰趣话》、阿兰《幸福散论》、雨果《巴黎圣母院》(合译)、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合译)等。著有随笔集《都市的茶客》、《第二壶茶》、《自说自话》、《牛首鸡尾集》等。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