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慈:我在硅谷养混血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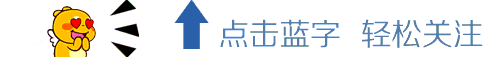
原文首发公众号“北美养娃那些事儿”
香奈儿-米勒的妈妈张慈说:“苦难会悄然来临,但正义还是会到。你们想象不到这三年我们怎么过来的,上法庭上到想吐,法官偏心、律师扭曲事实、犯罪人撒谎……美国司法系统太恐怖了,要不是大米写了那封感化了成千上万人的信 Victim’s Impact Letter, 她想翻身做梦都不可能!
孩子通过写作治疗伤害,终于活过来了,我要为此欢呼!文字的力量将带给全球受性侵的女性力量和温暖……尤其是那些尚在黑暗中挣扎、想自杀的女孩,我和我女儿与你们在一起。
亚裔给美国主流社会的印象就是唯唯喏喏,街头被抢劫的是亚裔,校园被嘲笑的是亚裔,工作压力大跳楼的是亚裔,香奈儿的勇敢和对美国司法的改变是亚洲人的曙光、是一种希望!
她在法庭上宣读的《受害人宣言》,千万人被感动得掉泪无数次,不是因为她的苦难,而是因为她语言中有一种孤注一掷的力量,一种强大的求生感、一种逼人的正义感。我是中国母親,我比犹太母亲更强大。”
张慈和先生是如何养育孩子的?这是几年前她写的抚养孩子的心得。香奈儿-米勒能在苦难中站起来,是有一个坚强的后盾,一个温暖的家庭。

米勒爸爸的话
“我们Palo Alto的孩子是如何长大的?他们有好的父母,有安全的社区可以走路去上学,四周围的家长都是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在受到家长支持关注的学校上学,有一两个好老师,有宠物,家长有足够的钱带孩子去国外旅游,孩子一旦找到自己的兴趣,马上就与众不同。
When them have particular interests, that’s where it makes difference。而独立思想,永远是最重要的,它超逾一切,很少有人能做到。”
—— 克里斯多夫·米勒博士
一
Palo Alto,斯坦福的根据地

一种教育成功的标准是:重点名牌大学,容易赚钱的工作,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有机会发挥天赋;另一种教育成功的标准是:独立思想,不放弃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赚钱,不尊重权威,不自由毋宁死, take all the experience seriously;最后一种教育成功的标准:任其自然,与其相关,保持与孩子的亲密关系,辅助孩子完成心理和兴趣需要,找到所爱的生活,找到生命的意义。
最后一种是我自己的,我选择那样养孩子,我也是这样长大的。
Palo Alto 是我两个孩子的故乡,她们生于史坦福医院,在 Charleston Ave -Arastradero Ave 这条大道上完成了她们从童年到少年的教育:Hoover Elementary School, Terman Middle, Gunn High. 最后,大女儿上了UCSB, 小女儿上了Cal Poly.
我的先生是心理医生,我是作家,我们的孩子,数理化不太好;音乐,只有能力欣赏,不能深究;但她们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超强,人文知识强,人际能力更强。她们的幸福就是当小孩,我们的幸福就是当父母。
挣扎了很多天,我体会着养育孩子的种种滋味,想要搞清楚自己是如何把小孩养大的?我这个中国人与克里斯那个美国人是如何互相撕咬着,将孩子整长大的。但还没闹清楚,自己就把文章写出来了。
Palo Alto是这个地球上的泡沫,史坦福大学坐镇,IBM, HP, Intel, Google, FB, Cisco, Yahoo, LinkedIn, Apple,Tesla这些引领世界高科技发展的各大电脑公司, 汽车公司都在四周,它充满创新的概念与开拓的年轻人,生在这个叫“硅谷”的泡沫里的小孩,天生就和别的地方小孩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二
在Gunn高中当家长

不一样在于这个镇上有一个类似于“阳澄湖”似的Gunn高中,不管什么样的螃蟹,扔进去以后,捞出来的都是“大闸蟹”。我老大是2010班毕业,同届毕业生有24个进了史坦福大学,10多个进了伯克莱加大,2个哈佛,3个MIT,1个普林斯敦,2个耶鲁,还有NYU,杜克,达特茅斯,布朗,哥大,加州分校等。
这个镇的房子比伦敦,东京和纽约还贵,但仍然源源不断地有人从外州,其他小镇,其他国家搬进来,因为这里是:硅谷。这里的小孩种族背景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只有一样东西类似:超级聪明。
有一天,在YMCA的澡堂子里,一群裸体的,黄皮肤的,姿色已经掉落满地的华人妇女站在一起,高声大气地用中文讨论孩子的教育与去向问题:哎呀那谁,XX 她们家的安娜考上了哈佛,XX她们家John上的是普林斯顿吧,early admission 呀,人家那谁去的是FD。。。包装费用太贵了。。。人家麦克早都进史坦福两年了。。。”

早在十年前,这支队伍就是我的队伍,我也会抓一条毛巾站进去,忐忑不安的听着这些自己本身也是清华北大上海西安交大南大厦大毕业的老娘们的唠叨。
幸亏我的孩子已经水落石出了,将我从如何教育孩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家孩子中美混血,孩子没有全部拿A,SAT考得OK,但我照样爱他们。现在坦白一句实话吧:我从不看她们作业。
因为我成长过程中,没人看过我作业,也没人给我去开过家长会。这后面一条,我倒是没有照搬,我坚持参加了两个孩子所有的家长会,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初中,高中,我都坚持参加每一个家长会,并在学校做义工。
我做了14年义务劳动,包括在幼儿园给小孩刷马桶,喂小孩们养的鸡,帮助小孩做手工。在小学给小孩开车去远足,春游,参观博物馆;给老师印教材,做午餐,组织中国年庆祝活动,小孩体检维持次序。
初中主要是监督乐队练习,开车带球队去大老远的城市比赛,节日打扫,等等;高中,除了开车带球队出城比赛,年度给老师做感谢盛宴,橄榄球大赛上卖热狗汽水,还有半夜三更冒着大雨去铁路站岗,预防学生卧轨自杀。
之外,就是孩子在校外的各种运动和上课:中文课,奥林匹克数学班,绘画,钢琴,长笛,电吉他,空手道,歌唱,芭蕾,垒球,足球,排球;曲棍球,GRE补习,西班牙语补习,找校辅导员开会,突然有一天,这一切就到头了,孩子上大学了。
三
女儿上了大学

我心里也希望,大女儿去上耶鲁大学,学习文学专业,她写作能力很强,13岁就在伯克莱大学暑期班读莎士比亚。我带她去耶鲁大学参观学校时,耶鲁大学的老师,我的朋友苏炜一见我女儿就叫起来:“你就是我们耶鲁要找的那种小孩!”
我的女儿朴实厚道,天生爱读书,运动能力强,个子高人漂亮,她没有告诉我们,她高中最后两年都在 East PaloAlto 的“饥饿夏令营”给那些没有钱进夏令营的非裔和西裔孩子上数学课,绘画课,舞蹈艺术课,运动课。
我的大女儿最后上了UCSB,圣特巴巴拉大学加州分校。这个学校在大海边,有美国大学最漂亮的校园风景,她非常喜欢UCSB,当然,每个小孩最终都喜欢自己的学校,但是UCSB有一个系校CCS,是美国大学暗藏的明珠,叫做:College of Creative Studies, 它有科学和艺术两种,没有传统的积分制,也有科目考试。学生转学,主要靠作品和教授推荐。由于UCSB常年阳光普照,我女儿热爱打沙滩排球,她健康得不亦乐乎!
她上的创意学校的教授非常欣赏她在Spoken Words上面的天赋,给她和她的同学在好莱坞的酒吧,图书馆办过两场秀,别人是讲两三分钟的短故事,她则可以一口气用不重复的词将一个8分钟的故事讲完。
CCS有着充足的学术环境和充足的创意空间给她写作提供条件,加上UCSB 离家仅仅五个钟头的路,她可以常回家。我女儿过了四年得意的大学生活。在校期间,她获得UCSB的写作奖CCS Poetry Prize及全国性的文学奖 Brancart Fiction Award。
美国的家长普遍关心的是,孩子是否开心,又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潜力,又没有找到自我,能不能成为他/她自己喜欢的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大女儿酷毙了!
四
大学枪击案

但是,就在她毕业考试之前两周,一个男生开枪杀死了三个同学,打伤七个同学。我女儿的朋友,屁股上也挨了一枪。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在一个黑下来的剧场里,正在准备放映我的电影《哀牢山的信仰》。
看见手机上Wechat 突然出现一个微信消息:UCSB 校园枪击案,三死七伤。。。我当时跑出剧场,跑到办公室,拿起座机电话拨了远在美国的女儿的手机,我在静音中等待她的声音,那几秒钟,我的身上都是冷汗,心脏也不跳了,嘟---嘟---嘟---虚妄的人生啊,我的孩子出事了,我的生活出事了!
听到手机里女儿一声:哈罗!
用手捂着嘴,我呜呜地说:宝宝你没事吧?她睡意朦胧地说:我们很多人在一起,你别担心。
我想起她出生的时候。大米生于1992年6月,史坦福医院。她出生时七磅十二安士,头小,双腿长,有点像青蛙。医生把她甩在我胸前时,她使劲地睁开一条缝似的眼睛望着我,我一下子就被电到了,我哭起来,哭到停不下而抽泣。她的小眯眯眼使劲地睁着,努力看着我,她在寻找 connection, 她在问:你是谁?
我给她答案了吗?我做到大米心目中向往的那个的妈妈了吗?
我记得她五岁那年,很讨厌学中文。星期天,我带她去斯坦福大学马立平中文学校上学,出门时,她紧紧抱住一根柱子,大喊大叫:我愿世界上有一个商店,我可以买一个新妈咪。。。我使劲掰开她的小手,把她拖走了,送到马立平那里去了。
十五年后,在UCSB的留学交换项目中,她自己报了去上海,在复旦大学上中文课。我呢,又去上海陪读了半年。
五
两个女儿

虎妈出现的时候,Palo Alto 又掀起一阵如何教育孩子的波澜。虎妈的丈夫是犹太人,犹太人是偏母权的。我的丈夫却是一个倔强不妥协的美国人,他决不允许我强迫孩子做任何事情:不准强迫小米进合唱团;不许送孩子进补习班,不许包装孩子,孩子申请大学,全部自己弄。
有时候我很想咬死我的丈夫,如果不是他,我的大米和小米会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她们会去上东部更好的大学。
但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包括我们的婚姻,我们孩子的成长,她们的现状。
小米现在在Cal Poly 念大三。她的专业是Computer Social Graphic, etc. 她刚刚从德国留学一个学期回来。她小时候很讨厌去欧洲,纽约。每次都要受伤或者哭叫,好早点回家。可是大二却自己申请去了欧洲,不停地写信回来说,欧洲太酷了!
小米的出生比大米要容易得多,她也不睁眼睛看我。她的出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她经常生病,害得我中断了作家生涯;她的个性非常特别,几乎不吃人类吃的东西。
她两岁半,我带她去Bing Preschool 排队报名,见到斯蒂夫. 乔布斯站在门口跟两个家长聊天,手上端着一杯咖啡。当时他的大儿子在Bing Preschool。那时候,小米还不会讲话。她到三岁才慢慢开始讲话。小米就是喜欢那个学校,喜欢把她的果汁瓶埋在那个学校的沙坑里。
但最终没排上队,上了另外一个平民的幼儿园,跟一群墨西哥孩子一起长大,爱上了墨西哥玉米饼;小米9岁时,在万圣节去见到斯蒂夫. 乔布斯家门前排队要糖,斯蒂夫·乔布斯的太太和儿子站在门口给小孩每人发一块一磅重的巧克力和一只苹果。小米盛装扮成小美人鱼,提着一只小篮子,接受乔布斯太太给她的糖果。她的个性及其认真,每天都必须是她想象中的某一个角色,盛装出门。
而大米从来不干这种排队要糖的事情,也不喜欢穿故事服装。
小米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孩。她天性不爱学习,好玩,好宠物。她要狗,爸爸就给她买狗,她是由两条牧羊犬伴随长大的;她还养过南美洲的大兔,乌龟,蛇,各种老鼠。但她最好的是鲨鱼。她学会阅读之后,读过上百本有关鲨鱼的书。
老二默默无言,除了玩,对学习和运动都没兴趣,她去上学就是为了去见朋友。她弹过一阵电吉他,因老师被我开除了,她也就不弹了;她喜欢做小电影,在手机上做过几十部鬼怪小电影;带她去书店,图书馆,她转一圈就走了,说没有一本书是她想看,值得看的,除了哈利波特,她从小热爱大鲨鱼,她自己读完了400多本有关鲨鱼的书,她也只收藏关于鲨鱼的书。我曾经很沮丧,不知道怎么调动老二的学习兴趣,扭转她的读书态度。
克里斯总是跟我说,要给小孩犯错误的机会,其实那才是成长的代价和需要。
最终,小米爱上水下摄影,高中的时候,爸爸给她买了一台水下摄影机,她拍了很多杰出的作品,人物几乎全部是她的女朋友,她们盛装从高处跳进水里,在小米的镜头中变成花朵。她申请大学,有一大优势就是她的摄影作品很惹眼球。
小米在Palo Alto 有很多朋友;追求她的男孩也很多。她的比较认真的一个男友,来过家里给她送玫瑰,男孩考上哈佛大学,而小米上的是加州大学,两地分居,她干脆就算了。
大米独往独来。男友考上达特茅斯,飞机飞来飞去,四年花了克里斯不少钱,克里斯为了女儿的幸福,一点不在乎。
六
怎么当父母?

我的两个女儿如此不同,如何与我的女儿connect,是我一生的使命,所以,在教育上,我的态度就很明确:任其自然,与其相关。婚姻中最大的财产也是孩子,教育孩子是父母最重要的事,让孩子回归自己的轨道天性,是婚姻无憾的解药。
怎么当父母?这个问题,孩子一生下来,我和克里斯就在吵。每次必有答案:不离开孩子,把她们养大!
我父母没有养过我,直到我成人,都无缘与父母一起生活。我外婆是那个抚养我的人。怎么养我的,我就怎么养我的小孩。我的外婆,只有这几招:给我东西吃,给我床睡,随时都在家里等着我,不回家她就到处找我;她没看过我作业,她不识字,但她是一个铁杆穆斯林,每天五次礼拜,连文革中,她都敢悄悄做礼拜。她的家族,有一说是2200年前跟着诸葛亮去到云南的人,有一说,是明洪武14年犯事儿后冲军到云南的重犯。面临教育,这种家族的教育都只有一种:任其自然生长蔓延。
我高中毕业考上县城应届文科状元,我的动力是好奇心和写作热情。那时我天天写作文,想象未来。一个人的资源包括他的时间、精力和天赋。而如何支配他的个人资源,将最终影响他生活策略的形成。
孩子要靠他们的个性活下去,家长强迫孩子学习是没有用的,孩子讨厌的东西自然坚持不下来,而如果是孩子喜欢的东西,即使放着不管,他也会坚持下去的。我就坚持了写作,这个活动就像是我的宗教一样,我每天必练习,就像教徒做礼拜。
我经常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与教育理念关联的一些转发文章,其中大多只在某个方向或几个点上,并不是系统的比较和分析。系统全面,精炼简洁的理解中西方教育的文章并不多见。那种有独特见解,会引起争议的文章更是少见。
我自己写的,也不怎么样。原因是,人太复杂了。任何一种教育系统,只要是真的东西,绝对有价值和分量,这包括真心,真爱,真货。
七
克里斯如何当爸爸?

他从不批评我们的小孩,他认为她们事事拔尖,样样优秀出色,很给他面子。他对小孩的爱,常使我吃惊。因为我没有见过中国男人那样对孩子的。
举个例子。大米高三时参加了曲棍球,教练是史坦福大学来的二十多岁的一个女子,叫丽莎。她是白人,运动员,非常严厉坚韧。我的女儿腿很长,跑得也很快,她却从来不让大米上场。为了讨好她,我大冬天的坐在记分台上计分,吹终场哨子。花自己钱给队员和教练买水,土豆片,饼干,披萨。甚至,和其他家长义务开车送整个球队去大老远的城市比赛。
可丽莎根本不吃这一套,大米就像是不存在她的视野里。这件事让我很痛苦,就告诉了大米的爸爸。米爸非常愤怒,他就干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天,home game, 我正在伤心地看着时间一分一秒流失,教练根本不换人,大米和六个女孩一直坐在草地上,手握曲棍,没有任何机会上场。我方太弱,落后于Poly 高中。上半场结束了,队员休息,丽莎脸色难看。
下半场又开始了,又是原来那六个队员上场,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是米爸。他友好地问,球赛如何?女儿上场了吗?我如实汇报,他平静地说,你把手机递给教练。我说不能,球赛又开始了,她在执教。丈夫压低声音咆哮:请你把这娘炮的手机递给她!我跑过去,正好暂停。
我把手机递给了丽莎。我看见她的脸又红变白,又变青。她将电话还给我,高声叫我女儿的名字,叫她上场,换了一个女孩下来。大米一上去,像一头鹿飞迸,她从小就是田径运动员,打过篮球,排球,有非常好的运动素质和运动意识。
只见她轻松进球了,而且连进两个,将比赛翻盘。比赛进入高潮,围观的双方家长都群情激扬,叫声不断。大米没有再下来过,直到终场。
赢了。大米兴高采烈地向教练跑去,结果发现丽莎脸色铁青,转过身,根本不理她。她看了我一眼,跑过来问我。妈妈,刚才那个电话是谁打来的?我支支吾吾,她逼我:是爹爹吗?她跑了,没有和队友一起收拾球具。
等我在学校忙完回到家中,见大米在厨房里高声教训父亲:你以为你是谁,可以这样做?米爸说,我错了;大米:你以为你一个电话就可以摆布教练,扭转我的命运吗?米爸低下了头再次说,我错了。大米不依不饶:你以为一个人的荣耀要靠她的父亲去讨吗?米爸的头更低了,几乎要到胸膛上了,说,我道歉。大米:你以为,我一生的奋斗就是为了通过父权走捷径吗?你以为。。。你以为。。。你以为。。。
随着低头的程度,米爸灰白的头发遮住了前额,看上去真的很可怜。
我很为克里斯自豪,美国人,从来不逆来顺受;同时我也从这件事发现了大米自信自强自重的一面。从她小嘴里蹦出来的那些逻辑性很强的反问句,实际上就是克里斯的基因。
八
Palo Alto的家长们

Palo Alto 的居民,四对夫妻就有三对是Ph.D,剩下那一对,只有一个是Ph.D,这是个夸张的笑话,但非常真实地告诉了我们Palo Alto 居民的教育程度之高。这些居民的后代,在基因上天生就比别的地方孩子竞争性强。
先生和我就是第四对夫妻:他是Ph.D, 我不是,但我有很强的写作能力,我发表与出版的东西远远超过他。回到90年代的硅谷,还没有出现 Google and Facebook的时代,我家的周末晚餐桌上总会坐上七个白人Ph.D, 唯一不是博士的我,在厨房里做菜,他们会说:整死我们也做不出这种好吃的东西来!
我们和这些人后来都生了孩子,我们和他们的孩子,都很有安全感地开始上学。直到有一天,他们开始吃不消:胡佛小学的华人学生,占了39% 的比率,华裔家长开始抱怨学校的作业分量不够,白人则不允许学校走亚洲结构教育的路线。
那些从六岁到十一岁的孩子,在大人眼中就是国家的未来,为了美国的前途,两方家长展开政治大战,受不了的家庭转学,剩下的继续干。我留了一个孩子在胡佛小学做实验品,将小的孩子转到了以话剧和诗歌教学超强的Juana Briones 小学。
在这场战斗中,华人中出现一个华裔妈妈,工程师,她带领一群中国家长,给PA教育局递交请愿,在PA的小学中开设中文课。几年后,此举成为现实,Ohlone School 是现在设有中文语言教育的学校,但仅此一所。
我则带领其他的中国家长,历史上第一次在Palo Alto以白人为主的公立胡佛小学,成功举办中国年庆祝活动,耍龙,舞狮,跳莲花,扇子,灯笼舞,诵唐诗,吹箫等等,连做三届。英文媒体,中文媒体,都有大肆报道。这个经历导致我对媒体重要性的发现。
九
写专栏
等我的两个孩子都小学毕业上了Terma Middle,我得到了一个写专栏的机会。Palo Alto 一共有12所公立小学,三所公立初中,两所公立高中。当时的Palo Alto Daily News 希望有一个学校事务专栏,就由家长来写。我们五个作家出身的妈妈们,担当了这个没稿费的专栏写作工作,职责是报道与监督。我个人负责Hoover Elementary, Juana Briones, Terman Middle, Gunn High. 我们决定每个月开一次例会。
第一次例会在Crescent Dr ( Crescent Park) 一栋西班牙建筑里,主人是一家上市公司CEO的老婆,房子前院有上百年的红杉树,后院是面积达三亩的花园,游泳池,网球场都是主人设计的。
家中一尘不染,客厅摆放着一张巨大沉重的厚木长桌,家具和一切摆设皆精心设计并兼具美感。这算是我第一次知道Palo Alto 北边的居民与南边的居民生活质量的不同。多年后,中国上市公司“步步高”的CEO也搬进了 Crescent Park, 2012 年,FB的CEO马克·扎克伯格也搬进了 Crescent Park。
我的专栏的编辑叫 Ann Walker, 她的先生 Newman Walker 是PA 从XX年到XX 年的教育总监,也是胡佛小学与阿龙尼小学两所实验小学的创办人。我的每一篇文章都得到了她的校对和建议,在此感谢。
写专栏的这三年,我发现了白人与东方人教育理念的巨大区别。白人尊重孩子,对孩子相当负责,与小孩平起平坐,跟孩子交流以“问”为主,从来不打骂。
华人和印度人,对孩子以“告与教”为主,姿态是从上到下,有的家庭打骂孩子。白种人孩子因家庭问题吸毒,滥交,自杀的人数多于东方人,跟白种人孩子交往的东方孩子受到的影响却正面的多,增加运动兴趣,做事有胆量和创意,独立,对自己的行为相当负责。
在美国,孩子是国家的主人。大街上的乞丐没有儿童和青少年。美国每个家庭的小孩都是父母的神。
今晚,我走进毕业回来家中暂住的女儿大米的房间,她睡着了,我望了她很久,我喜欢她。我的女儿是美国女人,我的女儿是美国的前途。
而我,仍然是中国的女儿,我一生都无法摆脱这种身份。无所谓好与不好,只是我认真用这种经验去抚养美国的未来。


想知道大米是如何度过那段黑暗时期的,网上搜《Know My Name》。
—— 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需经允许。照片来自网络

《北美养娃那些事儿》
立足硅谷,放眼世界。《北美养娃那些事儿》由北美家长分享养儿育女,申请大学,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真实故事。
欢迎关注《北美养娃那些事儿》, 请扫码。

推荐阅读相关教育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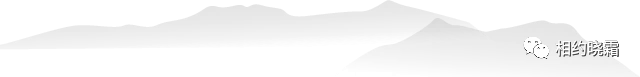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