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敦煌修大佛


记者 | 宋诗婷

下午两三点,瓜州的太阳把整片榆林河谷照得发白,峭壁、砂砾、河道边的几抹绿都像是失去了颜色,一个个面目模糊。语言也被风干了,话一出口,就断裂在日光之下。

唯一能和这白光相抗衡的是李云鹤身上那件比蓝天更蓝的工作服。我们紧跟着他,走出寺院,左转,踩上土黄色的栈道台阶。这条通往三层6号洞窟的栈道要转三个弯,登近百级台阶,今年87岁的李云鹤每天要往返五六次。
老爷子有些喘,跟在后面的我非常喘。气还没倒匀,等在门口的徒弟就推开了那扇深棕色的洞窟门。一个巨大的弥勒佛头出现在我们面前,震撼来得猝不及防。
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距离十几米的位置,以平视的角度与一个宽四五米、高6米的佛头相对。
那弥勒佛眉峰柔和,双眼狭长,好似带笑,丰满的两颊又添几分祥和。站在这样的距离和角度与他对视,内心的震撼无法言语。李云鹤让徒弟们搬了两把椅子,我们在由脚手架搭成的工作区坐了一会儿,试图在短暂的沉默中平整情绪。
工作台上铺展着工程图,佛头、佛身等各个角度的佛像照片。李云鹤拿起一张,带着他60多年都没改变的山东口音对我说:“是唐代的,24.7米,敦煌第三大,榆林窟第一大的佛像。这些彩绘和贴金是嘉庆时候的。工程还没完,下一步就是怎么贴金上色了。”
榆林窟第6窟是建于唐前期的一个洞窟,也是榆林窟最大的洞窟。和莫高窟的96窟、130窟一样,因为有大佛,所以窟顶极高,占据了三层空间。窟前的殿堂,形成了榆林窟唯一一个寺庙建筑。
洞窟的形态是唐代的,但窟内壁画经过历朝历代重绘,如今留存最多的是五代和宋代的壁画。
窟内最有价值的就是这尊大佛了。和敦煌的其他两尊大佛一样,这尊弥勒佛像很可能是武则天时期,营造弥勒大像风气的产物。
塑像依东侧崖体凿塑,再在外层包裹泥制材料,精雕细琢出生动的表情。尽管在嘉庆时期做了贴金处理,但佛像有丰韵的体态,阳刚气质与柔和感完美融合,这些都是唐前期的大佛塑像所独有的。

榆林窟第6窟大佛
因地制宜依附岩体建造,大佛才有如此大的体量,但岩体老化和早期一些保护工程的施工影响所造成的岩体断裂却是不可预测的,这正是眼前这尊大佛所遭受的劫难。
今年是李云鹤在榆林窟修大佛的第四个年头,在他长达63年的文物修复生涯里,这是周期最长的一个项目。

2015年11月,李云鹤刚结束山东的一个修复项目,回到敦煌准备休假。“一天晚上,王院长(时任院长王旭东)给我打电话。电话里语气特别严肃,让我明早8点就从敦煌出发,去榆林窟,他在那儿等我。”放下电话,李云鹤就觉得,事情可能有点大。“榆林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得多着急才要在那儿等我?”
第二天一早,李云鹤从200多公里之外赶到榆林窟,一推开6号洞窟的门,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整面佛头,从耳朵那儿裂开,掉下来,一路刮掉了手臂、下面的佛像、龙柱,掉到两腿之间,太惨了。”提起这个瞬间,李云鹤又心疼地落泪了。
从那天起,他就住在了榆林窟,开始了漫长的修复工作。整个莫高窟和榆林窟加起来有2000多尊塑像,李云鹤修过其中的三四百尊,但难度这么大、价值这么高的还是第一次。在这个年岁遇到,是困难,但这一生能遇到一次,也是幸运。
修大佛最初的两个月,大部分工作都是处理佛头滑落所产生的碎石、水泥片等垃圾。“光垃圾就清理出近70吨。”这些佛像残体被埋葬在戈壁上,大家还建了一座塔,“就在对面,佛头修好后,他就能看到那些残片,一直不会分开”。
点击图片,一键下单【最美敦煌】

佛像的修复工期长,但李云鹤已经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研究材料构成和实验修复方案上了。今天敦煌的文物修复已经全面科学化,保护研究所里设备齐全,从泥料构成到修复所需黏合剂的分子式,都能数据化分析。大佛的修复还用到了三维打印技术,这些新技术是60多年前的李云鹤无法想象的。
“什么是文物修复?那时候我哪知道啊!”刚到敦煌那年,李云鹤23岁,“原本是要去新疆的”。上世纪50年代,国家号召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援助新疆建设,李云鹤也动了心。“去新疆,就顺道把外祖父送来敦煌吧。”因为舅舅的这个嘱托,李云鹤到了敦煌,到了莫高窟。
那时的敦煌研究所,算上行政人员,不过30多人,正是缺壮丁的时候。常书鸿听说有个年轻人来了,就想方设法要把人留下。不仅想把眼前的人留下,他还让李云鹤写信回家,再写信去新疆,多叫几个同学来,因为“敦煌也很缺人才”。

1965年9月30日,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徒步进城经过佛爷庙休息后合影(敦煌研究院供图)
和火热的新疆相比,敦煌太默默无闻了,没人愿意来,除了答应留下的李云鹤。实习期,他被分配的活儿是打扫洞窟。“我们这里每年刮一次风,从大年初一刮到腊月。”李云鹤说,那时的莫高窟,还没有今天加固的外部结构,栈道、栏杆、隔离带,什么都没有。戈壁的风不断卷来新的沙土,拍打在并不坚固的石窟壁上,又敲下更多沙土。每天,李云鹤按照当时的洞窟编号,从最北边开始,顺着号码走个S形,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清扫尘土。这个过程就像是西西弗斯推石头,不断重复,永无止境。
当时,李云鹤对敦煌石窟并不了解,但他看着那些不断被沙土掩盖、侵蚀的底层洞窟,看着东倒西歪的塑像和风一吹就脱落的壁画,还是心疼。在那一片片落下的壁画残片上,他看到了,也听到了时间。
或许是被他西西弗斯式的劳作打动,李云鹤成了当时三位实习员工中唯一留下来的那个。
成为正式员工后的某一天,常书鸿突然把他叫到办公室。“交给你一个任务。”常书鸿说,“这工作你不会做,我也不会,但你可以试试。”常书鸿交给李云鹤的任务是修复壁画,当时,所里几乎所有员工都是学术型专家或者临摹专家,能做文物修复的一个都没有。“不仅敦煌没有,当时整个中国懂这种泥质壁画修复的人也一个没有。”虽然不知从哪儿入手,但李云鹤答应常书鸿“试一试”。
他接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每个普通人都能做的。花了几个月时间,他把每个洞窟里凡是有颜色、有线条的壁画残片都小心翼翼归拢起来,放在洞窟的角落里。别的做不了,就先把那些东倒西歪的塑像用东西支撑住,“起码不要倒了”。
1957年7月,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受文化部委托,到莫高窟进行壁画保护情况考察和研究壁画病害治理方法。那是敦煌第一次有外国专家以壁画修复的缘由来到莫高窟,手头有任务的李云鹤当然不会放过机会,他一直在边上协助和观察,找一切机会偷师。
研究院决定用474窟做修复实验。李云鹤看着外国专家把一种白色牙膏状的东西挤在一杯清水里,搅拌成乳状液体,再用一支针管,吸满调试好的黏合剂液体,往起甲的壁画缝隙里慢慢推。黏合剂渐渐渗入地仗层,专家就小心翼翼地用一层纱布隔着,将壁画粘贴回地仗层。
据说是因为环境艰苦和水质太差,没过多久,捷克专家就回国了,留给李云鹤的是能照猫画虎的一套修复工具和流程方法。一边做着基础工作,他一边开始了修复壁画的各种实验。
先是改良捷克专家的设备,他将条纹较粗的纱布换成了吸水性好又不会在壁画上留下纵横条纹的纺绸,这是在老先生们的美术耗材里找到的灵感。推送黏合剂的针管玻璃棒被他换成了血压计上的气囊,力度和精度更好控制,最初的气囊还是他用一块糖从小孩手里换来的。
从接触到壁画修复的第一天开始,李云鹤就和泥巴打起了交道。直到很多年后,儿子李波继承衣钵,开始从事壁画修复这一行,他让儿子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和泥巴,一和就是三年。到了孙子也一样,不仅和泥巴,所需的泥和水都要自己扛到修复现场。
当时,敦煌没有任何科学修复的设备或实验室。李云鹤就选用不同的泥土,按照尽可能与壁画材料接近的泥土、麦草比例调和,再把实验样本放到戈壁上、屋顶上、气象站晾晒,比较、研究出最合适的材料用于实际修复。“虽然现在有各种设备,非常精准了,但我父亲和我还是在检验前会先摸一摸,告诉实验人员可以重点观察其中某个样本。基本上,检验结果出来后,我们看中的那个就是最合适的,这是常年的经验积累。”李波告诉我。
做了这些准备工作后,李云鹤还是不踏实。他去找常书鸿,说想学学画画,再学学雕塑。“你干什么?是不是想出名,也要去搞临摹?”常书鸿很警惕。“我说,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要给壁画治病,要给塑像治病,我不了解这些东西是怎么做的,用的什么材料,就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病害,我主要是了解这个过程。”李云鹤赶紧解释。
常书鸿一听,放心了,撒手让他去学。先跟着史苇湘先生学了一年画,又和孙纪元先生学了一年雕塑,虽然不精通,但用在壁画和塑像修复上也足够了。

1962年,常书鸿又心事重重地把李云鹤叫过去。“他让我去洞里修一下,161窟,再不抢修,壁画就快落没了。试一试,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李云鹤赶紧接下这个新任务。从答应常书鸿“试一试”,到真正开始修复一个洞窟,他已经为此准备了6年多。
李云鹤向很多媒体和研究者回忆过当年161窟的惨状——一开门,空气稍微一流动,壁画就像雪花一样哗哗地落下来。
在各种对于莫高窟的研究文献中,161窟都是很少被提及的一个。它位于崖面中位置最高的那一层,在拥有莫高窟第二大佛像的130窟的北侧,在著名的张议潮功德窟156窟的正上方。这个开凿于晚唐初期的洞窟在当地民间被称作“观音洞”,因为洞窟壁画是以各种观音造型和经变图为主的。南壁有文殊经变,北壁是普贤经变,西壁中央绘十一面观音曼荼罗,每幅菩萨主画都环绕数十组菩萨海会,窟顶井心还绘有千手观音曼荼罗,四周环绕伎乐飞天。整个洞窟一眼望去,就是数不清的菩萨,气势很是壮观。但因为缺少像156窟一样更具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大幅作品,161窟在名气和研究文献上都弱了很多。
但在敦煌壁画修复领域和李云鹤心中,161窟都是值得被铭记的。1962年开始,李云鹤带着分配给他的两名工作人员常驻161窟。“起甲、空鼓、酥碱……你能想到和想不到的病害,在这个窟里都有体现。”如今的161窟,虽然有不可逆的残破,但壁画里成百上千的菩萨图像清晰可见,虽有褪色,但各种颜色和线条都柔和、顺畅,很多细节依然保存完好。
“当年可不是这样的。”李云鹤说,起甲、酥碱严重的壁画,整个画面都是断裂的,基本看不出内容,再加上常年暴露在风沙和灰尘里,壁画的颜色也几乎看不出。
所有修复工作的第一道工序和医治伤口一样,那就是清洁。他用自制的吹气工具,轻轻吹掉壁画上的灰尘。吹得不能太用力,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把整块壁画吹掉。也不能太轻,否则吹来吹去都不起作用。吹干净后,再用他早年研发的那套注射工具,将注射器靠近壁画,在起甲的缝隙里注入黏合剂。“一次不行,第一次只是让材料浸润、吸收,还要注射第二次,严重的还得有第三次,这样才能粘牢固。”注射好黏合剂后,要让液体风干一会儿,再找准时机,隔一层纺绸把壁画贴回去。粘好后再用软棉球在并不完全平整的壁画表面按压一次,以保证粘合得足够紧密。最后一道工序是检查,要用一个小喷洒筒,往修复好的壁画表面喷水,如果有没粘好的部分,那里会一下子离开地仗层,重新鼓起来。遇到这种情况,之前的几个步骤就要再重复一遍。

2017年10月25日,文物修复专家李云鹤先生在榆林窟的文物修复实验室。
直到今天这个壁画修复已经高度科学化、数据化的年代,李云鹤这套手上功夫都是必不可少的。“数据确实可以准确地告诉你黏合剂的使用量,还有按压力度,但可能每寸壁画的参数都不一样,实际操作中你是没法不断测量的。”李波说。现在他的侄子李晓洋也走了文物修复这条路,他吃洋墨水,也懂整套科学保护和修复理念,但落实到具体修复中,靠的还是这套手上功夫。
修161窟时,莫高窟还没有通电。李云鹤和那些做临摹、做研究的老师傅们一样,靠自然光和镜子、白板的反射光源工作。一起修复的另两个人常常不在,李云鹤总是一个人干活。一把小板凳,几样工作用的工具,洞窟里是没有时间概念的,一个人要面对一面墙,或一个佛像身体的某个局部待上一整天,出了洞子,常常恍如隔世。
161窟所有壁画面积加在一起有60多平方米,李云鹤共花了700多天修复,平均每天不到0.1平方米,可能还够不上小菩萨图像的一张脸大小。
虽然慢,但终归是修好了。直到今天,50多年过去了,161窟依然像当年刚修复完一样。在常驻榆林窟修大佛之前,李云鹤偶尔还会回去看一看161窟,看到它依然完好如初就放心了。

161窟给李云鹤的修复师生涯开了个好头儿,这个洞窟的成功修复也是莫高窟自主修复的开端。李波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渐渐从考古所研究员转型成文物修复师的。“父亲那一代是抢救性保护,人都要死了,先救活再说。后面,包括和美国盖蒂合作,包括父亲他们带着我们这代人,都渐渐开始做科学保护了,到了现在,晓洋这波,就需要有各种监控数据,做科学性和预防性保护。”李波觉得,“老爷子到现在还能工作在第一线,这和他一直在学习新理念、新技术是分不开的。”
采访快结束时,李云鹤带我们去了他在榆林窟的住处。那是一幢修在河谷边的铁皮房子,和所有工地上能看到的一个模样。坐在铁皮房子门口往坡上看,眼前就是榆林窟新建的办公楼,员工宿舍也在那边。“给我留了房间,不愿意住,这儿多好,离吃饭的地方近。”李云鹤指着眼前的一片绿色对我说,“我们还种了菜呢,萝卜、小白菜……”
榆林窟的条件不太好,但李云鹤很喜欢,这里让他想到了过去那些莫高窟没有水、没有电的日子。那时,常书鸿也组织员工耕地、种菜,那是一种只属于开荒者和创造者的快乐。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8期,更多精彩报道详见本期新刊。
实习记者胡艺玮对本文亦有贡献)
大家都在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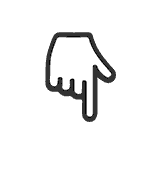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
《最美敦煌》+《我心归处是敦煌》
点击下图,即可一键下单
▼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周刊书店,购买更多好书。
阅读原文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