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花了8万块,买了他爸爸死刑



我不是刻意装逼啊,因为家里有钱的缘故,我结识了不少富二代。
同时,因为家里生意做得比较大的缘故(我真没装逼),商业道路从福建一路铺到成都,当时也在成都居留了一段时间,也就认识了许多当地土豪的孩子们。
四年前回成都时,跟在上大学的朋友们一聚,当时我身穿一件麻油叶图案的短袖,肉正吃到一半,坐我旁边的一个黄毛小哥们碰了下我肩膀,开口问我:“阿潘,你也飞叶子吧?”
我一懵,脸一愣。
黄毛又一抬手:“愣啥呢?你没飞过?”
我赶忙摆手:“没飞过,没飞过…”
发小在一旁,扭过头来一脸震惊地望着我:“啥?你竟然没飞过叶子?”
接下来是一桌人都看向我,他们的表情像在看一个古代人。
我震惊了,没想到飞叶子在这个大学生圈子里已经成为常事,没飞过竟然会被围观。
四年前的成都,经济发展虽然没跟上北上广,但也不至于落后到穷乡僻壤的地步,我朋友们所住的位置在机场附近,高楼大厦四边都是,这么一个地方,吸毒竟就这么肆无忌惮在火锅店谈论起来,毫不避讳。
我连忙移开话题,他们也没继续谈下去。
饭后,黄毛提议上他家里唱歌。
黄毛确确实实家里有矿的,独栋别墅小区,自己安装了一套K歌设备,我们一行人进了房,他却没开机器,径直从柜子里掏出一个铁盒子,掀开,里面整整齐齐全是大麻。
“飞起!”
四周的富二代们纷纷拿起来,见我没动静,黄毛凑了过来,也不说话,往我面前举了举那一盒。
我没动。
发小走过来,笑着看我:“潘啊,来一颗,信我,没事儿!”
我还是没动。
黄毛开口了:“你看我们,哪个像上瘾的?没人上瘾,你试试呗?”
我拿起一根,皱着眉,一些绿黄色被卷起在白纸里,与我平时抽的香烟不同,它连烟嘴都没有。
黄毛点起火,笑盈盈看着我。
你问我那时候心里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我确信房间里没有任何迷药和听话水,他也没有给我使什么套子,我却叼着大麻,往那团火越靠越近。
然后一只大手飞出来,啪的一下把大麻打飞了。
“人家爱飞不飞,关他妈你屁事?”
这个人叫周晗。
我从这一刻开始和他成为朋友。
周晗在这个圈子里活了十多年,整日和他们混在一起,却很难得的没有碰过毒品,后来我在成都的那段时间,没事就找他吃饭聊天,也常感激他那天的大手一挥。
后来我们还是经常聚在一起玩,但飞叶子时他们不再叫上我俩,关系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跟从前一样,平日扯淡开玩笑如旧。

我这才意识到,一部分吸毒者在劝你吸毒时,是他们是真的认为毒品是个好东西,想跟你分享,让你也体会到“快乐”。
就像我看到一个好玩的游戏,一场精彩的电影,一张爱豆新专辑然后分享给朋友的心态一样。
这种不带歹意的劝吸反而更可怕。
有人把麻叶藏在烟卷里,佯装普通烟让朋友抽下,最后笑盈盈地跟你说:
“你看吧,我没骗你,你还不信。”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悲剧的开端,都是毫无歹意的。
所以你永远也察觉不到,跨出的哪一步,就是悲剧的开端。

我问过周晗,跟他们耍了这么多年,是怎么做到完全不碰的。
周晗跟我说:“我从小到大,爸妈什么都不要求我,学习成绩无所谓,逃学上网吧无所谓,早恋叛逆打架斗殴甚至也无所谓,他们只重复一句话,就是别吸毒,从小说到大。”
那时候我们把飞叶子当成一个梗来玩,我俩在网吧通宵打游戏,新装备一出他就买,一两万的往里充钱,充完对我一笑:“你看,飞叶子多垃圾,还是打游戏费钱!”
我说:“费钱?你他妈隔两天就充一万,你这叫他妈烧钱……”
游戏里有个土豪排行榜,他长居第一,每次刷新排行榜,看着自己一点点往上升就一脸满足。
我说这破游戏你玩多久了?
周晗很自豪:“八年了,从小学玩到现在,天天玩。”
我说赶紧卸了吧,这么玩下去明年你家就得败光了。
他很冷静地看了我一眼:“不会,我算过,要七十年。”
我沉默了一会,周晗又一拍脑袋,拿出兜里的保时捷车钥匙:“还有四辆车可以卖,应该不止七十年吧!”
那天通宵完,我第一次去了趟周晗的家里,也是第一次见到他妈妈。
周母见我们大清早回到家,赶忙从厨房拿出早餐来,周晗一甩手:“妈,我俩不吃,我俩要睡觉,刚通宵完。”
周母笑,说:“怎么又去网吧瞎玩!别把人家小潘带坏了!”
那时候我没想到,第一次见周母,也成了最后一面。
我们俩从床上爬起来时已是下午,周母见我们醒来,准备出门买菜做晚饭。
当天我家里有事要赶回家,周母便开车送我回家,我下车时,还让我常来家里玩。
我一口应允。
没过几天,我们全家便搬家去了北京,并在朝阳区定了居。
后来和周晗联系才知道,那天晚上,周晗没等来他妈妈,却等来了两个警察。
他的妈妈在高速公路上被警车别停,然后手铐逮捕,直接送进了警局。
这一别,就是四年。
家中所有财产全部没收,周晗还剩一辆十万块的车。
警察说:“你爸妈贩毒。”
周晗拍桌子:“我爸妈怎么可能贩毒!”
警察也拍桌子:“那他们是干什么的?”
周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父母从来不告诉他家里的生意是什么。
周晗就等判决书下来,等了四年,最后母亲还是被定了死刑,枪决。
有关系的人告诉周晗:“你爸把所有的罪都推给了你妈,你妈全接受了。”
“为什么?”
“不然两个都得死刑。”
“那现在我爸呢?”
“等判决书,可能还是得死刑。”
周晗不知道是哪天执行的,只是突然有一天就被通知去领骨灰。
到了地方才知道,骨灰盒是要买的,最便宜的两千,最贵的八千。
他连二百都没有。
给我打来电话借钱,给身边的几个富二代打电话借钱,几个人转过去,一万块,他买了最贵的。
他一个人把骨灰盒整理好,朋友有些担心,请他来家里吃饭,发现他一往如常。
“我好像没什么感觉,我已经不记得我妈长什么样了。”

朋友们拍拍他的肩,从兜里拿出叶子继续飞,周晗开车回家——现在的家是地下室,潮湿阴暗,蟑螂四处。
那段时间我爸妈也听说了这件事,让我立刻与周晗断绝往来——他们之前完全不知道周晗父母是贩毒的,我被父母逼得只能和他断绝关系。
后来再去成都,见到周晗,他正在卖那辆剩下的车。
他没怪我,只跟我说好久不见。
我歉意地挠头,问:你卖车做什么?
他说车卖8万,有人可以用8万让我爸不被判死刑。
我跟他一起卖车,把钱给那人转了过去。
然后那人跑了。
紧接着,他爸的判决书下来了。
死刑。
周晗大喘了一口气,面无表情地呆坐在木椅上,一整个下午。
到了晚上,我拿着外卖拎到他眼前,晃了晃。
他回头看我,说了句:
“在毒品这,七十年,过得可真快啊。”

“我爸妈是坏人吗?”他问我。
我沉默了一会,说:是。
周晗:“我也觉得是。”
那会正是毕业期,他从大二开始的学费全都是那群吸毒富二代们凑的。
毕业会结束后,我们一群人又聚在一起,大家说去网吧打会儿游戏,开了机子,他在沙发上发呆。
我问说,你那游戏不玩了?
周晗说,号早卖了。
周晗说:“幸亏卖得早,还能值点钱,现在这游戏都没人玩啦。”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低头陪他一块发呆。
网吧玩到半夜,还是那个熟悉的黄毛,站起来提议,上家里唱歌喝酒。
他又拿出一盒大麻,分着。
房间里甚至来了一群高中生,男男女女,扎着耳洞的,也有戴着眼镜的书呆子,接过来就开始嘬。
有一两个看起来完全没碰过的,甚至都不知道烟该怎么拿,被他们的朋友或闺蜜现场教会了。
“你看我们,哪个像上瘾的?没人上瘾,你试试呗?”
跟四年前的场景一模一样。
穿着校服的孩子,呛一口,呛两口,第三口就会了,瘫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有的开始发癫,有的还在唱歌,有的脱了衣服装疯,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大麻草的腥味。
我过去制止时,被本人呛:“关你屁事?”
原来他们是主动想学的,主动结交富二代,主动吸毒,主动成为社会人,以让自己在学校里混得开,受到大哥们的庇护。
吸毒多社会啊。

黄毛绕了一圈,转到我们俩面前来。
铁盒一伸,冲着周晗:“周晗,飞一颗。”
周晗往后缩了一下,没吱声。
黄毛一皱眉:“不给面子呀,你学费都是我们哥几个凑的呀!”
周晗咬着牙,拿起一颗。
黄毛咧嘴一笑,点起火来。
火碰到叶子的那一瞬间被我拍飞,我抓起黄毛衣领:“人家爱飞不飞,关他妈你屁事?”
几个高中生站起来,冲来想帮他们的“大哥”出头,其中一个飞猛了,还摔倒在地上。
周晗冲我摆了摆手:“没事儿潘,我飞。”
他点起叶子,猛嘬一口,然后哈哈大笑。
混着草腥味的雾从他嘴里喷出来,盖着他的笑容,融入四周的人群。
叶子灰落在沙发上,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来他借钱买来的骨灰盒,里面放着他妈妈的骨灰。
骨灰没温度,烟灰有。沙发被烫了个洞,露出焦黑,我看着那颗洞,手臂还停在空气里,一时不知该往哪儿放。
他终究是飞起了叶子,可没人再来管他了。
或许越是对一个东西恨之入骨,就越容易堕入其中吧。
而可悲的是,长大成人,周晗靠的却是厌恶了一生的东西。

回到北京没几天,传来一屋人被抓捕的消息。
周晗也在其中。
几个高中生被退学,他们的刚毕业的学历作废。
后来我去过许多次成都,直到今天,我依旧能闻到那股草腥味。
有的藏在酒吧里,有的发生在校服上。
他们学着流氓的模样,说:“叶子算什么,现在都打针。”
不知道打针指的是哪一种,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真还是假。
有些不太敢飞叶子的,开始学打气球。
买各种英文名称的气弹,成箱成箱地往柜子里搬。
我小时候,逃课去网吧通宵打游戏,饿了叫份泡面自己煮,累了回家睡大觉。
现在的孩子们躺在家里打气球,成宿成宿地飞,飞出毛病的人比比皆是,还不知回头。
混上道了,还学着自己卖。
放进踏板摩托的车座下,人模狗样地找人交易转账,学电影里黑帮们的风流,琢磨街头暗号。
我采访的时候,他们眉飞色舞,似乎对吸毒这件事了如指掌。
有人连叶子是什么都不知道,但也要强行装懂。
谁在让他们变坏?
我不知道,我也调查不了那么深,我更不可能去追随毒品的根源,我只是个普通人。
我只能用力拉住身边的朋友,让他们把叶子放下,或者以绝交相逼。
我原以为我能拉住周晗,可我错了。
后来我知道,毒品的重量,对我和对他来说不一样。
我不知道对周晗来说,这算是解脱还是更沉重。
一根烟草对我来说只有几克重。
可对周晗来说,这等于七十年,也等于父母亲。
他知道贩毒即是坏,有人因它而堕落,也有人为它丧命。
所以他没埋怨过这个世界,也从不抵抗。
很多年后,我依旧会想起与他成为朋友的第一天,他皱着眉拍飞那根我眼前的大麻烟,一脸厌恶又指着黄毛破口大骂的样子。
那时他身子笔直地站在我身前,像守卫城池的英雄一般。
往 期 推 荐
(点击下图即可看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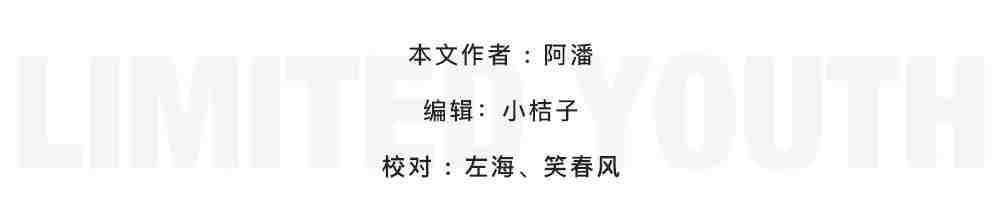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