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企业垄断怎么破?听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怎么说


技术进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随着大型科技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都变得越来越大,随着隐私问题加剧和假新闻泛滥,我们逐渐意识到,赋予科技公司不受限制的权力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过去,监管机构可以通过分拆公司或对业务进行公用事业化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科技巨头迄今还未曾有过分拆的经历,即便很多人和决策者都感到应该做点什么——但到底该做些什么呢?又该怎么做呢?
这种形势下,2014年诺贝尔奖得主 Jean Tirole 的见解就显得尤为重要,他是市场力量和监管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梯若尔最近出版的新书《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就科技行业的竞争和垄断,如何思考技术改变经济的方式,以及我们可以对此做些什么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以下为 Tirole 在接受线上媒体 Quartz 杂志采访时,对一些如今比较紧迫的问题发表的看法,或许能给身处科技世界的我们、给监管机构一些有益的启示(内容经编辑有删改):
· 科技行业在发展早期,给人感觉会形成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即使是小型企业,也能以很小的成本,覆盖数十亿人。可实际上,竞争似乎变少了。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已经完成了使命。
小型企业在很多方面获得了赋权,它们可以享用便宜的后台和云服务;它们可以轻松地与消费者建立联系;它们可以精准地投放广告,而不是无的放矢地进行大规模宣传;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贷款机构为它们的借贷提供了便利,就像中国的蚂蚁金服为700多万家中小型企业提供服务一样。
而且,重要的是,它们可以更容易地打响自己的名声。以往,出租车司机要依靠出租车公司的名声;如今,通过评分机制,司机可以在打车软件平台上建立自己的声誉。
但在平台层面,规模收益和网络外部效应的存在,对竞争构成了挑战,导致了自然垄断和赢者通吃的局面。

网络外部效应可以是直接的:我使用 Facebook 或 Twitter,是因为你也在用;如果很多司机在为 Uber 或 Lyft 开车,那么我就会用它们打车。网络外部效应也可以是间接的:我们也许不会直接关心平台上其他用户的存在,但这种存在能够让平台的服务得到提升,很多应用程序或外送服务都存在这种情况。
举例来说,如果你使用谷歌搜索引擎或 Waze 交通导航应用,那么我也会想使用它们,因为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这些服务所做预测的质量会获得提升。
自然垄断局面能够带来广泛的市场力量,并伴随着一种意愿,即通过长期亏损来「购买」未来的垄断前景。在此,你可以想一想亚马逊或 Uber。
· 像谷歌、亚马逊和 Facebook 这样的科技公司,它们形成垄断了吗?
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静态和动态,或者是瞬态垄断和永久垄断。庞大的规模经济以及强大的网络外部效应意味着,新经济中会经常出现垄断或高度寡头垄断。
关键问题在于「可竞争性」。垄断不是好事,但只要潜在的竞争使他们保持警觉,他们就会给消费者带来价值。如此一来,他们将被迫进行创新,甚至可能收取低价,以便维持庞大的用户基数,同时也让新入者难以撼动自己。
但要让这样的竞争机制运转,有两个必要条件:其一,有能力的竞争对手必须能够进入市场;其二,在能够进入时,切实进入市场。

在实际中,竞争对手可能很难进入一个市场。而且,就算成功进来了,他们或许会觉得,与其和现有的市场领导者竞争,不如被其收购,这样更有好处。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种「为收购而进入」的做法几乎不会创造任何社会价值,因为实际上,这只是新入者从市场领导者那里分得一杯羹而已。
· 十年前,沃尔玛似乎在零售领域掌握了垄断力量,但后来,市场为我们带来了亚马逊。如今的科技垄断企业有朝一日也有可能面临激烈的竞争吗?
是的,别忘了谷歌在搜索引擎市场取代了 AltaVista,Facebook 在社交网络领域将 MySpace 挑落马下。
沃尔玛和亚马逊都高效地利用了与采购、物流和配送有关的规模收益。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就是垄断企业,而是说,零售行业出现大型企业不足为奇。
沃尔玛占据主导地位得益于激进的成本削减;亚马逊能够变革市场,是因为其互联网模式进一步为消费者带来了便利。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我们必须从动态角度去分析行业,而不仅仅是静态视角。
再说一次,这里的关键在于,一个能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新入者,它在进入一个市场时的难易程度。
· 那么,潜在的进入壁垒是什么呢?
这通常涉及小众市场。
还记得吗,亚马逊一开始只是在线书店,而谷歌起初仅仅是一个搜索引擎。之后,新平台可能构建起完整的产品线、进行扩张,与占据主导地位的平台展开竞争。
不过,现有的主导平台可能通过技术或营销捆绑,给最初进入小众市场的竞争对手制造障碍,比如表现出对自家服务的偏好,或是用忠诚度折扣打价格战,或是采用其他打击新入者的手段。
此外,用户不可能同时使用多个同质化平台,这也让进入变得更加困难。如果用户能够把个人数据从一个网络轻松迁移至另一个网络,那么,切换到新的社交网络就会变得更容易。

如果现有的打车平台不讲究排他性,那么进入网约车领域,就会变得更容易。
· 你认为科技垄断弊大于利吗?谁在为它们造成的弊害付出代价?如今,科技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很低,甚至是免费使用,这种局面不同于以往的垄断。这有没有改变我们考虑或定义垄断力量的方式?
是的,总的来说,消费者往往能够占到便宜,因为我们是在免费使用一些出色的服务,比如谷歌搜索引擎、Gmail、YouTube 以及 Waze。
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我们提供给平台的宝贵数据,我们并未得到报酬,这一点,Eric Posner 和 Glen Weyl 已经在他们的新书《Radical Markets》中提醒我们了。
不过从整体而言,我们的生活水平因为数字革命而得到了大幅提升。不过我们应该记住的是,这些都是双边市场。例如,消费者的另一边是广告商,他们会支付大笔费用,来获取定向推送广告的能力。所以,仅仅分析消费者这一边是不完整的。
· 市场力量是否为监管提供了正当理由?如果是这样,传统的监管方法能够提供解决方案吗?
旧式监管很难找到立足点。首先,考虑一下公用事业型监管,一个世纪以来,这种方法一直主导着电力、电信和铁路行业的监管。这种监管方法试图规范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中的利润。
例如,服务成本监管着眼于已知的成本,通过设定价格,来确保公司能够收回成本。但要在科技行业实施这种监管方法,是非常困难的,尽管科技行业跟公用事业一样,具有很高的固定成本(真的非常高,因为向最终用户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通常为零)。
为了收回成本,我们必须进行估测,并把估测中低到看不见的成功概率考虑在内。由于大多数平台都会失败,因此收回成本需要一笔不可忽视的利润,但到底需要多少利润,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在这里,制药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类比:同样固定成本高昂,成功概率极低,边际成本也很低。
而衡量和测算相关的问题增加了这件事的难度。一方面,市场上有很多潜在的未来主导企业,监管机构无法在其初创阶段就监测它们的支出。第二个问题在于营收方面,这与平台活动的国际化性质有关。
那些平台已然精心挑选了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数据,等等)的注册地,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纳税,它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来摆脱公用事业型监管。总的来说,公用事业型监管似乎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 那么分拆科技巨头的办法怎么样?
把它们分拆开来,本身没有什么不妥,但只是为了弱化企业的力量而进行分拆,那可能无法实现我们的目标。例如,把 Facebook 分拆成五家公司,这对解决隐私问题不会有什么作用。
过去,我们分拆过标准石油(Standard Oil)、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铁路和电力系统。对于互联网平台,我们需要做更多的思考。首先,实施资产剥离需要时间。
1984年那时候,铁路、电力以及大部分的电信业,都只有简单而稳定的技术。相比之下,目前的平台正在快速演化。我们必须确保,干预措施在实施的时候不会已经过时。
其次,我们需要应用经济推理。要分拆一家企业,我们必须找出其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关键设施,也就是,将之与潜在竞争性细分业务区分开来的设施,并确保,该设施不会再次垄断那些潜在竞争性细分业务。
有两种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限制业务线,或是对关键设施的公平访问进行监测。我们能够把一家电力公司分拆成相对明确的若干业务板块,比如发电、输电和配电,其中输电网络是显而易见的关键设施。同样,铁路系统中的铁轨和车站,明显是竞争对手无法轻易复制的设施。
我们假设,我们把谷歌的搜索引擎确定为关键设施,并将它从 YouTube、Waze 和 Gmail 当中分离出来。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了从其他服务收集的数据,搜索引擎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高效地回复我们的查询请求。总的来说,如果要让结构性补救措施发挥作用,那么在采用这些措施之前,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考量。
· 那么,反垄断措施应该如何发展?
首先,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反垄断决策中的举证责任。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
想一想 Facebook 对 WhatsApp 和 Instagram 的收购。它们跟 Facebook 一样,都是社交网络。它们本可以成为 Facebook 的竞争对手。但这有证据吗?不尽然,因为这只是在没有发生收购的前提下,我们对未来情形的一种猜测。
在缺乏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去证实竞争受到了抑制。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站在竞争的一边,同时认识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犯错。
其次,经济学家必须帮助反垄断机构发现有害行为,并设计出简单的补救措施。例如,最优惠价格保证(也称最惠国或价格平价条款)确保了消费者在使用平台时,能够从商品或服务的最低价格中受益。

正如我在《公共利益经济学》中所解释的,经济学家已经证明,这种看似良性的行为可以让平台从商家那里收取大笔费用,因为后者需要平台来接触目标消费者。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一些课题做更详细的研究,例如数据所有权和数据进入壁垒。
再次,管辖权问题在数字经济中变得更加尖锐了。我们必须坚持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能基于任意的行业分类和特定的行业法规而对不同的竞争者实施不同的监管。
例如,传统媒体在编辑责任和广告方面,就比社交媒体更受限制。此外,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提升效率,我们还必须对知识产权和税收问题进行国际协调,并确保跨国公司不会受到大量异质、不连贯的区域性监管法规的影响。
最后,我们必须更多地使用更具响应性的措施。传统方法的缺点众所周知:自我监管倾向于自我服务;竞争政策的出台往往过于缓慢;而公用事业型监管,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不具可行性(而且有时反而会受到束缚)。
我们必须发展我所说的「参与式反垄断」,即由行业或其他各方提出监管草案,反垄断机构给出意见,在提供法律确定性的同时,也允许某种程度的灵活性。
我们必须接受犯错的可能性,当监管机构从错误中学习并逐渐调整指导方针时,监管创新也必然会随之演进。正是因为这样的适应性政策,专利池才得以回归,测试新商业模式的监管沙箱也应运而生——这些新模式既不受现行监管法规保护,也不在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之内。
翻译丨何无鱼
校对丨李莉
来源丨Quartz
相关阅读推荐

点击图片查看完整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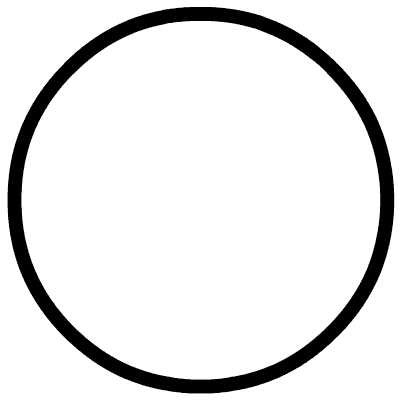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