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瞿秋白《多余的话》探讨革命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困境和精神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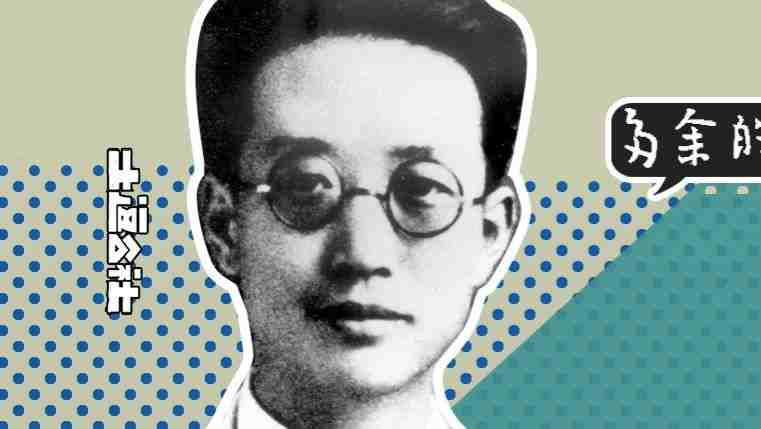


“……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蛻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
(……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瞿秋白《多余的话》
作者 | 叶舒芒
编辑 | xd
美编 | 黄山
微信编辑 | 侯丽

一九三七年,上海刊物《逸经》的第二十五至二十七期刊载了瞿秋白就义前最后的一份写作《多余的话》。此时,距离瞿秋白牺牲已有约两年。由于《多余的话》的手稿一直未见天日,这份文稿的真伪自刊载开始就饱受争议。同样饱受争议的还有瞿秋白在文稿中表现出来的政治立场。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承认,自己是一个因为“历史的误会”而勉强做了十多年政治工作的文人。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始终没能完全战胜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自我,甚至认为自己已经离开革命同志的队伍很久了。在人生即将抵达终点的时候,瞿秋白并未高喊激昂的革命口号,而是坦言自己“需要休息”。[1]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这些表态成了瞿秋白革命立场不够坚定的证据。在这篇文章里,我试图从《多余的话》的文本出发,去探讨一个横亘在所有革命知识分子面前的精神困境:革命知识分子的革命自我与知识分子的阶级身份之间的矛盾应当如何处理?我认为,《多余的话》反映出来的并不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必然悲剧,而是一种知识分子习惯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自我剖析”——的根本局限性。

革命知识分子的双重自我
对于今日的不少学生出身的社会行动者来说,阅读瞿秋白的写作很容易产生共鸣,这是因为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上,可能少有人能像瞿秋白这样清晰地反映“革命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的内在张力。瞿秋白出身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幼年家道中落。一九一六年瞿秋白的母亲金璇因不堪落魄而自尽时,瞿家甚至无力筹钱安葬。一九一九年瞿秋白投身五四运动,一九二零年他加入李大钊与张崧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同年又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前往红色革命之都莫斯科进行采访。从瞿秋白的青年时代开始,革命者的身份与他的知识分子出身就交缠在一起,这两重自我之间的挣扎也始终困扰着瞿秋白。文学评论家夏济安因此说:
(瞿秋白的)这两种人格都需要专一的忠诚,但是对之投入相同的经历是不可能的。一种冲动是要追随自己天性,满足自己对温和、柔情、美丽的物件和舒适的氛围的渴望。而另一种冲动则是追随理性,做理智认为正确的事情,毫不迟疑地从整体上来接受革命,接受革命所伴随的严酷、丑恶和变态。[2]
从这种视角来看,瞿秋白在就义之前写下的《多余的话》仿佛给这两重自我的碰撞书写了一种结语。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透露自己在这双重自我的漫长纠缠中感到深深的疲惫。他激烈地批判自己身上所有的布尔乔亚特质,却又无力地承认自己从没有决心和勇气去彻底地摆脱自己的“绅士意识”。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文人,他是因为“历史的错误”而被卷入布尔什维克革命当中。但固然他从来嫉恶,却也从没有做侠客的勇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甚至庆幸自己最终可以终结这两重自我之间无休止的斗争,即便其代价是“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死亡。[3]

这些表态给瞿秋白的历史评价一度带来了巨大的争议。由于《多余的话》的原稿从未面世,因此连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也难以确定这份写作是不是由瞿秋白亲笔写下,或者有没有遭到篡改。直到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写作《回忆秋白》时,杨之华对这一文本的真实性仍然抱有怀疑。文革期间,《多余的话》成为了批斗瞿秋白和杨之华的重要“罪证”。瞿秋白被定性为叛变者,《多余的话》则是瞿秋白“变节”最重要的罪证。瞿秋白“为了活命”,“把自己参加革命的历史统统说成是‘不幸’,是‘历史的误会’,是‘不得已’的。”[4]杨之华为瞿秋白辩护,主张《多余的话》受过国民党篡改,则被指是为了保护变节的丈夫的身后形象。[5]
这些争论本质上正是在延续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瞿秋白的双重自我之间的对抗。瞿秋白的批评者认为,《多余的话》证明瞿秋白的激进自我最终未能战胜他的布尔乔亚自我;瞿秋白的辩护者则指出《多余的话》的特殊语境,以此说明瞿秋白在写作时所必须采取的策略,以及文稿真实性的可疑之处。换言之,在文革的语境里,瞿秋白的批评者和辩护者实际上共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如果《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内心反思的真实流露,那他的革命性就会被折损,他的革命忠诚也因此需要被质疑。
在文革之后,对《多余的话》的研究逐渐偏离了这一前提。八十年代之后,《多余的话》由一种政治斗争的文本和研究对象,逐渐转换为一种精神分析的文本和研究对象。研究者们希望跳出政治批判的桎梏,去还原革命人物在社会历史环境的压迫下所需要进行的精神斗争,从而丰满革命者的形象,由此诞生了一系列为瞿秋白绘制精神肖像的研究。[6]
这个转向实际上搁置了《多余的话》所折射出来的核心政治问题,亦即革命知识分子的两重自我之间的矛盾究竟有没有处理的余地的问题。对于和瞿秋白遭遇相似困境的今日的行动者而言,这样的研究即便能带来一些精神和情感上的共鸣,也难以帮助他们处理这个困境。当然,要着手处理革命知识分子双重自我之间的矛盾,我们首先要理解瞿秋白本人是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个矛盾的。

“自我剖析”与知识分子的阶级局限性
瞿秋白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位置这个问题早有反思。一九二四年,瞿秋白在《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一文中指出,尽管在社会生产力欠发展的历史阶段里,知识分子往往能代表社会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也因此肩负一些政治参与的责任,但长远来看,“智识阶级终究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7]这是因为在瞿秋白看来,无论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旧知识分子,还是新时代里在新经济体系下成型的新知识分子,终究是寄生在生产者之上的。知识分子因享用着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才能获得“代表社会文化”的地位。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可以担负先锋的工作,但即便是担任先锋,知识分子也往往畏缩,怯于承担责任。
这并不是瞿秋白第一次进行这类思考,他的这个判断无疑源自更早之前对自己的反思。一九二二年,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前往莫斯科。在漫长的旅途中,瞿秋白写下了《饿乡纪程》这份交错着旅行日志和个人反思的纪事。他承认自己旅俄的初衷并非为了崇高的社会理想,而是为了适应自己精神上的好奇心。他同时反思自己这种对精神生活安宁和物质生活安俭的追求,也意识到“理想的天国,不在于智识阶级的笔下,而在于劳工阶级实际生活上的精进。”[8]到达莫斯科之后,瞿秋白近距离地观察了十月革命之后的苏维埃政权,他同样清醒地意识到俄国智识阶级的怯弱:在社会真正需要知识分子承担责任时,他们反而抛弃人民纷纷出逃。瞿秋白的这些反思透露出一种清澈的真诚:他早早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出身对自己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的塑造,并在后来十余年的人生历程里持之以恒地进行着这样的反思。

瞿秋白
瞿秋白的这些反思折射出革命知识分子这个身份在革命叙事和革命实践中的独特地位。一方面,在大部分社会格局里,知识分子在经济上都依赖于更底层的劳动群众。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出发,知识分子囿于其布尔乔亚阶级属性,难以真正肩负革命重担,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革命中也有其独特的功能。敏锐的知识分子有时能先人一步感受到社会中的结构矛盾,独特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也使知识分子能够掌握一定的发声渠道来揭露这些矛盾。换言之,知识分子的智识储备和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都有可能成为革命动员中的核心力量。也正因此,瞿秋白在《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中才肯定了知识分子在前动员时期的作用。
思考和分析往往是知识分子探测社会问题的核心工具。尤其是像瞿秋白这样有良知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在思考和分析社会的结构矛盾时,不会忽视自己本身也是不平等社会结构的受益者,而是会将自己也视为自己的批评对象,视为结构矛盾的一种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分子仿佛比其他阶级更能理解自己的获益者身份,也仿佛更能意识到自身的阶级局限性。
然而对于坚持阶级视角的唯物主义者而言,矛盾之处在于,如果通过反思就相对轻易地能使人看清自己的阶级局限性,进而使人置身于阶级局限性之外,那阶级局限性又何以成为局限性?尤其是对于立志于动员群众,使群众形成有自我意识的行动阶级的革命者而言,他们往往认为人人都有成为知识分子的潜质,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具备自我剖析的能力的潜质。如果反思就能使人置身于阶级局限性之外,那仿佛就是说人人都有远离阶级局限性的可能。这和唯物的阶级视角背道而驰。阶级局限性之所以被称为局限性,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它限制了阶级个体的发展轨迹,使同属一个阶级的不同个体的性格特质、思想观念和行为符合某种规律。但另一方面,阶级局限性之所以难以被超越,正是因为它本身是阶级个体身份认同的核心组成部分。辩证地看,阶级局限性在一方面是限制阶级个体的桎梏,在另一方面同时也很有可能正是该阶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使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区分开来的特质。
从这个角度来看,瞿秋白所坚持的“自我剖析”正是革命知识分子的阶级局限性之一。清醒的自我剖析当然并不总是无益的。如上文说的,具有自我剖析能力的知识分子能更明确地意识到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对自己的塑造,从而更准确地理解和诊断社会的问题。但一个以革命实践为理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必须意识到,这种自我剖析的能力同时也会限制他们的发展。具体来说,通过自我剖析甄别和诊断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病症”——例如瞿秋白说的缺乏勇气的性格、“调和主义”的作风、追求精神安宁的理想等等——并不能通过自我剖析来解决。一味沉浸在自我剖析之中无助于革命知识分子处理他们的知识分子自我和革命者自我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无法在个人的维度上得到处理;只有在一个更宽阔的、共同体的设定中,精神困境中的革命知识分子才能看到一线曙光。

革命知识分子的精神出路
在《多余的话》的最后一篇《告别》里,瞿秋白与他的革命事业、革命战友以及纠缠他一生的精神困境挥手作别。他这样总结他这一生的教训: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细微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9]
许多与瞿秋白相似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都曾指出,革命者在革命共同体中的形成情感纽带与前革命时代的社会关系截然不同。格瓦拉就曾说:“建设共产主义,那就要在缔造物质基础的同时缔造新人。”在格瓦拉看来,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个体具有双重属性,他既是单独的人,又是集体的一员。革命者的集体关系,既有他从自己的阶级出身携带而来的旧社会关系,也有他在新的革命共同体里形成的新社会关系。意识到这一点,格瓦拉认为“应该干脆承认(革命者)是不完善的,是非制成品。昔日的包袱转移到了现在个人意识当中,必须不断地进行工作,来根除这些包袱。” [10]
格瓦拉的论述仿佛在给瞿秋白,以及所有和瞿秋白陷入相似精神困境的社会行动者提供一条并不容易但有希望的前路。和瞿秋白一样,格瓦拉认为革命者的身份既有其崭新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会从非革命关系里继承下来一些“包袱”。同样地,格瓦拉也认为,新形成的革命关系需要逐步地取代非革命关系的包袱。但格瓦拉明确地意识到,“新人”的塑造只能通过建设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作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有意识的自我教育当然是重要的,但个人的自我教育并不能替代在社会实践和革命实践的教育。

切·格瓦拉
换句话说,格瓦拉的“新人”只能从运动中来,到运动中去。革命知识分子需要将自己放置在从革命运动中形成的崭新的革命共同体里。在这个革命共同体中,革命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的特质、弱点和局限性,都可以被策略性地部署。在这个革命共同体中,自我中心式的“自我剖析”才可能被淡化,因为只有在运动中形成共同体式的革命自我,才能使知识分子把那种布尔乔亚式的对“小我”的关注转化成对共同体命运的关注,也才能从不断的自我剖析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将知识分子的出身、精神气质、特长、弱点和局限性都理解为服务于革命事业的工具,从而从知识分子自我与革命者自我的不停斗争中解脱出来。
自我剖析的能力使革命知识分子能更清楚的看到他们的精神困境,但也正是自我剖析的能力限制了革命知识分子处理这个精神困境的能力。因此,比起来自其他阶级的革命成员,革命知识分子可能更需要意识到,“寻求内心的精神安宁”是革命知识分子不会有结果的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知识分子必然要被无休止的焦虑、自我怀疑与抑郁所吞噬。即便如格瓦拉所暗示的那样,这样的精神困境不会有一个完整的、彻底的解药,但革命知识分子仍然可以在有限的空间里,以自己有限的能力,在新自我和旧自我的冲突中找到一条艰辛但光明的出路。
注释:
[1]瞿秋白:《多余的话》,译林出版社,2012,第9、12、37页。
[2] 夏济安:《瞿秋白:一名软心肠共产主义者的炼成与毁灭》,收录于《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获取于https://www.douban.com/note/546749834/。
[3] 瞿秋白:《多余的话》,译林出版社,2012,第38页。
[4]《瞿秋白是一个大叛徒》,《文革简讯·讨瞿专号》,总第四期,1967年1月15日。
[5]《此地无银三百两》,《文革简讯·讨瞿专号》,总第十期,1967年2月7日。
[6] 除了夏济安的研究之外,还可参见海青:《〈多余的话〉与瞿秋白躯体的历史意象》,《史林》,2009年6月,第130-140页;刘岸挺:《忏悔的“贵族” “贵族的忏悔”——再论瞿秋白〈多余的话〉》,《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0卷第6期,2004年11月,第32-36页等。
[7] 瞿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 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1,第4页。
[8] 瞿秋白:《赤都心史》,东方出版社,2015,第53页。
[9] 瞿秋白:《多余的话》,译林出版社,2012,第38页。
[10] 切·格瓦拉:《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guevara/marxist.org-chinese-che-19650411.htm。

本文首发于土逗公社
转载请联系土逗获得内容授权
喜欢这篇?
扫码赞赏


漫画:发条

阅读原文,赞赏“土逗”~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