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同性平权运动丧失激进性了吗?



原图出自: richardmagazime.com
作者 | Cole Stangler
翻译 | LiVE
编辑 | xd
美编 | 黄山
微信编辑 | 侯丽

1968年5月,由于警察的镇压,法国全国兴起了一场大罢工。在巴黎索邦大学占领运动的初期,几名学生在主会场外的墙上挂了一张挑衅的海报。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画像中,出现了一个“男同性恋革命行动委员会”(Revolutionary Pederastic Action Committee)的宣传单。这个仅存在于书面上的组织谴责对“性少数群体”(erotic minorities)的镇压,并呼吁“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等”去自由表达自己。
除了在工厂和街道上的行动,1968年的5月也是深刻反思社会弊病的时刻。尽管法国的抗议运动迅速消退,但其批判精神仍在燃烧。当数百万人一起罢工时,必然会发生的情况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注意力转向了性、对性的压抑,以及最终关于性的政治行动。虽然1968年的各种“大事件”已被大量的笔墨书写了出来,但是LGBT的平权仍然1968遗产中被低估的一部分。
长期的左翼活动家兼作家Daniel Guérin是在1968年5月余波中出柜的人之一。正如他在1972年出版的《青春自传》(Autobiography of Youth)中所写的,这场运动“让许多同性恋者与自己和解”。在公开场合公然反抗之后,再继续为了妥协于现有社会秩序而隐藏自己的性偏好,似乎是太愚蠢了。
1971年,活动家们创立了第一个明确致力于法国同性恋事业的组织: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Homosexual Front for Revolutionary Action (FHAR))和Red Dykes (Dyke在俚语中指女同性恋)。后者本身就是FHAR和妇女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MLF))的产物。这些名字如今听起来可能很古怪,但它们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政治动荡的程度。

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FHAR)
由于一个全球超级大国的经济陷入停滞,人们的政治想象不断膨胀,罢工愈演愈烈:工人们纷纷谴责流水线上的低工资和压榨灵魂的劳动;移民活动家反对种族主义和恶劣的居住条件;毛派、托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将目光投射于一些此前在政治领域之外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和囚犯的恶劣生存条件。法国《世界报》定期连载一个名为“抗辩”(contestation)的专题板块,记录每天的罢工和抗议活动。对许多这些运动的倡导者来说,社会主义革命似乎触手可及。
于是,刚刚政治化的同性恋者开始通过这些抗议的镜头来思考他们自己的痛苦和被剥削的处境。对他们来说,消除对同性恋的歧视与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不相容的。他们没兴趣去影响政客,也没兴趣去赢得选票。他们认为自己正在为性别革命奠基,而这场革命将和即将到来的政治起义一同降临。
在法国左派的传统中,同性恋活动包括出版报纸、游行和制造混乱的公共活动。FHAR的联合创始人Guy Hocquenghem编辑了1971年4月版的Tout!(Everything!)特刊,专门献给同性恋。在这份报纸的版面上,同性恋活动家们要求“自由堕胎、避孕”和“同性性行为以及所有性行为”的权利。

Tout!和FHAR出版物L'antinorm的封面,中间即为1971年4月刊
他们参加了5月1日在巴黎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游行,有一些男同性恋穿着女装,以此挑衅法国共产党和与其紧密联系的工会——总劳工联盟(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 (CGT))里顽固古板的领导人们。他们在巴黎美术学院(School of Fine Arts in Paris)举行会议,其中一些会议变成了同性恋联谊会,有时还不只是“联谊”这么简单。在有一次的集会上,据说作家Daniel Guérin和Françoise d’Eaubonne脱光了衣服。这些会议和政治活动一样,都属于群体治疗时间,是男女同性恋能够聚集在一起,分享内心深处的焦虑,梦想一个更美好世界的难得时刻。
1968年5月是政治行动事实上的参考点。它既被视为人们反击的时刻,也被视为对性取向认同自我反省的触发器——正如俗话所说的,这标志着“长期斗争”的开始。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石墙运动”也起到了类似的功能:它迅速壮大了一群骄傲的同性恋活动者,他们吸引公众注意,呼吁采取进一步的直接行动。就像他们的法国同伴那样,这些人既是平权运动者同时也是革命者,他们为自己的组织取的名字——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就证实着这一点。
虽然由于各种原因,FHAR和Red Dykes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失败了。但是,作为一个狂热的、对权力不感兴趣的群体,这些组织留下了令人惊讶的遗产。日益崛起的社会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支持同性恋权益事业。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当选后,社会党议员们将法国的恐同法律彻底废除。

纽约骄傲大游行 图片来源:Hunter Abrams
如果说,今天的LGBT活动家在西方的诉求更为温和,那么这一部分是社会进步的明证。婚姻平权的成功和对各种形式歧视的约束标志着无可争议的胜利,这也是上层政治阶层的艰难让步(虽然他们现在还在或多或少地歧视着同性恋和跨性别群体)。但是,如今主流平权团体的话语——无论是美国的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还是法国的LGBTI+联盟(Fédération LGBTI+)——都经常显露出一种被压制了的政治想象,这种想象被如今他们的防御性的姿态阻碍得停滞不前。
对这些六八弄潮儿政治诉求的怀旧可能毫无意义。但是,我们不能不倾佩他们当时深邃的雄心和壮志,他们勇敢地提出要消灭我们大多数人在今天仍然对其合法性坚信不疑的一整套制度:核心家庭、军队和婚姻本身。如今的人们确实会时不时地批评一下这些制度,但是却有很少人能去坚信它们的存在阻碍了自由平等社会的发展。不幸的是,可能还得需要另一场与68类似的运动,才能让足够多的人敢于再次相信这一点。
原文链接:
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may-1968-lgbt-rights-france

本文首发于土逗公社
转载请联系土逗获得内容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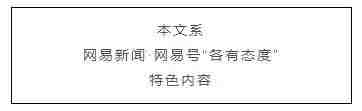
喜欢这篇?
扫码赞赏


漫画:发条

阅读原文,赞赏“土逗”~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