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痛苦,只有感恩

从今年9月起,头疼,因为从暑假就得了中耳炎,还在等待中耳炎的鼓膜修复手术,所以一直以为头疼跟中耳炎有关。在上海耀中工作时晚上经常备课到10点,头疼,以为是耳朵发出警告;9月和10月分别给对外汉语人俱乐部的老师做了两场分享会,身体不舒服,出于对同道的尊重,站着坚持了下来,讲座下来觉得体力不支,也以为是中耳炎在作怪,当时还笑着跟俱乐部的负责人孔婷说我是“带病”参加。直到10月底的一天,我去北京一家汉语教学机构谈合作,去的路上就感觉恍惚,聊的过程中居然连拿笔的手都哆嗦,看电脑屏幕一片模糊才觉得不对劲儿。
去北大医院(给我看中耳炎的大夫也是我的朋友就在那里工作),在他的建议下,挂神经内科号,看病,在医生的建议下拍脑部的CT,复查,一周之后,10月29号,星期三,北大医院神经内科的黄教授和隔壁神经外科的鲍教授简单一会诊,告诉我:“你脑部长了个东西,而且已经很大了,具体什么不清楚,吃药打针不管用,马上住院手术”。10月30号,在爱人艳萍的陪伴下,我住进了北大医院神经外科的病房,病床号是33号,而我,33岁。
我还算坚强,但并不是那么乐观的人。平白无故脑部里长了个东西,且这些年没有半点感觉,任谁也紧张。我不怕死,可我怕自己走了,母亲在这世界上再没有一位至亲,怕自己走了,皮皮失去父亲,艳萍失去丈夫。也不甘心,自己还有那么多心愿未了,还有两个梦想要实现,更舍不多那么多好朋友。
给自己的家人和一些朋友发了微信:“我脑部长了个东西初步判断是良性的也不排除是恶性的已经住院下周手术希望能挺过这一关。”家人和朋友的鼓励和祝福也纷至沓来,家人中,最给我鼓舞的是小姑,电话中才得知,五十岁不到的小姑已经先后做过两次良性肿瘤手术,且怕我担心都没有让我知道,给我打电话那会儿,她也躺在病床上,正要接受阑尾炎的手术;朋友中,难忘北语苏老师简短且有力的话:“人生坎坷只能选择坚强,你一定能迈过这一关,我相信你!”从大夫那传来的也是乐观的消息:根据我的临床表现和大夫的经验,肿瘤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良性。
安抚好母亲,有艳萍相伴,我逐渐把心态调整好,耐心地等待手术。在这期间,我一直很喜欢吃医院给病号做的病号饭,以至于艳萍笑着说:“你真是吃什么都好吃!”。
从住院到手术有一周的时间,记得有一天,艳萍偷偷给我买了点猪头肉带进病房,我正津津有味地吃着,走进一高大的大夫,满脸英气,看我正大口吃饭,笑着说:“这一看就是山东大汉,猪头肉可不是我们的病号饭哈。”他问了我是做什么的,艳萍替我回答是“教外国人学汉语的”,我则很骄傲地告诉他艳萍是北大毕业的。这位医生查看了一下隔床的病人,临出门的时候,望着我(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他的眼神),一字一句地说道:“手术完了,你还可以做老师!”

后来我知道,这位医生是张家涌大夫,北大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我的主刀大夫之一。
比原定的日期晚了两三天,手术定在了11月5号,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我竟然没有丝毫紧张,除却之前说的原因,还因为平时交流时,隔床的做完手术的病友已经把医院手术室的“壮景”跟我描述了一遍:一个个手术室一溜儿排开,像大会议室要开会;一排排医生和护士站立,感觉要上战场的战士。躺在手术车上,我只觉得新鲜,上了手术台,麻药一打,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给我主刀的两位医生,一位是北大医院的老院长,中国神经外科领域的权威鲍圣德大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这个领域全中国最好的大夫之一;另一位医生,就是前面提到的张家涌大夫,按照我堂妹夫(他也是医生)的说法,他是颅内手术“高手中的高手”。至于自己为何如此幸运,能让两位大夫尤其是已经“封刀”的鲍大夫亲自为自己做手术,那就是另外一段故事和自己的福报了。
手术本来预计四个小时,结果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手术整整持续了八个小时。手术后不久,我就苏醒过来了,这让家人一块石头落地的同时,更让所有给我手术的医护人员欣慰。后来听艳萍说,在我还在苏醒室的时候,就有一位医生走出手术室,兴奋地告诉等在外面的我的家人:“手术非常成功,比预想地还要成功!毕竟是年轻人,体质真好,手术做完就苏醒过来了,就是出血过多,好好休息!”
我被推回病房的时候,按照医院的规定,只留下艳萍留下陪我。就在这时,走进了张家涌大夫,他让我握了一下拳,确保最担心的手术影响四肢的情况没有出现,然后又是一字一句地说道:“手术做得非常成功,睡觉吧!”,转身离开,只留下一个高大的背影。
第二天,张大夫告诉艳萍,其实手术过程非常惊险,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手术,所以他们非常欣慰。
手术有多惊险,我也不知道。直到后来出院后,我去北大医院复查了两次,鲍大夫聊起当时我的病情,先后轻描淡写地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你的肿瘤虽然是良性的,但是太大了,手术时根本就不敢直接开颅,慢慢,先吸出肿瘤一些水,再一点点儿地开颅、清除,开颅之后,你的血压居然直接降到5!当时真是很危险。”第二句话是:“你再晚来一个星期,就没命了。”
在我住院期间,至少在我记忆中,张家涌大夫曾先后四次亲自操刀给我做了一些诸如放血之类的小手术,以至于我的责任护士有些好奇地问我:“你跟张主任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其实,她哪里知道,在生病住院前,我根本就不认识张大夫。
至于鲍大夫,仅举一例,第二次去复查的时候,艳萍不小心“暂时”丢了我的医保卡,鲍大夫知道后,无论如何不愿意给我们开自费的检查单和药单,说“这是不少的钱呢!”
其实,只有一千多块钱,相比手术费用,根本算不得什么。
但我知道,这叫“医者仁心”。

左一为黄大夫,右一为鲍大夫(2014年12月31日)
我想起手术前我跟鲍大夫一段简短的对话:
我:“鲍大夫,手术复杂吗?”鲍大夫:“谈不上复杂,中等手术。这就好比我们的工作,你们工作是上讲台,我们工作是上手术台。麻药一打,你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剩下的就交给我们了。”
对大夫来说,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工作而已,可是,一条条宝贵的生命却被挽救,一个个鲜活的希望被重新燃起。
这让我想起七年前,我刚刚成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清华大学的一位前辈曾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对你们来说,这只是一份兼职的工作而已。可是你们知道吗?一个留学生从此爱上或者讨厌上中国,可能就是因为你。”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住院的时候,我随身带了三本自己的《麻辣汉语》,想着一本给自己看,另外两本送给主治医生和主任护士。后来发现三本根本就不够用,索性先送给鲍教授、张主任和护士长三人。看到我从床头下拿出书的一刻,鲍大夫一愣,我也看到张扬大夫带惊喜和感动的目光,鲍大夫“一声令下”,这本书就在护士站里传阅开了。因为是漫画形式的作品,所以给工作疲惫的护士们尤其是值班的护士们带来了不少欢乐。大概出院前四五天,我练习行走经过护士站,看到我的责任护士张琪护士正疲惫地一手托着头,看着这本书。我忍不住让三姨回病房,帮我取来手机,拍下一张模糊但珍贵的照片。
同样是有一次经过护士站,一位我很熟悉,和蔼可亲的经常给我换药的护士(后来知道这位护士姓姜)主动跟我说:“我们看了你的书,真的很有意思。看你的各项恢复指标比如血小板儿、体温等都回复得不错。快点好起来,你的家人、你的学生都在等你!”。
如沐春风!
手术的前一天,远在青岛的姐姐、哥哥、妹妹和妹夫来到了北京,并在医院附近的宾馆住下,四个人都是请了年假过来陪我的。
就在去年,德高望重的爷爷安详地去世,留下了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知道我患病的消息,大爷、姑姑等很着急,但是因为年龄的关系,不便过来,就这样,以姐姐为代表的我们家的第三代来到了我的身边。而在我们刘家,姐姐是公认的不让须眉的第三代中的佼佼者。
尤其让我意外和感动的是大姑家的妹妹和妹夫也一同前来,妹夫也是医生,在青岛工作,正是这个原因,他执意前来陪我。按照姐姐的说法:“人多了好。”
还记得手术那天哥哥帮大夫把我推进手术室时我能感受到的坚定而稳定的步伐,还记得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有一双大手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与此同时,我听到的是:“老公加油!”。
我手术后的第二天,要做一个例行的术后脑部的CT检查,那时我已经完全清醒了,记得是被五个人(还有艳萍)一起推进的CT室。因为身体极度虚弱,我没法从病床自己转到仪器上。
于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出现了:哥哥姐姐等四人,一人抬住床单的一个角,硬硬地把我裹到床单中间,抬到了仪器上。
姐姐等四人陪了我五天,而这五天,也正是我手术后最难熬的五天。因为手术完的当晚受了一点惊吓,加上手术失血过多、连续两天没有休息好,从术后第二天开始,睁眼闭眼,我的眼前全是一片幻觉的图像,让我在亦真亦假、似生似死间煎熬,睡觉睡不好,于是第二天一睁眼又是一片幻觉,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我的幻觉图像可谓“丰富多彩”,从浮雕到医护人员的影像,从各种卡通人物到电脑符号,简直可以说小说了,呵呵。)幸亏有姐姐在,她跟艳萍一样,有一种可以让人瞬间平静的气场。姐姐的开导和鼓励,哥哥罕见的耐心,妹妹和妹夫的开朗,伴随着我度过了最难熬的手术后的初期。
有一天晚上到了吃饭的点,妹妹和妹夫在陪我,饿了,饭还没有来,他们告诉我姐姐和哥哥去给我买饭了。等了许久,就在我要不耐烦甚至要发火的时候,姐姐和哥哥回来了,带回来一份热气腾腾的西红柿鸡蛋面,那是他们从一家饭馆中带来的。为什么那么久呢?因为姐姐告诉他们要少油少盐,师傅要专门做。
有一天姐姐自己在陪我,张家涌大夫问她:“你是志刚的什么人啊?”,没等姐姐回答,我就自豪地告诉他这是我老家的堂姐,张大夫跟姐姐聊了两句,转身走开了,姐姐也正好出去接电话,剩下旁边一位病床陪护的护工惊讶地跟我说:“你一口一个‘姐姐’,我还一直以为是你的亲姐姐!”。

姐姐他们是请年假过来的,我前后住院13天,姐姐他们在医院里陪了我整整五天。艳萍利用APEC放假的时间又陪了我两天,然而出院的日子还遥遥无期,我甚至还不能下床,就在这个时候,二姨和三姨一个从济南,一个从泰安,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医院。
母亲这边兄弟姐妹五人,大舅年事已高且身体不好,在农村休息,小舅英年早逝。剩下的就是母亲和二姨、三姨姐妹三人了。姐妹三人感情很好,但又性格迥异。母亲人缘最好,也能操心;三姨和其他家人来往不多,唯独和母亲、和我感情最深,也最疼我,我出生时,正是奶奶和三姨把我从农村的卫生院抱回老家的;二姨呢,天生乐观,有见识有气场,是“大城市”的人,但是二姨有点和家人“老死不相往来”的意思。济南和泰安那么近,这么些年,记忆中就是我结婚时以及两个表哥结婚时她“亲自”来过泰安,按照母亲的幽默说法:“没什么事情能惊动你二姨”,但是这次,二姨被惊动了。这让我想起自己在济南山师大读专升本的那两年,哪天我吃腻了学校的饭,就给二姨打个电话:“二姨,我去你那儿吃饭了。”,然后就在同宿舍舍友的一片羡慕嫉妒恨中“飘然而去”。正是那两年,二姨见证了我从一个专科生到研究生的蜕变。
艳萍把二姨三姨接到医院的时候,我头上还裹着一个“像柚子的包装袋一样的网兜”(艳萍的比喻),脸胖胖的,且按照张大夫的说法,会“越来越肿”。三姨一见我就抱着我的头哭了,二姨是一滴眼泪没掉且笑嘻嘻地说:“这不状态挺好嘛!”。
剩下的日子都是二姨和三姨陪我度过的,从脑袋上的“网兜”被摘下,到自己大小便功能回复正常,到能下床活动,到最终出院,二姨和三姨在悉心照顾着我,也给我诠释了“亲人”二字的含义。
北大医院住院规定很严格,病人作息时间都很有规律,且规定晚上只能有一人陪床。本来应该是二人轮流留下陪我,但是二姨有点高血压,最怕觉睡不好,在三姨的坚持下,她每天晚上回附近的宾馆休息,留下三姨睡在陪床椅上晚上照顾我。每天早上,二姨在开门的时间早早到来,帮我洗漱、滴耳药(住院那会儿我中耳炎还没好,需要每天滴耳药,万幸是右耳,跟动手术的右脑在一侧,没有影响),三姨则抓紧时间去楼下医院的职工餐厅把三个人的早饭一起打来。在医院病床的小桌上跟二姨三姨一起吃饭的情景,历历在目,三姨还不时跟我开个玩笑什么的,比如把我最爱吃的花生藏起来。
我晚上睡觉最喜欢安静,怕光怕声音。偏偏住院时晚上总睡不好觉,病房里三个病人,一会儿护士查房,一会儿他起来喝水,一会儿我又渴了,尤其是半夜,经常把已经熟睡的三姨从梦中叫醒,让我内疚至今。记得有一个晚上,我惊讶地“发现”三姨睡觉居然打呼噜——我最受不了的呼噜,然而慢慢我发现,当内心平静下来,伴随着三姨的鼾声,也能入睡,且很亲切。
二姨和三姨在医院悉心照顾着我,两位母亲在家里照顾皮皮(岳母在得知我生病后就从东北赶到了北京,留下岳父一人在家),艳萍下班后回到家哄皮皮睡觉,让两位母亲得以休息一下,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而我的身体,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恢复。手术后的第八天,我就可以在二姨和隔床病友的搀扶下下床走几步了,走到床前,我举目远望,看到的是北海公园“美丽的白塔”,《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旋律瞬间回荡在耳边。
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不是来医院陪我,二姨本来也要去医院取出胳膊里的一块儿钢板,她最近受了一次外伤,但她跟我说:“不着急,随时可以取”;三姨在家里的孙女天天打电话,哭,想她,但是三姨跟我说:“彤彤有她姥姥带着,你什么时候出院,我什么时候回去。”
三姨还告诉我,在农村的大舅母,每天为我上一炷香,“什么都不管”的大表哥,每天一个电话询问三姨我的病情。父亲、母亲、艳萍三家的亲人给的钱,更是一笔笔地汇到了艳萍或者我的帐号里。
至于二位母亲和艳萍,那已经不是用文字可以表达的了。这世界上没有伟人,却又伟大的母亲;没有完人,却有完美的爱人。
小时候听毛阿敏的《朋友》:“千金难买是朋友”,是啊,有朋友真好!
从住院到手术有六天的时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如此严重,加上医生给我传递的都是乐观的信息(还记得我的主治大夫张扬医生有一次“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下我的CT片,笑呵呵地对我说:“小问题,等着做手术吧!”),所以我把病情告知了一些朋友。瞬间就有北京的朋友要来看我。
可我性格的原因,一是那会儿自己已经剃了光头,自恋的我不愿意让人家看到自己这个“熊样”,且不愿意让大家牺牲周末的时间来看我,二是,那会儿我还不了解医院的看望病人的规定,以至于有几个好友(比如泰宇)都已经到了医院门口了,又被挡了回去。对不起!唯一“成功”的是海峰,在知道我住院的第一时间就赶到了医院,来了个“突然袭击”,和我简单聊了一下,给我留下一个红包后离开。
手术前我知道自己一段时间内肯定是不能摸手机了,所以把艳萍的手机号发给了几个不停地给我发短信打电话最关心我病情的朋友,告诉他们手术后可以跟艳萍联系,之后就是上文说过的“九死一生”的手术了。
手术后为了让我安心养病,再加上那会儿我确实也很虚弱,艳萍替我婉拒了一些好友,然而还是挡不住朋友的关心;我手术后的大概第四天,远在泰安的黄刚从山东坐动车来到我的床前,还带了铺盖,打算要陪床,那会儿姐姐他们还在,他来时我正睡午觉,他和姐姐悄悄地聊了会儿,跟哥哥吃了顿午饭,等我醒来之后才跟我说话聊天;我出院前的一个周日,高中时代的同学好友卓宇也来到我的病床前,当年我们班数一数二的学习委员见到了我这个班长,短短二十分时间不到,却格外亲切,那会儿我已经能下床,忍不住下床跟他坐在椅子上聊天,艳萍就在一旁听着笑着。也就是那次聊天,我发现艳萍经常夸我的“过人的记忆力(毫不夸张)”一点儿也没受影响,甚至还记得送给卓宇的《麻辣汉语》上的赠言和卓宇给我的短信的回复。卓宇笑着说:“你这是什么脑子啊!” 还记得卓宇一见面伸出俩指头问我:“这是几?”,我回答是“二”。现在想想,当时我该说“这不是你嘛!”。
我出院后的第五天,11月23号,星期天,“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孔明从济南来到了家里看我,和他一同前来的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他的妻子也是我们大学同学),还有另一位我的大学好友倩。那天下着小雨,知道他们要来,我前一天晚上激动得睡得很好(哈哈),养足了精神等他们。
妈妈做了满满一桌饭菜,还有三姨这次从泰安带的地道的山东煎饼,我举起手中的粥,大家“以粥代酒”,喝了三杯酒,第一杯,敬我的两位母亲,辛劳而伟大;第二杯,为我们十年的友谊干杯(我2004年在山东师大读专升本的本科,今年是我们相识十周年);第三杯,祝愿我们的父母家人一生安康。
临走,倩不顾母亲的执意反对,像吵架一般给我留下一个厚厚的红包,而我知道,她在济南做老师,收入并不高,宝贝女儿也不到五岁,正是用钱的时候。
他们走后,我才想起,只顾着高兴,忘了拍照留念。孔明说“来日方长”,倩和我都觉得遗憾。而我知道,有些时刻,会沉淀在心里一辈子。

从左至右依次为:孔明,娟子,倩。(2016年8月于济南)
在宁波的徐老师,在上海的郁老师,在海南的洪老师,在新加坡一所国际学校工作的鲍老师,在欧洲定居的研究生时期的好友友情,在美国罗德岛大学孔子学院工作的刚与我认识半年的张老师,同样在美国的黄老师,在土耳其工作的高中同学志国,还有远在南美的师弟雅琳…..微信、微博私信、电话,问候纷至沓来。
患难见真情,让我倍感感动的还有仅有一面之缘的在西北的同道苏老师。我们之前都是在网上交流,只有一次她在北语开会的时候匆匆见过一面,但彼此很投缘。短信里得知我住院的消息,她坚持要给我汇款,我的手机里至今还保存着她发给我的短信:“朋友有通财之义,一进医院花钱如流水,你给我个银行账号,让朋友尽个心意”。钱我没有要,但是这份情意,会永留心间。
而上天也很会安排,就在我快出院的时候,苏老师也生病住院,我们从同道变成了“病友”,在我文字写到这的时候(今天是12月15号),苏老师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在慢慢地恢复中。
如果说这些还是已经熟识或者见过面的朋友,更多的祝福来自网上素未谋面的朋友,尤其是在我出院后得知我并不是因为中耳炎住院的朋友。有些“朋友”,你跟ta见过很多面,却从未走进彼此心里;有些人,素未谋面,可你知道,ta 就是你的朋友。这些真挚的祝福,都默默地记在心底,无以为报,唯有做更好的自己。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这次生病住院,机缘巧合,还认识了一位同样做对外汉语的朋友,只见过几次面,聊过几句话,但我知道,我们可以成为彼此信赖的朋友。
十二年前,也是我读研之前,我在山东做了四年中学英语教师。卢特,是当时我教的学生之一,选择卢特做学生代表,记录下学生带给我的感动和幸福。
为什么选卢特呢?因为他确实很“特别”。从我住院到今,两个月不到,我跟卢特见了整整四次面,每一次见面都有不同的感受。
第一次见面,是我出院前的一个周日,卢特和其他三个学生来医院看望我。跟他们一聊,我才知道,学医的卢特已经读研,正在医院实习,而他实习的医院,是北京天坛医院,那是北京乃至全国的神经外科的顶尖医院。卢特的专业方向,正是神经外科。这次见卢特,除了惊喜之外,我有些惭愧,因为这些年一直忙着追梦,忘了去关心这些宝贵的学生,我知道卢特是学医的,却一直忘了去关心他到底学的什么专业,有什么打算。
第二次见卢特,是我出院后的第五天,周六。因为手术时左额架了一个支架,所以留下一块儿外伤。我把外伤拍了张照片发给卢特,卢特让艳萍陪我去他实习的医院,给我处理了外伤,拿了消炎药。当天我发了一条微博和微信:“昔日的学生已经成长为医生,在天坛医院实习,今天给我处理了一下手术后的外伤,作为老师是多么的自豪!”。那次见面,也让艳萍感慨颇多:知道老公有很多学生,没想到已经如此成长!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我们俩以卢特为中心和主线,谈了一路昔日的学生。
第三次见面,是出院后的第一次复查,那时我的身体恢复得不错,但是左眼不知什么原因看不清楚,艳萍在陪我去北大医院复查之后又来到卢特所在的天坛医院。卢特把CT片子给他的导师看了一下,告诉我“给眼睛点时间”。也就是在那次见面时,聊起当时得知我住院的情形,卢特告诉我当时他听到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很担心,因为在天坛医院,一般住院的病人都是病情很严重的了,说这些话时,我分明看到他的眼圈是红的。就在那一刻,我读出了他流淌在心底的善良。卢特在他的办公室里把我脑部CT片拿出来,用手机拍了下来,笑着对艳萍说:“这就是我以后的案例了,别人的片子我记不住,刘Sir的片子,一辈子也忘不了!”。

十二年前,我还在卢特这个年纪,正把青春和激情飞扬,那时我会想到,十二年后,我会经历一场疾病,而我的一位已经成长为医生的学生,就在我的身边,给我治疗,安慰我、鼓励我、感动我、骄傲我吗?
第四次见面,是上个周日,卢特约了王一、君祥三人,一起来家里看望我。还记得去年四月,一个春光灿烂的日子,卢特四人来家里看皮皮,亚文把“柔弱无骨”的皮皮抱到怀里,吓得不敢动弹。转眼一年过去,皮皮已经可以用叉子给三人喂苹果吃了。卢特看了我复查的脑部CT,兴奋地告诉我:“真的恢复得太好了!”;聊起当时我的病情,尤其是手术开颅后血压降到五的时候,我看到卢特的眼圈又红了:“老师,血压降到五,就相当于你身体里没血了!”。然后他又笑着说:“老师,你跟死神交了一次手,重要的是,你赢了”。
想起30岁生日那天,我在人人网的日志中写到:“拥有学生的喜爱,是自己无可代替的财富的积累,莫可名状的骄傲的底线。”
2010年,我在上海大学城见到了昔日的学生方筱、李烨、李沐、尹哲等人,短短六年过去,看他们从一群还略显稚嫩的中学生成长为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我写下一首小诗《你们都在成长》:
“你们都在成长,伴随着青春和梦想;少了年少的几分青涩,散发着自信的光芒。你们都在成长,思想的火花已擦亮;骄傲着自己的校园,追逐着自己的梦想。你们都在成长,善良也是一种力量;走在你们身边,幸福在心里荡漾。你们都在成长,昔日的学生今日的榜样;不管未来怎样,我为你喝彩期望!”
手术完的当晚,我居然兴奋得睡不着觉,我问艳萍:“老婆,你觉得这次手术过后,我会有什么变化?”,艳萍想了想,跟我说:“老公,我觉得你从此会变得很豁达。”
我不知道自己今后会有什么变化,这场疾病是一笔太宝贵的财富。十年之前,父亲因意外去世,让我对人生、对生活有了第一次感悟;十年之后,伴随着这十年的经历,当自己与死神擦肩而过,这场疾病又会带给自己怎样的思考和变化?

我不知道自己会有多“大”的变化,但是自己却感受到了一些小小的变化。比如我养成了手写日记的习惯,哪怕很短,因为当自己老去,想看着自己每天是怎样认真地度过;比如每天早上看母亲在厨房做饭,我不会再看一眼就走开,而是凝视瞬间,心里充满温暖;比如我努力地告诉自己,“永远不要生气”,要平和,要大气,像艳萍一般;比如在坐三轮时我不会再去计较那几块钱,因为知道师傅们是怎样的不容易;比如我把值得珍惜的朋友一个个写下,心里想着,有他们,自己就不孤单;比如我开始觉得自己以前的狭隘和骄傲是多么可笑,虽然骄傲中带着梦想的风帆;比如我不再觉得有谁曾对不起自己,反思的是自己。
最重要的是,无论今后自己做什么,选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首先选择成为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尤其是“好父亲”,因为在我出院后踏进家门的一瞬间,我只想把皮皮抱在怀里,告诉他:“爸爸今后哪儿也不去了,只想陪在你身边,看你成长!”
北语的一位我老师也是我的恩人电话里跟我说:“知道你住院后,我们几位老师就想去看你,可是又担心你心情不好,所以一直没去。”我告诉她:“怎么会心情不好?丝毫没有疾病的痛苦,我心里满满的全是感恩!”
感谢命运的安排,在那个周三的上午,鲍教授每周唯一出诊的日子,我来到了北大医院;感谢北语的这位老师,如果不是我们的缘分与情谊,我不会有幸得到最好的治疗;感谢微博上素未谋面的张老师,您的与癌症抗争的经历为我诠释了“坚强”;感谢我挚爱的亲人和朋友,为我诠释了爱与情意的真谛;感谢我的正在成长的学生,感动我、骄傲我。
出院后的第二周,我去北大医院做复查,自己一人空腹坐地铁,来到医院,抽血、拍片、做核磁,觉得自己很坚强。在诊室的门口,遇见一位老人,以下是我们的对话:
我:大爷,您身体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大爷:小伙子,我没事,我是来给我老伴儿拿药的,她有老年痴呆症,以前都是保姆过来拿药,这几次保姆得照顾她,我自己打车过来了的。我:大爷,看您精神真好,您高寿了?大爷:我89了。我:………大爷,您的身体真棒!您也真棒!大爷:我13岁就参军了,呵呵。
原来,岁月留给我们的,不只是沧桑。
我想要幸福,上天对我说:“赐你一场疾病,病中你会领悟到什么是对你最重要的,你会更加懂得感恩、珍惜,懂得感恩,知道珍惜,你就得到了幸福的真谛。”
我想要成功,上天对我说:“最大的成功是‘人’的成功,一个人死后或有危难时,有多少人会发自内心地去怀念或者关心他帮助他,这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回顾你患病的经历,你还想怎样成功?”
我想要成长,上天对我说:“经历本身不是财富,对经历的反思才是。赐你一场疾病,你会由此反思自己的过去,反思自己身上的不足,希望你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而热情,更多一份宽容和谦逊,这是最好的成长。”
上天问我:你还想要什么?
我回答:“我什么都不要了,原来生命的真谛从来都不是‘我想要什么’,而是‘我拥有什么’,心怀善念和梦想,知足常乐,爱自己、爱家人、爱生活、爱朋友,就是这么简单!”
“要懂爱,好好爱,深深爱”。
2014年12月18日
完成于北京家中,自己手术出院一个月之际
原文于2014年12月发表于新浪微博“北语刘志刚”
2016年11月感恩节 美国 蒙哥马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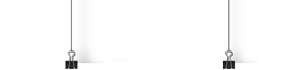
“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帮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黑暗中默默陪伴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坐车看望你的人、陪你哭过的人、总是以你为重的人、带着你四处游荡的人、说想念你的人……是这些人组成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是这些温暖使你远离阴霾,使你成为善良的人”_村上春树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