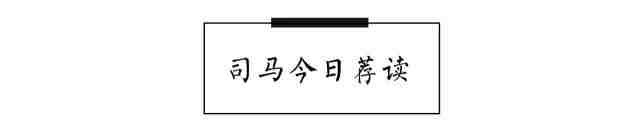童年被性侵,母亲是同性恋者,她却用一部纪录片,向所有过去温柔地说“谢谢”


这是司马推送的第 745 个与众不同的人
母亲是同性恋者,社会最底层,辍学生,性侵受害者,黄惠侦身上有很多标签,有人看了片子,说“这片子太猛了”。的确,这些元素杂糅在一起,随随便便,就能挑动媒体的神经。
黄惠侦却不想煽情,回避励志,好像用最生猛的食材,清蒸白灼,上了一碟最寻常的家常小菜。
那碟清清淡淡的小菜,不同于任何家国天下历史浩荡的纪录片,那是一部私人纪录,扣问的,是“妈妈,你爱我吗?”三问三答,却如同向天而歌。“这世上没有任何一种关系,是理所应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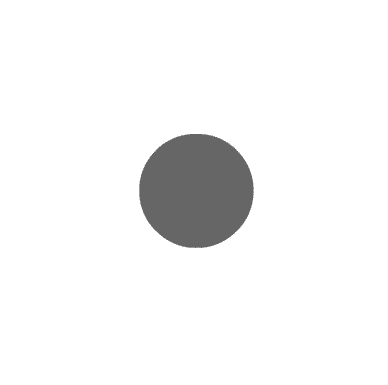
台湾放映结束后,黄惠侦在角落孤零零等着例行的导演问答,迎着观影结束时涌出的人群,迎着光亮,背影单薄,有观众,忍不住抱了抱她。
柏林放映结束后,一个日本男人跑去跟黄惠侦说,“抱歉在你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事,但是请你知道,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父亲那样的。”一连说了好几遍。
侯孝贤曾经连样片都没看,就告诉黄惠侦,“你只管专心创作,其他的我来。”

《日常对话》导演黄惠侦(右)与女儿一起出席电影试映会
于是,16个T的硬盘容量,150个小时的影像素材,从1988年拍摄到2016年,剪成了88分钟的纪录片。
于是,这部片子提名台湾金马奖,问鼎柏林国际电影节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评语是“充满力量,具有普世价值的勇气之作”,但是,你可能永远都无法在国内的影院看到它。尽管明天5月17日,就是国际不再恐同日。
它太私人了。“我的母亲是个同性恋者,我应该怎么面对?”“我的父亲性侵我,我应该怎么面对?”“我的母亲,到底爱不爱我?”

母亲“阿女”与黄惠侦的女儿在一起
然而这样一部触动了很多人的片子,
黄惠侦的母亲,阿女,
在片子仍是雏形的时候,并不认同。
“有谁要来看我的故事?”

——阿女——
从小到大,黄惠侦的母亲阿女,
生活在那样一个地方,
她习惯了和朝夕相对的亲人,做陌生人,
她也习惯了,不在乎自己。

从不往来的亲戚们
“你们知道她喜欢女生吗”,这个问题抛出来,
阿女在老家的亲戚们都是支支吾吾,
打岔得让人好笑。
“我不知道,知道这个也没用。”

视线不自在地转移,
“衣服要赶快洗一洗。”

没有一个人愿意直面镜头,谈起他们身边的同性恋者阿女,拍摄这一段时,距离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地区,仅有两三年之隔。
然而在台中嘉南平原上的云林北港,事情变化的速度很慢,留在这里的人们脑袋里的条条框框,几乎和50年前没有什么分别。
1956年,黄惠侦的母亲阿女,出生在北港。原名月女,阴柔温婉,她早年的模样,还有几分衬这个名字。

年轻时长发秀眉的阿女
阿女成长中,所获得的所有温情,都是来自家族中的其他女性。
住在邻村的外婆,每次阿女过去,口袋里都会多出几个叮当响的铜板。灶台上还会特意生火,给阿女煮一顿雪白的白面线。
阿女的妈妈会偷偷给阿女零花钱,不让她下田做粗活。她钓青蛙,打芒果,捉蟋蟀,惹得父亲暴怒,也是妈妈护着她,让她不被父亲打。
妈妈离世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阿女。

然而在这个家的大部分时刻,
阿女都是无足轻重的。
生前,父亲的零花钱只给这个家庭的三个男孩;
死后的墓碑上,他的名字旁边,
也不会镌刻女儿的名字。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罗大佑唱的就是1970年代的北港。这个以农业为主的保守小镇,像如今千千万万的城镇一样,人口长期负增长,镇上少有年轻的面孔。
阿女的二姐先行北上,独立赚钱,在她的坚持下,阿女有了机会读书,成为了全家唯一一个读完小学的女生。
也就到此为止了,继续读下去,不过徒增经济压力,还多了一分嫁不出去的风险。
1970年,阿女14岁,也来到了台北,成为中正路上纺织厂生产线上的一名女工。自己生产出的好看衣服,和她们没有太多关系;闪着霓虹招牌的电影院、大剧场,她们也没钱买到通行券。工厂附近庙口的野台歌仔戏,是阿女唯一的娱乐活动。

白上衣,扎进白长裤里,阿女总是精精神神地去看戏。一次落雨,台上扮相好看的演员,下来拿了把伞给她,后来她成了阿女的第一个女朋友。
演员身后不缺献殷勤的粉丝,一来二去,二人常常吵架。吵得最凶的一次,阿女把对方送的金戒指、礼物、衣服,一样样在床上排列整齐。一赌气,从台北回了北港。
这个决定,改变了阿女的一生。
像如今热衷“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一样,逃离后,在老家的生活常常陷入惯性,这惯性包括作息,饮食,也包括婚嫁。

21岁的未婚女孩,是70年代农村最该被担心的物种。”
相亲会上,妈妈,姑姑,兄弟,都对阿女面前这个大她5岁的客家人阿源满意。阿源矮胖,眼神凶得很,阿女并不喜欢,但最疼她的妈妈也没能护得住她。
这事就这么定了。
两人一同离开家乡,去了台北,住了一间落脚都局促的房子。

纪录片中,黄惠侦重回童年的这间小屋。
阿源是油漆工人,每天领到的日结工资,他通通奉献给了酒精、烟草、牌桌。使不完的精力,发泄在阿女身上:一面是当时不为人知的“婚内强奸”,一面是用拳头教会阿女听话。
从精神到肉体,阿源全面支配着阿女的身体。
阿侦和妹妹,在这场噩梦般的婚姻里来到人世。“如果可以,我不想结婚,也不想你们出生,来受苦。”

带孩子的阿女
多了两张吃饭的嘴,阿源并没有想要勤勉起来,家中的债务日渐沉重。为了让活人活下去,阿女决定亲近死人。
原先看歌仔戏时,台下有人招工,是做牵亡,顾名思义,牵引亡魂,是台湾特有的丧葬过程中的仪式,以超度死者。
阿女也报了个名,去了才知道,这份工作,要下腰、劈腿、翻跟头。因为工时短,可日结,拿到手的钱也比在工厂多,最能救急,阿女留了下来。

家中无人照看,月嫂太贵,阿侦自小就跟着母亲,见了一场场葬礼。
可能是耳闻目染,可能是阿女引导,已经没人记得事情是怎么发生的,6岁时,阿侦成了最年轻的牵亡歌阵演出成员。
当时阿女在的阵团满员了,很长一段时间,她们要各自去台北桥和万华做工。为免波折,阿女用几万块,买了音箱、麦克风、扩音机、三弦琴、法器,花钱挖来别的阵团的法师和琴师,印好写着“阿女牵亡歌团及各式阵头”的名片。
28岁的阿女独立开工了。

以为自力更生,日子会好过一些。然而奔波一天,卸了妆,脱下演出服,带着阿侦、阿侦妹妹回到简陋的屋,等着阿女的没有一个字的好言好语。往往是拳打脚踢一顿,一天辛苦所得,一分不留。
一个问题,开始在阿女心头反复斟酌。是一个人走,带一个女儿走,还是三个人一起走?
牵亡歌阵,说到底也只是底层的工作。阿女担心自己并没有能力养活三个人。少一个人呢,或许还能负担得住,但是留下来的那个,会遭到丈夫怎样的对待?
最终她下定决心,死,也要三个人死一起。

台北的一个夏日午后,倒映在小阿侦眼中,真的像周杰伦歌中唱得那样,“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
活了三十多岁,阿女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了全盘的决定。
她翻出之前东藏西藏的几千块存款,一张配偶栏印着阿源的身份证,楼下招来一辆出租车,带着两个孩子,终于离开了这个“家”。
——阿侦——
黄惠侦后来在自己的书里说,提到“家”这个词,她第一个想到的还是童年那个仓皇离开的地方。

她说自己好像从没离开过
那里的达新牌衣柜,她喜欢自己整个躲进去。合上门,一道天光从缝隙里漏进来,包围着她的是妈妈层层叠叠的衣物,她感觉自己像这些衣服一样,是被好好收藏并且被爱着的。
水泥和瓷砖砌成的水槽,母亲在里头洗净菜蔬,点燃瓦斯炉,架好锅,一锅白水里普通的菜蔬翻滚咕噜,渐渐生发出一些食物的香气。像小时候外婆给自己做白米线一样,母亲不善言辞,只会沉默地做完这一切。
阿侦把那个厨房称为自己童年的“临时天堂”。

天堂之外,是一场接着一场的葬礼。
阿侦和阿女接活的葬仪店中央,摆着两具棺木。葬仪店老板的女儿,常常被放进棺木里睡觉、玩耍,朱唇红腮的金童玉女,是这些小人儿的芭比娃娃。
牵亡仪式上,持香祭拜完毕的家属们,转头就为家产吵得不可开交。灵堂前香烟落下的香灰,被这些争红了的眼睛死死盯着,想要看看是不是隐藏了亡者的指示。
老师布置了日记作业,别人的日记中是公园、博物馆、游乐场,黄惠侦却只能想起,这一幕幕荒诞剧。

长大后,阿侦才知道牵亡是底层才做的工作
在小学读书的状态也没有持续很久,因为从家逃出时,户籍没有迁出,母女三人一直是幽灵人口。好不容易由阿女的朋友说情才入了学,阿女要跳阵亡补贴家用,连连缺席,引起校方注意。
终于有一天,阿侦收拾书包离开了学校,开始了全职的牵亡生涯。

“小学就辍学,是怎么执导纪录片的呢?”不止有一人,问过黄惠侦这个问题。
她说自己有四所学校。
第一所,是她的一本小字典:路边招牌,塞在信箱的广告单,糖果饼干的包装纸,不认识的字她自己要通通查一遍。
第二所,是邻近的漫画出租店。恐怖漫画,倪匡的科幻,推理小说,和《日常对话》气质迥异的这些读物,是她逃避现实的小小避难所。
第三所,是二手映像管显示器组装起来的有线电视。阿侦在上面看了好多好多电影,看到逼仄现实外的人生,还有那么多种可能。
1998年,一个午后,阿侦和妹妹照常准备化妆扮相,都是熟人面孔的阵头中心,混进一张生脸,别人介绍说这是电视台的记者,要来拍一拍牵亡。
这个人其实不是记者,而是台湾重要的纪录片导演之一,杨力州。

杨力州问了很多问题,好奇的阿侦问得更多。临走前,杨力州给了一张广告单给她,顺着单子上的地址,她第一次走出自己的生活圈,换了两趟公交,抵达了位于敦南诚品的放映会,那里,她第一次看到了不同于电视上的纪录片。
“原来电影不都拍得是事业有成,凯旋归国,达官显贵,俊男美女。平平凡凡甚至坑坑巴巴的人生也可以被叙述。”
又转了好几趟公交回到家,阿侦满脑子都是一个念头,原来还可以这样,用纪录片,为自己说话。
——对话——
阿侦有一种温柔的行动力。
拍纪录片的想法,她没有滞留于大脑。
她报名去了芦荻社大,创办社大的人是心理学出身,在那里阿侦学习了拍摄的基础技巧,又不仅限于此,她开始重新打量他人,街上擦身而过的行人,牵亡仪式上的人,母亲,自己。这是她的第四所学校。
她要拍一部关于自己家庭的纪录片,解开自己心中的疑问。


为什么亲人却好像陌生人?
存钱买了第一台摄影机SONY TRV-900后,
从98年开始,她常常在家中,开机,
将镜头对准母亲和其他亲人。
七岁的时候,阿侦发现了母亲爱的是女人。
现在轮到了妹妹七岁的女儿问她,阿嬷是男是女?

这个疑问在十几年后有了回响。
已经长大的两姐妹重新面对这个问题,
一个能理解阿嬷,却说不清对同性恋的想法。
另一个大方对镜头说,“每个人都有权利相爱。”

阿侦对同性恋的起初了解,就是糟糕的,当时来了一个六十岁的阿伯,聊天时转了话锋,“你妈妈是同性恋,是变态。”
阿侦在意的,却从来不是母亲的性取向,而是深埋心底却没有问出的:
为什么你喜欢女生,却会结婚?
为什么你离我们这么远?
为什么关于你自己,你从来不说一个字?

阿女好交际,知道怎么对人好。
除了歌仔戏演员的第一个女友,
她陆陆续续又交了十几个女朋友。
后来阿侦去回访他们,
他们都笑着来回忆母亲。

牌桌上的母亲,也总是说说笑笑,
阿侦不明白,为什么在外这样好的母亲,
在家横亘在他们之间,永远是沉默。
好像父亲的幽灵在那里,从来没有离开,
他们从来没有从中和的旧屋走出来。

在外和在家中,阿女判若两人
拍纪录片,不是为了拿奖,甚至也不是为了直面同志议题,原因极其单纯——接近陌生的母亲。
阿侦发现,镜头对准母亲时,自己总是切很大的特写,细腻到皮肤、白发、皱纹。起初,阿侦并没有想好怎么讲述母亲和自己的生命故事,这么复杂多端,又冗杂沉重。
直到自己有了孩子,她才开始渐渐理解母亲。因为女儿的一点点生病受伤自责,多少,也体会了一点当初母亲的心情。
她说,如果20年前,就仓促把这部片子拍出来,可能会更锋利,和今天是两种面貌。
也不会有影片后半段,母女二人坐在餐桌两端,一场让观众心颤的对话。

实际在拍摄时,这场对话拍摄用了三个多小时。摄影师离场,留下三台机器,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然后就是漫长的沉默。
对两个笨拙的人而言,这次对话尤其艰难。同一屋檐下的母女,竟然都不确定,对方爱不爱自己。

阿女也没有信心。

阿侦说,我如果不爱你,当初离家,怎么会回来。

阿侦小声啜泣,问出了隐藏几十年的秘密。当时一墙之隔,父亲让我摸他的生殖器,你怎么从来没有问过我?
那时候晚上和他一起睡,为什么我会半夜跑回来,你都不想知道吗?
她笃信母亲知道这场童年中的灾难。

阿女嘴笨,只能一再重复,
你说的,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当年是这样,
我会更恨他。

很长一段时间,
阿侦都觉得自己不干净,
也以为是因为这件事,
母亲不爱她。

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
黄惠侦却温柔地不可思议。
她告诉母亲,你没有做错什么,
好像也在告诉童年的自己,
和其他受到性侵的女性,
“这不是你的错。”

她希望自己的母亲,
在这个家,
是开心的,
不要再被父亲的幽灵缠着不放。

虽然已经四十岁,
我还是你的女儿。
你心里的事情,
可以对我说出来。

拍摄结束后,阿侦和工作人员一起整理素材。旁人看得更清楚,告诉黄惠侦,如果你母亲不爱你,怎么会陪你在那里沉默三个小时?
她只是和太多传统父母一样,不善言辞。尽管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她早已“出柜”。但是在和最亲近的人相处时,他们永远好像都在“柜中”。
直到黄惠侦用摄影机破开这扇柜门。

阿女和阿侦的女儿
影片结尾,黄惠侦的女儿,也学妈妈,
拿了一个玩具摄影机,去找阿女玩。
“阿嬷,你爱不爱我?”
好像在替阿侦发问。

第一次,妈妈说“你这么坏我还爱你。”
小女儿直接被吓跑。

第二次,小女儿再问:“你爱我吗?”
阿嬷说:“你爱我吗?你爱我的话,我也爱你。”
小女儿跑到她的妈妈身边,
说,“阿嬷都听不懂我说的话!”
第三次,阿侦再让女儿去问,
小女儿问:“阿嬷阿嬷,你爱我吗?”
阿女说:“我爱妳。”

小女孩笑得甜,
“阿嬷说爱我耶。”
拿起摄影机,
给她眼中的阿嬷留影。

“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一遍一遍地问,第三次,母亲才终于脱口而出——“我爱你啊。”
长达四十年,这对母女,终于走向和解。
金马影展上,黄惠侦特意把观众席的中央留给阿女,让她没法提前退场。阿女第一次,以观众的视角看了自己的人生,结束后,观众站起来对阿女说,“你是个很棒的妈妈,你很勇敢。”第一次,阿女感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和拥抱。
回家后,她第一件事是来到灶台前,点着火,架好锅,给阿侦煲汤做菜。
平常,也时刻惦记着女儿最爱吃的食材。

连着一个月,阿女的心情都很好,阿侦在家时,主动和她问东问西。
她也会像其他母亲一样,面上不在意,心内却悄悄地为女儿骄傲。还向朋友广而告之,自己女儿的片子要出国,去柏林,邀请他们也来观看。

(左起)雷震卿、林婉玉、侯孝贤、阿女和女儿、黄惠侦、制片Diana
2017年2月的柏林,追光灯打下来,舞台中央是涂着浓妆红唇,身着头盔制服、过膝长靴的高挑男人,拿着第67届柏林国际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的名单,身后一块环形屏幕,几部提名的影片旁,是一个双手相握的logo,一手肤色较浅,另一只手肤色深一些,指甲修剪整齐,甲油鲜红。
泰迪熊奖是柏林国际电影节专门为同性恋或泛LGBT群体设立的奖项,从1987年至今,已经举办了31年。

主持人念出了三个音节:Hui-chen Huang. 黄惠侦《日常对话》,是她。全场视线聚焦到这个不太高的东方女性身上,她穿着黑色休闲西服,短发齐腮,一副窄边黑框眼镜后,眼神好像总要和你温柔地碰一碰,听听你能从生命里,挖出什么故事。
这个夜晚是属于她电影人的高光时刻,此刻正在看着她的人里,几乎无人知晓。
她6岁开始在牵亡歌团工作,三年级从国小辍学,她度过了生命的前十个年头的地方,是一间弥漫着汗水、酒气、烟味、油漆味的小小隔板房。
从那里到柏林的这个夜晚,中间是她拿起摄像机拍摄自己的同性恋母亲的二十年。像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柏林国际电影节上的黄惠侦
影展后,阿女跟阿侦说,自己想买一辆新摩托。阿女骑着旧摩托,阿侦和女儿坐在后座。阿侦看着母亲的背影,不太宽厚,风呼啦啦吹,能体会到她沉默的欢喜。
他们一起挑了一辆浅蓝色的小摩托。阿侦嘱咐,不要用这车带女儿,不安全。母亲还是趁她不在,偷偷带女儿去庙口看歌仔戏。偶尔,她还会像个小孩和女儿抱怨,你妈妈,好啰嗦哦。
那个对谈的餐桌上方,浅绿的画框里,是女儿画的一对双栖蝴蝶。
像是台湾老派歌手黄安的一首歌,“在人间已是巅,何必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

“我当妈妈以后懂得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这世上没有任何关系是理所当然的,跟每个人相处都要从头去建立两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跟自己的母亲,还是跟自己的女儿。
没有人生下来是属于谁的,女儿爱你不是理所应当的,是需要你去经营的。当然也没有人天生就是父母,做父母是要学的。”
黄惠侦给她的人生,做出了最温柔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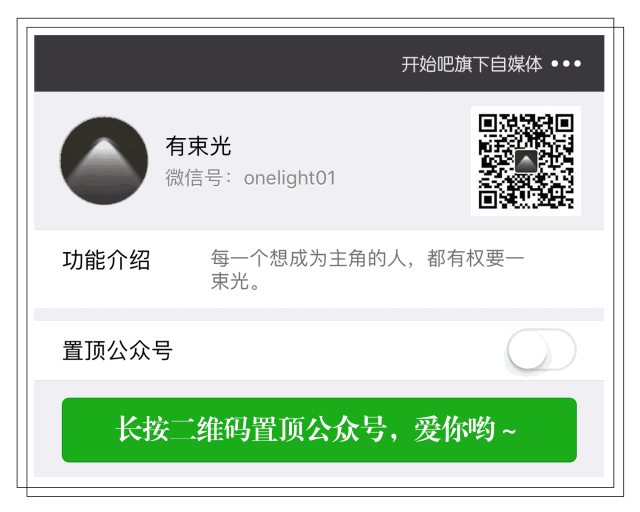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