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场 | 齐帆:求学浙大宾大,任教港大哈佛,他却最终选择了创业实践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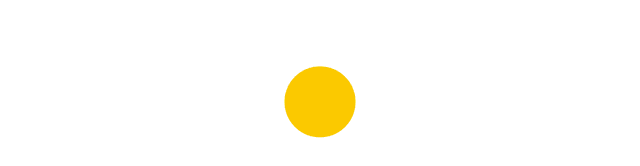

从浙大,到美国,往香港,再归重庆,
齐帆在近十年间,体验了不同的角色。
他强调,建筑人不能囿于自己的小圈子,
而是要跟上时代的脉搏,
用架构的理念来督促自己为城市的发展出一份力。
采访人 | 李
编辑 |李, 艺梦
本期人物
Qi Fan |齐帆
几里设计合伙人/设计总监

浙江大学 建筑学学士
宾夕法尼亚大学 硕士
曾任职于美国SWA Group和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学科导师,现为专注城市尺度综合设计的独立事务所JILI DESIGN几里设计创始合伙人。
以下为正文
A=ArchiDogs
Fan=齐帆
A:你一直走着一条令人艳羡的人生之路,那浙大和宾大有着怎样不同的求学体验呢?在港大的教学体验又带来怎样的收获?
Fan:浙大教学体系是国内学派,在日常训练里,把各种尺度到类型都走一遍,浙大的建筑学特色不在于学术深度有多深,而在于它像杭州这座城市一样很开放,学习期间有机会参与到很多不同的专业里,并认识不同系别的人,圈层的约束很小。
但它和美国的教育体系差异则非常大,本科期间习惯于一个学期做几个studio,国外则是一个学期做一个项目,在不同区域挖掘不同深度。国外学习强度要大得多,读研期间会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未来,该在什么领域做什么事,所以压力会很大。但自己对专业抱有很大的兴趣,研究生阶段学习非常投入,也是对学科体系和价值观理解最深刻的时候。
我在港大做教职期间,主要负责基础教育工作,以及和内地大陆高校的链接。大一时是通识性教育,港大的公共基础课程,主要涉及对城市、环境、人文的理解。而大三、大四的教育跟国内不太一样,国内是拿着教材告诉你,城市划分含哪些概念、考点是哪些;港大则更重视教育的互动,很有意思,理解城市的方法像研究生时代的方法,把城市剖析成交通、垃圾回收处理等不同方向,即细分到城市几个大的不同的点。
一年级学生组队会参与到不同课题里,比如说你选的课题是城市垃圾回收,那就去研究城市有几个垃圾回收点,这么大个城市,垃圾是怎么运作的,前半学期体验城市,后半学期组队后制定研究方法自己去调研。
A:也就是说实践性更强,那港大建筑学方面的教育又有怎样的特色呢?
Fan:学科内的通识教育要细分一点,建筑学院内部的通识教育就是研究城市空间、形态及结构。全校的通识教育,则是关注什么是香港这个城市,从交通层面、水的层面、垃圾的层面去全面解构城市,怎样去理解你所研究的这个方面,比如步行体系,郊野公园体系。研究生课程,更多的是组织studio课程,典型西方式的教育。香港更偏向于西方的教育体系,鼓励学生去做presentation,不停去自我研究、挑战和表达。对我而言启发更大的是,香港不同层面的基础性学科教育,以前只能管中窥豹,现在的两年时间可以全职参与到里面去,收获挺大的。
A:毕业时应该面临很多选择吧,为什么会独独挑选港大教职这份工作呢?
Fan:其实是对学术比较感兴趣,想趁自己年轻的时候,去尝试不同的职业。国外读书、国外设计、国内设计院,不同城市生活的状态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三十岁之前可以极致去体验的。一开始对学术这个体系很感兴趣,但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想着国内读博士,进高校,开自己的工作室这很安逸,这辈子就这么定下来了,于是想去了解这个体系,同时也想去体验香港的生活,接触到独特的教育体系。
A:的确是很棒的体验,之后选择回到家乡重庆工作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Fan:虽然我对教职工作很感兴趣,但学校这个平台成长很缓慢。作为一个有充分自我认知的年轻人,像建筑这种实践派学科,觉得自己没必要全职在学校,更大的价值在于实践和对社会做贡献。学校像个象牙塔把自己保护得很好,每天相对比较形而上,而我的心很大,想在我想改变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印记。



离开重庆十多年,之前对重庆的认知比较简单,但作为重庆人,对重庆是有很强的情感的,跟重大、川美做学术交流时,察觉到这座城市在发生某种变化。我希望能为这座城市做某种贡献,而不是简单地说我想造三座房子出来,我希望带来更多的资源,去影响它的进步,这会让我更有价值。
而深圳、上海这些城市不需要我,那里有大量的精英海归,是顶级设计师的乐园。我从这些城市是去汲取它们的营养,而在重庆,我们是输出,希望带给重庆一些东西。回来时自己想为这座城市多做些事情,我们有很好的学术资源,构思着把学术作为一种价值带入这种城市,所以就成立了几里工作室。
A:学术方向和实践方向都是致力于旧城更新中的各个尺度研究与实践,那几里工作室也是专注于“城市更新”吗?
Fan:一开始想做城市更新的,像成都是把重心更多地放在新区开发这一块。但渝中半岛,没土地能做新区开发,只能做旧城更新,生活方式的更新,比如成都的太古里,是成为更有趣的业态而不是传统的新区,高大上的尺度建筑背后,对老城里充满了想象。
A:所以从太古里的业态中你获得了怎样的灵感呢?在项目整合和跨界思考后,又如何在实践中尝试自下而上的更新方式?
Fan:太古里更多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业态,由非常有情怀和能力的地产商,买来做开放式街区。渝中区地很难拆,老城迁改成本很大,民间门面也极具商业价值,高度混合的建筑群,不能说拆了做个低密度街区。所以借鉴自下而上的方式,社会的效率会更大,通过轻投入的景观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介入一些新元素的刺激来带动整个区块的成长,区域具备更大的商业价值和旅游价值后,一定会有民间的资本和智慧介入。

比如太古里周围,年轻人一看,有大量的旅游经济价值,那我也想来开个花店,洋气的青年民宿,外区的更新便自然地自下而上。渝中区不见得有这样的机会,介入一个太古里来带动,但可以通过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来带入城市的更新。相信只要这个地方导入了很多人流和商业流,民间的资本一定会蜂拥而至。
如果本地居民租金提升,年轻人能开店,那便从城市的良性循环里获益了。现在要考虑的是,未来的更新怎么让大家都参与进来,政府投更少的钱,并且最大化刺激整个城市智慧的资本。
A:改造过程中,要找到异化、有历史价值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仿古、做仿古建筑街,城市需要独特的印记和价值,这点如何做到?
Fan:重庆一定要用当代的思维去看城市,活在当下,这个时代对好的东西的追求,对美的追求,对好的空间和商业业态的追求,是我们要去满足他们的。


做锦里的时候,是对城市文化一种很前卫的追求方式,仿古就是我们的方式。但现在我们的诉求,城市的眼界、格局、修养更进步了,这个年代不需要仿古了,锦里、洪崖洞都是二十年前的东西了,那是上个年代城市主流人群的倾向,而现在我们看,90后的意识已经走到前面了,没有旧的东西就展望未来,有旧的东西,就好好保护它。看70、80年代的老厂房觉得感动,那个年代的美学是这样,存在就是合理的。
但今天再去修一个何必呢,2017年大家喜欢太古里,又何必再去造一个锦里呢?比如今后大家又喜欢科技感,幻想未来,太古里同样也就成了历史建筑。
A:哈佛GSD把重庆作为一个城市实验室,你认为是什么吸引他们来到这座充满张力的城市,因为立体、魔幻吗?
Fan:重庆是个多中心的城市,没有绝对中心,而是通过桥梁隧道把各个区连在一起,每个商圈不会跨圈消费,每个区都有自己的shopping mall。而几里的合伙人中有哈佛的博士,便考虑哈佛大学有没有可能来重庆做个选题,做个studio,他们就很感兴趣。



哈佛大学的同学们正在整理自己的成果
重庆作为建筑学的范本城市,很有价值,很有意思,城市的地域具有多样性,我们也希望通过引进学术资源,从而能打开城市的维度。这座城市很立体、很独特,城市老东西、新东西对比,地形跟城市建设的矛盾,交通的层次,这些点作为建筑学研究的方向很有意思。
A: 通过学术课题的研究,对鹅岭片区有怎样的认识和改造呢?
Fan:鹅岭山上有个老厂房,它的投资人和我们一起来做了活动,很有情怀的艺术商人。鹅岭二厂我们局部参与,但对整片山体和老旧居民区的未来也有个认识,通过哈佛的学术研究,找到有意思的点,更新出来是会很有国际维度和独特性的,不是老旧的弄堂和胡同,不是简单的立面粉刷,而是通过独特的点刺激城市的更新,形成重庆版山地居民的大片区。鹅岭是渝中区最陡的地方,很有城市研究样板的价值,希望用以点带面,向外延展的方式来改变这个城区。



哈佛的同学做的分析维度的综合模型

最魅力的地方:小区域中不同尺度的建筑
更新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如投资强度、老建筑的结构、周边社区的居民关系,市政配套的不完善,处理地形地貌的难度,这都需要花精力去研究和应对,但从中也学到许多。
A:这次研究取得了怎样的学术成果呢?而且你们有个更独特的创举,就是把学术活动开放给市民,从中有别样的收获吗?
Fan: 学术效果很好,出书策展,对重庆而言,对学界、市民而言算一个思维维度的打开,深圳有双年展、本地活跃的学术圈层,重庆也需要提升自己的眼界、格局,学习怎么跟世界对话,同时也让世界认识我们。
至于开放给市民是觉得,学校对学校,城市建筑学的教育模式有点封闭了。只是建筑师之间对话,建筑师和地产商对话,市民会不了解这个专业。建筑学从没想过去做国民美学教育,去引导市民,可他们未来也许会影响你的决策,希望城市小而美的,都是来自于市民组成的个体,但他们对专业的认知有多少呢。市民或许接受仿古,但没接受到当代最先锋的思想潮,只有当代的东西才能让我们的商业和城市空间持久生存下去,我们需要传达这种观念和审美理念。
A:几里工作室最近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项目“混沌星球”,可以简要介绍一下吗?
Fan:是老工厂加一个混凝土的入口的建筑,混沌目前为现在国内最大的互联网知识分享社群,线上线下社群,里面是学术的分享空间,偏科技和创业类的。


混沌星球1687实景照片
我们希望把它建造得有仪式感和精神感,像教堂般,象征重庆新时代的知识堡垒。


知识分享空间
A:作为建筑师,你喜欢徒步旅行,这样的过程会给建筑设计带来灵感和启发吗?
Fan:对一个城市旅行,要徒步,才会有完整的感知。拿着地图走,可以丈量出城市的尺度,曼谷半小时只能走一点,而在吉隆坡半小时却走了很远,东京核心区从东到西走一遍,脑子里很熟悉这座城市怎么样,坐地铁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对城市比较敏感,不经意会看到很多小东西,很有趣的空间、咖啡店、画廊。又比如重庆,a、b两点之间会有十几种不同的路径,徒步可以感受不同的空间城市。
A:几里设计今后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呢?
Fan: 创业要懂10个纬度的事,而不是一个纬度的。当老板和打工是不同的,你要多方考虑,如刺激员工积极性,收款,税务,人际关系的处理等等。
未来想走得更有意思,去拥抱一些新的业态。建筑师要跨界,建筑师在互联网,IT界也有architect这个词,是构架师的意思,现如今走到现在小众的胡同里,建筑有些孤芳自赏,我们很美,但不能参与到社会更深层次的分工。未来我们需要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构架师,去整合城市产业里的构架,既能做设计,也能构架未来的城市更新需要的功能空间,而不只是做美的设计,希望能链接到学术的思考。
A:最后,对于现在年轻的建筑师,包括在学校的学生,可以给一些具体的建议么?
Fan:建筑师不能封闭自己,认为你的职业发展途径就那几种,地产公司、事务所、设计院等。未来社会是在颠覆性的进步,建筑师如果不主动地走出去,只是个设计师,这很被动。在学校里,不要只跟建筑师玩,玩一些很形而上的东西,要学会多跟互联网、艺术、工程、经济的同学沟通,很多行业是很开放的。
经济学很开放,建筑学很封闭,尽量多链接,因为我们是建构师,需要了解每个行业的发展,建筑走在前面去整合别人的行业资源,最后形成新的可能性。谈逼格的建筑理论,只会玩形而上的双年展,只跟建筑圈层对话,这样略显狭隘,未来是建筑和科技跨界的趋势,所以我们要有更开放的心态。
采访人 | 李
编辑 | 李, 艺梦
版权声明
版权归作者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ArchiDogs或作者获得授权
THE END
推荐阅读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