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一日体验后,我明白了什么是张弛有度的生活


原作丨Mary Mann
编译丨Anna
谷歌对待工作与娱乐关系的态度,真的能解答“专注无能”这一永恒的难题吗?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到Google找了我的朋友Walker。Walker在Google工作,但我并不清楚他的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但每次我们谈Google,话题就只停留在Google的各式福利上——无限供应的食物、健身房、免费小工具、游戏室等等。

Google游戏室
“你想来杯咖啡吗?”他问道,然后领着我穿过装修一新的大厅。大厅里赫然挂着一个巨大的牌子,上面写道:“正在装修,若为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不是要去吃午饭吗?”
“是的呀,我只是说,路上你要不要顺便来杯咖啡。”他说道。“我要去办公桌那块儿收拾一下,旁边就有厨房,你可以自己做杯拿铁喝。”

Google餐吧
在Google,每隔300英尺(约90米)就有地方给你做拿铁。当然这些“厨房”不止供应咖啡,你还可以自己做鸡尾酒以及其他饮料。在这里,我估计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捧上一碗新鲜出炉的爆米花,躺在公司的睡眠舱里看Netflix的网剧。至少现在,一个星期四的中午12:30,我就看到了好几个员工正在干这事儿。此时此刻,我心中涌起了对科技公司强烈的向往。
“是呀,这儿的日常看起来是很爽。”Walker说道。“但是呢”,他突然一个转折,“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的工资大概会高许多。所以只能说,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你说是吧?”

带有休息舱的Google办公所
不过此刻我并没有太把他说的话当回事儿,因为摆在我面前的正是一顿极为诱人的“免费午餐”。Google的小吃吧实在是太棒了,去一次完全不够,我吃完后又折返回去了两次。
唯一让我有些不解的是,在一盘草莓核桃布丁上,竟然贴着“含牛肉及猪肉”的标签。“那是指布丁里的凝胶。”旁边的一位Google员工解释道。
这位朋友身材短小、一头脏辫、穿一件印着一排代码的T恤。这家伙,打扮的可以说非常有Google的特色了。不知道还以为Google的统一着装要求就是如此呢。

Google员工穿这样
Google办公室的大致情况就是如此,也差不多就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员工普遍都很年轻,而且普遍处于两种状态之一:要么是在紧张地工作、要么是在用一种充满竞争的形式休息。
比如我在Google看到过一间“乐高房”。房间有一整面墙都是装满了各色乐高积木的抽屉;而挨着另一面墙的,则是各式用积木搭成的建筑——马、恐龙、双螺旋……全都是员工的作品。另一间房则是“火车房”。房间被设计成旧时期火车站的样子,而每一节车厢都是一间会议室。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按摩椅、弹球机、台球桌等等。
员工们会蹬着踏板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或者是全神贯注地杵在站立式办公桌后,一副眉头紧锁的神情,专注到让人心生羡慕。
在我看来,这么个地儿还差一台乒乓桌就完美了。“我们的办公室和Facebook太像了。”Walker表示。“但我们的电玩游戏品种还是很丰富的,这点算是个特色。”

Google的“乐高房”一角
“啥?”此时的我盯着眼前的一位女雇员走了神,于是又没听进去Walker说的话。
这位女雇员正捧着手机、躺在按摩椅上看节目,一面看一面哈哈大笑。她年龄跟我差不多,我甚至可以想象出我和她处于同一状态下的情形——当我躁动不安的心思归于平静,开始为下一阶段的工作积蓄能量的时候,我也会像她这样。
放松,意味着不会工作到昏厥,意味着不会像个磕了药的孩子似的不停用Google搜东西。放松的状态下,你也用不上Google;你本身就是Google,你能告诉自己你想要什么。想到这里我突然喉头噎住,也不知道是因为笑声还是哽咽,于是赶紧喝了一口Google特供的拿铁清清嗓子。这是我两小时内的第二杯咖啡。可以说味道相当好了。

看着这位女员工,我不禁联想到了我自己。
对现在的我来说,生活的节奏似乎并没有那么完美。
现在正是学期正当中的时候,并且我手头有好些个找我做研究的客户,工作量因此也在不断增加。对我来说,工作日开始渐渐和周末混为一谈,每一天都仿佛是一场漫长的、平乏无味的的跋涉。
我的所谓“休息时间”已经丧失了休息的真正意义。
每当我打开Netflix或者Instagram,脑海中就会跳出一个声音“干什么呢?快去工作!”取而代之的“休息”,变成了参观Google、频繁地刷新纽约时报主页、查收电邮这些看似颇具生产性但实则毫无意义的行为。
看看新闻、做做报纸上的填字游戏竟然还给了我那么一点儿“做正事”的感觉,因为这些事儿仿佛“拓宽了我的视野”、“锻炼了我的思维”、“拯救了我的拖延症”。但实际上,我分明就是仍在拖延。尽管焦虑感的加剧意味着完成任务的剩余时间已经愈加紧迫,我还是会由于焦躁而不断浪费时间。

我甚至曾经因为过度焦虑去看心理医生,想请医生帮我开治疗ADD(注意力缺乏症)的药物。
经过观察,医生拒绝了我的要求。“我不建议给曾经有焦虑情绪的人服用这类药物,”他解释道。“不管怎么说,你并不需要这种药物。你在ADD测试中表现很好。”但是为什么我在ADD测试中的高分,和我在实际工作中无法专注的问题存在不符呢?医生也无法解释。“以我在工作中的专注程度,我肯定是连ADD测试都过不了的。”我心里这么想。如果维持这种状况,我大概什么事都做不成了。

可是我想不通。
为什么我同时拥有两份很棒的工作,却还总是内心不安、无法专注呢?
许多人都和我有同样的困扰:纽约时报上就有一个专栏是在讨论这个问题的。专栏的一侧,还有许多来自读者的评论。
举两个例子,比如有人说“我因为不想写论文而‘沉迷分心’”,还有人说“即使是在读完这一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也至少断了五六次,只为跑去查收email”。
我认真看完了专栏边所有的评论,而且可怕的是,我现在开始认真看各种电影、书籍的评论了。正文或正片我看不下去,反倒是那成百上千条的评论让我耐心地一条条看完了。我还在心底理直气壮地告诉自己说,这是在做“社会调查”,不是不务正业。这感觉就像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节食者,在漫长的节食长跑中,仅仅是吃了一条无麸质面包,就开始为自己了不得的自制力欢欣鼓舞。

但是我又能奈何呢?关于如何戒除“数据上瘾”的文章早已看了不少,却都鲜有帮助。数据上瘾已经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就像带孩子、健康饮食这种问题一样,大家日日忧心、却又都拿不出好的解决方案。Baratunde Thurston是早期就讨论过这个话题的作家之一;2013年,他的一篇相关文章还曾登上过《Fast Company》杂志的封面。于是我把他请来,想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建议。
从我2009年认识他开始,Baratunde就一直有给我提许多建议。
那时他是我们数据部门的主管,而我还是一名编辑部的实习生。他会花很长时间、非常详细地跟我讲,如何成为一名自由职业的社交媒体管理者。我也正是靠着他的建议赚到了跳槽期的生活费。
社交媒体是他的专长所在,也是他投入极大心力的地方。
曾经一度,他的工作、娱乐都围着社交媒体转,以至于他不得不完全断绝网络来重拾自己的生活。
他在Fast Company的封面文章中就描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我没办法一边关注着社交媒体、一边工作”他告诉我说。“现在我大多数的创作工作都是在火车上完成的。因为那是我唯一收不到手机信号的地方。”

《Fast Company》:
与《财富》、《商业周刊》齐名的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杂志之一
“数据上瘾”似乎还不足以表达出问题的根源。
早在“数据上瘾”这个表述出现以前,或者说互联网发明以前,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社会评论家Neil Postman就曾在评论电视时说过,人们正在“把娱乐化变成所有经历的自然呈现形式”。
你也许觉得这句话显得夸张,那么不如感受一下以下这些发生在2015年的事儿:
- 奥巴马总统鼓励宗教领袖写出更具娱乐性的步道文章,以便与恐怖分子团体的招募视频进行抗衡;
- 新闻节目主播Brian Williams承认曾凭空编造事实以增强其战争故事的吸引力;
- MIT设计出了一种算法,它可以预测出人们对指定图片的喜好厌憎。他们甚至把该算法做成了app,好帮助我们找出更吸引他人的图片。

Brian Williams
所以,无怪乎我用心不专。无怪乎我们皆用心不专。
“数据上瘾”问题的本质其实并非科技本身,而是科技让我们产生的期待——对连续、稳定地输入我们生活的娱乐性内容、刺激性内容的期待。
或者我们拿罗素说过的一段话来表达这个意思。罗素生活的时代,恰好让他经历了电灯、收音机、电视的发明。他说:“相比我们的祖先,我们实在要无趣得多。但我们却比他们更为畏惧无趣。我们已经意识到、或者说开始笃信,无趣并非人类生而俱来的本性。”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
Google的办公处尽管塞满了游戏机、玩具、小吃吧,但也并不利于解决“数据上瘾”这一难题,甚至还是这一问题的加剧。而且,正如我的朋友Walker所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娱乐设施的投入会导致工资的下调。何况即使是提供游戏室、按摩椅的公司,也不一定是在提倡着最佳的张弛平衡理念。完全可能的另一种情况是,至少有一部分的Google员工,虽然看似在努力工作,实则却是在工作期间刷Facebook、看Beyoncé的演出视频。
但是即便效果不一定好,Google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工作状态:工作时就努力工作,玩乐时就放肆玩乐。
心理学家米哈里Mihaly Csikszentmihalyi(齐克森·米哈里)曾经提出过一个叫flow的概念。Flow的中译为“心流”,指的是一种将个人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感觉。多用用那些游戏舱、按摩椅,不要让自己的休息时间碎片化,才能在工作、玩乐中都体验到“心流”的幸福与充实感。

匈牙利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
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A. J. Liebling,二十世纪中期的一位纽约作家。他在写作时极其专注、或者说“用力”,以至于每次都会汗湿了自己的衬衫,甚至有时会对着自己写的散文笑出声来。每次写作完后,他都会去大吃一顿,至少吹掉两瓶子酒、吃掉好几只鸟禽。相比这样的“暴饮暴食”,我可能更喜欢别的的放松形式,比如看电影。但是,若能把Google和Liebling的平衡方式稍加结合,那么我相信一定能得出生活的完美公式。无论如何,平衡生活带来的满足感,值得我们一试究竟。
后台回复“资源”即可下载海量免费学习资源
你可能错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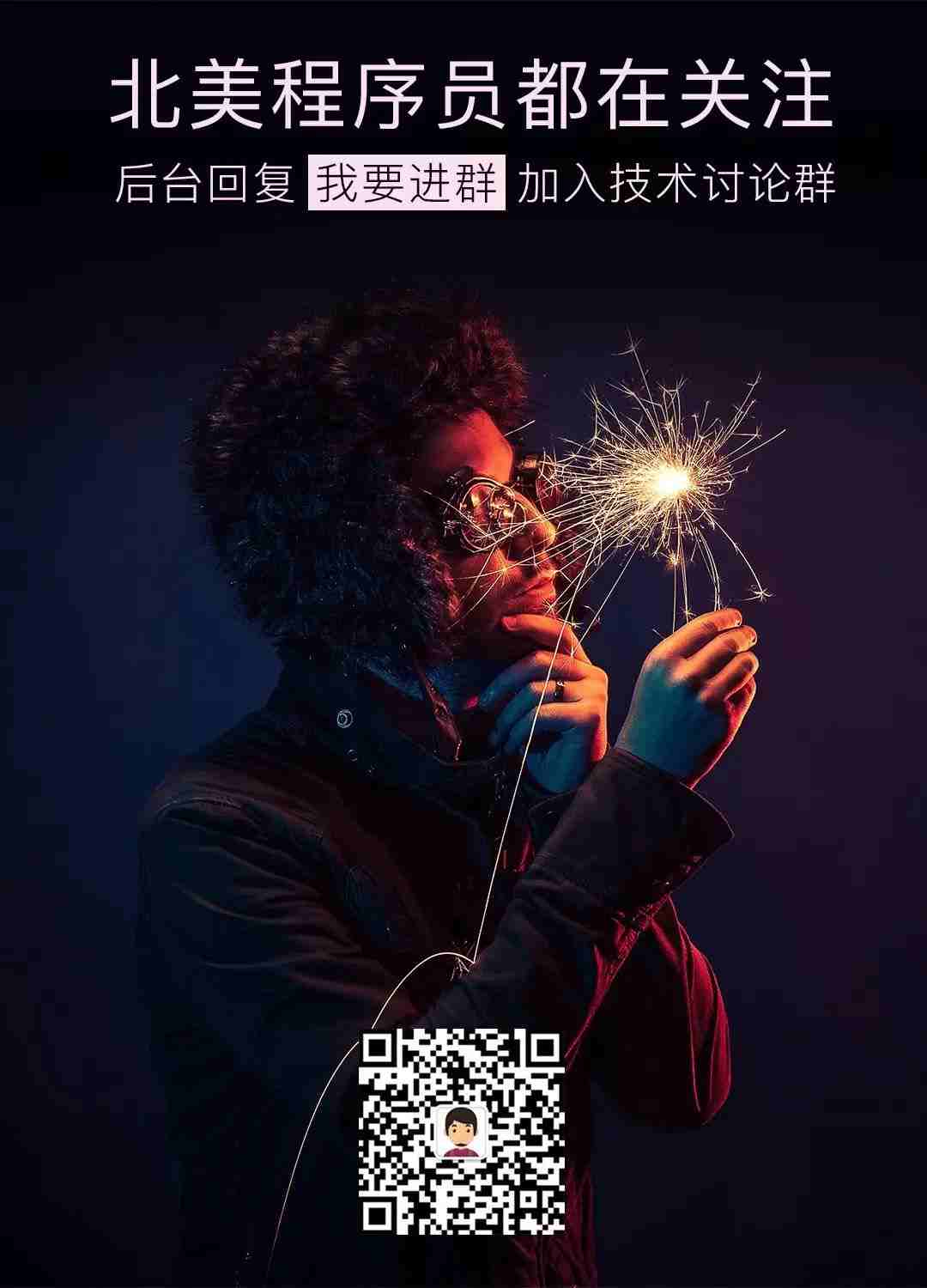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