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处,我听过的一门最有意思的课


本文授权转载自:别处World
微信公众号ID:else-world
这期互动,我们邀请了「别处咖啡馆」中的小伙伴们去回忆各自在国外求学期间上过的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门课。印象最深,不一定就是「最喜欢」,但或多或少,这门课为大家的生命带来过不同的可能性。
如果一门课程能够和「自己」真正产生关联,触动过心绪,就是最难得的。教与学的意义,也在于此,
我想到自己在博一时曾上过一门「台湾政经发展专题」,那门课的教授提醒我:情绪化的爱与恨,只是不曾参详史料的偏见。而因为那门课,对于台湾历史,我收起了很多从媒体、从口耳相传、从「别人都这么说」的角度获得的意见,而学会自己去找原始档案,去面对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也因为那门课,我的副修方向变成了「台湾政治」。
所以有时候,一门课,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吧。
选凝
于台北
◆ ◆ ◆
日本茶道课
@Hailan.J
坐标:北京
Lewis and Clark College/East Asian Study
老师是一位 60 岁左右的老妇人,非常喜欢日本文化,年轻时去日本进修了茶道和花道。我们上课的地点像是一个树屋,要走过藤蔓,走到半地下为止才能进去,颇有些与世隔绝的味道。
老师会提前半个小时,根据时令和季节对环境进行布置,有时候是一株当季花,有时候是一幅字,行礼、摆放茶碗、制茶、赏茶,每一个步骤都在缓慢而专注地进行,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此时此刻,和仪式的力量。

绿茶很清苦,配上老师从日本带来的小块甜品,然后听她讲述自己年轻时在异国的故事,很平常、缓慢的快乐。不刺激,但那种快乐可以印在我的记忆里,消除不去。
民族志(人类学系的一门专业课)
@Elevennn
坐标:Colorado Springs
Colorado College
因为比较奇特的 block plan(每月只上一门课)的学制,民族志这样需要走进田野、参访社区、自己做调研记录的课程就有了很多发挥的空间。
刚刚回到学校倒时差的时候硬着头皮补上了寒假作业:一本法医民族志。而后就在时常做梦梦到白骨和解剖大夫的节奏中,开始了上午批判写文化,下午去中餐馆聊天的吃吃喝喝学术体验。喜欢这门课不仅仅是因为活色生香的味觉体验,也是因为在频繁往返于市中心的中餐馆和学校的过程中,我渐渐清楚地意识到过分依赖大学所造成的脱节感。要在上午课堂里抽象晦涩的术语和下午剥的豆角中建立联系,也自我警惕要接地气,大概是这堂课珍贵的重要原因。
Cross Culture Management
@粲
坐标:墨尔本
墨尔本大学商学院
刚发送了第一封写给任课老师的感谢信,就看到别处发布的本次互动。
走到学生生涯的最后一学期也修读了不少课,想想还是感悟比感知更多。这次想说的这门课 cross culture management,授课内容并不算特别,甚至当初选课时也只是想将其当作水课,以缓解最后一学期的压力。在国外商学院读书的学生可能早已习惯了在放眼望去都是中国小伙伴的课堂里听讲,甚至讲台前还是一位中国老师。
不同的是,这门cross culture的教室里坐着来自澳洲、新西兰、美国、德国、丹麦、马来西亚、印度等各国学生。课程里安排了大量的案例分析和讨论,而学生的多样性正为这门课的学习提供了了非常好的分析样本。我虽也有过不少和外国朋友交流的经历,但却是第一次系统地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对彼此进行了解。
最后一堂课上,老师将相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分组,录下各组准备课堂演讲的会议过程,再在课堂上播放以让大家观察区别。那也是我第一次发现中国同学的小组需要较长时间进入讨论状态,领导角色较为明显;澳洲同学的小组讨论气氛热烈而吵闹,喜欢通过认同来表示反对;欧美同学的小组逻辑清晰,即便在最开始大家都没有想法的时候也会努力说点什么不冷场......即便观察样本很小,分析结果的确有点意思。

此外,这门课的老师在每节课后都会让大家写下心得和建议,再在下节课前进行小结。老师经常强调要给母语非英语的学生多些时间,并建议母语为英语的学生适当放慢语速。一些中国学生由一开始在课堂上的被动,到最后纷纷发言表达自己的见解,可能是其他课堂都较为少见的。
最让我触动的是,这位老师准备了非常多的有关的中国案例,通过和外国学生的深入讨论和分析,看着他们惊讶的表情,让他们认识一个新的中国,是一件让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甚至小小激动的事。
我一直提醒自己去标签化,但有时适当的承认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确是被各自的文化贴上了相应的标签,或许也是更好的「去标签」。
读研时的两门seminar
@水羊羊
坐标:美国
修读地点:密歇根大学
一门课是在生态学系,官方课程名是 Environmental 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嗯,这个名字很可能是错的,因为我的深刻印象全都在它响亮的民间叫法上:共产主义生态学。
开课教授 John 是一位须发皆白很像圣诞爷爷的生态学家,几十年党龄的美国老共产党员。环境生态学界左派很多,John 在其中算是比较激进的,研究生态学之余,他早年间还参与过美国和拉美一些国家的社会运动。跟他讨论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观点满满,有时非常强硬,自带耀眼的理想主义光芒。
我不知道 John 当初为什么把这作为一门课程登记在学校系统中,除了每周在固定的时间碰面,这门课没有固定教室,没有教学大纲,没有作业也没有考试,只是大家坐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著作、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与环境危机的关联。甚至,课堂里面的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都根本没有注册这门课的学分,来去自由,还经常有校外一些左派社团的人来参加讨论,感觉就像每周过一次组织生活。
作为一个纯理工科出身的环保主义者,我习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思考环境问题和解决方案,而这些讨论让我意识到环境问题还有其他方面。这个时代里我们大部分人的格局都很小,习惯于既有的社会运作模式也受制于它,即便有时察觉到社会的不合理之处,也缺乏智慧、勇气和力量去描绘不一样的未来。上百年前的共产主义者固然无法预见我们今日面对的问题,更不能给我们具体的解决方案,但至少我们可以从先人那里借一点想象力和信心,相信世界能够变得更好。

另一门课在环境学院,叫做 Food and Fuel,开课的也是个老爷爷,是一位环境经济学家。和共产主义生态学差不多,这门课的核心主题也是在社会制度中探寻环境问题的根源,不过课程内容就丰富多了。我们每周要阅读一些环境史的书籍,讲述现代农业、食品工业或者能源工业如何发展,如何影响环境;每周自行到附近超市、农贸市场等地方发呆一小时,观察食物和能源的流通;期末写一篇小论文批判现代食品或能源体系的一个方面。

开学时选课的有 11 人,三周之后留下来5人,还时有同学请假缺课,整个课堂十分亲密。我们的上课时间是晚 6 点至 8 点,九月刚开学时这个时段还是白天,后来日落时间逐渐提前,老师说既然我们探讨能源体系,先以身作则节约能源,大家想想如何能够不开灯上课……于是有一段时间我们每次课有一半是在黑暗中「瞎说」。记得学期中间有一次老师感慨到,他当年读博士时,很多课程都是这样小规模的,几个人和教授围坐一圈,进行一些深度阅读和深度讨论,现在呢,传授实用技能的大课多了,交流思想的小课很少了。
Critical Inquiry
@一览
坐标:美国加州
UC Davis
大一的第一学期,我选修了一门「水课」,亦即一般认为学分较高且难度较低的课。事实上,它带给我的挑战与影响远比我预想的巨大。它叫 "Critical Inquiry"。
这门课,如其名字所示,很注重批判性思维、怀疑、调查与研究。每一周,我们都会接受两堂两个小时的讲演,并参与讨论。从最早的「大学生与其社会责任」、「学术文献」,到「世界历史:从宗教到科学」、「医用大麻:利益相关者与立法」,再到「物竞天择」、「气候变化」,乃至「神经系统与认知」、「新闻与媒体」等等,讲演的内容海阔天空。
此外,约三分之一的讲座都由不同的客座教授提供,带来了更加多元化的体验,使我很受启发。尤其是分析事物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概念,使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之后我选修了微观经济学,并发现自己相比起自然科学,可能更擅长人文或社会科学。这也是促使我将专业从地质转为环境管理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像其他许多「刻板印象(同时确实没错)」的美国课程一样,这门课很注重小组合作。巧合的是,我这一组里的其余四人亦均是亚裔,包括华裔、越南裔等。说实话,虽然我念了三年美高,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活生生」的美籍华裔,与他们的交往也促使我对身份认同等问题进行了更多的阅读与更深入的思考。(PS: 推荐一本书,Vanessa Fong 的「Paradise Redefined: Transnational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 Quest for Flexible Citizenship in the Developed World」。)

这门课有期末考试,却仅占很小的权重。最有挑战性的是最终的学术论文与小组展示。
全班若干小组,被随机分配四个题目之一,互相竞争。我们组的题目是 "Plastic Ocean",亦即有关海洋被塑胶制品污染的问题。虽然大家因理念与能力皆相仿,合作得比较愉快,但一直没有足够的紧迫感,导致学期的最后两周简直是玩命一般地查找、使用资料。我们甚至曾浑然忘我地排演展示,不觉到了凌晨三点钟,租了一辆 Zip Car 一起去 Jack in the Box 吃宵夜。
最终,我们引用了约二十项一级文献、各自写作了逾三千字的论文(虽然可以一起查找资料与讨论,但论文是需要单独写作的),并合力做了十分钟的讲演。尽管未拔头筹,却实实在在地靠努力换来了一个 A,并为将来写作更加成熟的学术论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犹记得,那顿凌晨三点的宵夜,是我大一时吃得最香的一顿了。毕竟那一天(准确地说,之前一天),我们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我们当初学习、思索、奋斗的身影,现在依旧历历在目——就像那天快餐店里特别为我制作的素食汉堡一样,笨拙而又昂首阔步地前进着。(我才不会告诉你们,那位可爱的店员小姐姐,听了我的要求,想了想,拿走了鸡肉汉堡中的鸡肉与洋葱,发现仅剩一片生菜叶子了,于是给我加了几乎一整个番茄,以及几乎一整条酱黄瓜呢。)
酷儿理论
@shu_shelly
坐标:台湾
中央大学英文系
去台湾中央大学,我的主要目的是性/别研究所。研究所的创始人何春蕤老师是台湾的民运明星,她曾为妓权斗争。何老师有句名言:「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
带着如此纯洁的目的,我选了性/别研究所的酷儿理论课程。为什么选这门呢?主要是因为老师帅。
去台湾前我看了英文系的主页,就盯上了 Jonathan(肤浅如我)。等我开学见到他,他穿着紧身短袖,清晰地凸显了倒三角的身材和坚持健身的肌肉线条。我心里大呼:这么帅一定是 gay!(不出意料的话,研究酷儿的老师都是)
但是,Jonathan 的阅读作业很难,加上我学的专业姿势又太少,每次课堂上大家正热火朝天地讨论同性恋时,我时不时会弱弱地插嘴:「不好意思,drag(变装)是啥意思?」「sodomy 和 anal sex 有什么区别?」
但这反而成了我印象最深的一门课。

因为我读到 Gayle Rubin,她说最初婚姻是把女性当作礼物一样在宗族间交换,以巩固男性间的关系;我读到 Sedgwick,她说情欲三角(我们常说的三角恋)是在异性恋外壳下隐藏的男-男同性间的竞争又暧昧的关系;我读到 Judith Butler,她说我们不应该有性别的概念,连生理性别也需要被解构。我还读到有人说:越是恐同的人,反而是因为害怕暴露自己的同性倾向。
我想问,你的性别真的是你想的那样吗?
在这之前,我很少关注 LGBT 话题,因为我以为这个话题离我很远。但是,情欲本身就是流动变化的,不是吗?每一个人的性都像光谱一样存在着,比如性取向,你会偏直或偏弯一些,而决不会固定在一个极端。况且,作为女权主义者,我恍然意识到,LGBT 和女权其实是同一个阵营,当我想谈女权时,无法避免要谈 queer。

至于我们为什么要女权,为什么要学 queer,为什么要研究性别——我想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吧。
一节叫“The Design of Coffee” 的化工课
@括弧
坐标:加州
UC Davis
许多新生在入学前就听说过这门课了。「教做咖啡吗?听上去很有趣呢!」然后脑补出星巴克的小姐姐们左手磨咖啡豆右手倒牛奶的样子。
但是这门课并不是星巴克的工作培训,和制作摩卡或者拿铁也没有半点关系,既没有奶泡和糖来调味,也没有优质的咖啡豆,所给的原材料只是未烘焙的豆子和水。
这是一门向所有人介绍「化工究竟需要做什么」的课程,实验部分的最终目标是用最少的能量做出最受欢迎的咖啡,制作流程的每一个步骤都需要记录:用哪种咖啡豆、烘焙需要的时间和电量、具体的冲泡方式和消耗电量都要记录下来,最终根据之前的实验来设计自己的制作方案。考试会涉及到一些基础的反应动力学知识,除此之外也没有太大难点。

▲ 中间的光头就是教授
教授在最后一节 lecture 谈了下化学工程的就业方向:石油、食品、环境类的工作,以后就埋头在工厂里当苦力之类的。介绍完不忘抱怨一句:「你说我们这些化工人为什么要掺和这么多事把自己弄得这么辛苦?」
同学们都一脸茫然,内心 OS:对啊,我哪儿知道为什么随手选了个专业就这么累。这个时候教授卖了一碗鸡汤:「可是这个世界上,总是需要一些人来拯救地球的。」
这句话在当时听着特别受用。但是细想又觉得有点不对:怎么开采石油(消耗能源制造污染)和制作啤酒(培养酒鬼)就能「拯救世界」了呢?这一定是忽悠。
行为经济学
@老郑
坐标:成都
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商学院经济金融专业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相对新颖前沿的经济学分支,不被很多人了解。所以在我们学院,这门选修课很不起眼。在我那届,一开始还有大概二十多人选择了这门课程,试听期结束之后,人员折损一半。我猜大概因为这门课不像「金融交易编程」听起来那么「硬」,所以一些数学不好的同学一开始抱着「选一门轻松的课程捞便宜学分」的目的前来。其实老实交代,我也是如此打算的,只不过试听期结束之后,却舍不得「知难而退」了。而在课程结束之时,我和老师已经建立起了相当的友谊。
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是把人当成所谓的「理性人」看待,即人只有自私自利一种价值取向,头脑不受人性弱点的束缚,决策永远不带感情色彩,简直全知全能。基于这种极不现实的假设,经济学家门推演出的种种模型自然与真实世界相去甚远。大概他们也只能无奈地摊手,「谁叫你们人类这么愚蠢啊,我也没办法啊」!
最经典的的例子莫过于晚年的牛顿,自己闭门推算了一番之后杀进投资市场,亏得血本无归。大师临死前据说感叹了一句,「老子算得准天体星辰的运行,却算不过人心的疯狂啊」!
而新生的行为经济学,其目标就是把人类的种种「非理性」,包括利他行为等非自利的价值取向、情感偏好和人性弱点都包含在模型计算当中。这样做除了让模型推演更接近真实世界的运行规律,也让经济学家褪去价值判断的「上帝角色」。谁说给人带来快乐的只能有一种目标,一种价值取向?你自可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难道说别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就是经济效用为负的蠢货啦?
行为经济学这门学科,往大了说是结合了心理学、神经认知科学、信息工程、博弈论等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这门课上我们只是浅尝辄止,我们在课上做的核心工作,其实就是解数学题。首先我们把具体情形下的选择困境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再通过解数学题追寻答案。
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情形,说明一下数学语言是如何简练地概括人生境况的。
比如公司同事 A,B 两人做着同质同量的工作,彼此是很好的朋友,知根知底。两人的月收入分别为 X 和 Y 元,A 的效用(可理解为快乐程度)为 U(A)。
古典经济学假设 U(A)=X;这个很好理解,一分收入一分快乐。而在行为经济学者眼中,这个函数有着太大的改进空间。
首先可以考虑 A 可能有不只一种价值取向,除了想自己多拿钱以外,他还会和同事B做比较,甚至还因此产生两种相反的心理倾向。首先人衡量自己的幸福程度都要找一个「参照物」,而对 A 来说,做着同样工作的好朋友 B 的工资水平,就是他最完美的参照点。因此一方面,如果 A 的工资比 B 高,他会产生额外的幸福感;但另一方面来讲,假设 A 有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他干着一样的活,如果得到的钱比朋友多,心里会产生愧疚感,反而降低总体幸福感。
一般来说,人或多或少都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而且自己作为吃亏一方时,感觉更为强烈(但自己获利时依然也会感到愧疚)。
所以从最基本的考量入手,A的效用函数至少可以改进为 U(A)=X+a(X-Y)+b(Y-X)。a、b 均为系数,其绝对值和相对大小反映着A的价值取向。这还只是最简单的线性函数,考虑到人的主观感受通常不是线性的(你工资从 5000 涨到 1 万时非常快乐,再从 1 万涨到 1 万 5 时快乐程度递减),这个效用函数还能做出更精致漂亮的改进。

所以我当初为逃避数学选了这门课,却在每堂课上乐此不疲地推演着复杂的数学题,但心中并不感到厌烦。这位授课的印度胖大叔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第一次觉得演练的数学跟真实的人生有着血肉联系,不再只是模糊抽象的「空中楼阁」。当年课后和这位老师常一起散步去吃饭,从他口中得知当今的行为经济学已经发展到相当精妙的程度,模型数据都是在大型计算机上运算,心理学的最新临床进展也会被纳入行为经济模型的考量。
甚至他的一位学生,毕业后去到加拿大政府部门工作,运用行为经济学的思维为公共决策建言。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经济学工作的快乐和伟大。在那之前,我总以为所谓「国民幸福总值」之类的提法都是文创产业和宣传部门官僚们哄人的鬼话。那时才知道,原来还真有思维超前的学者们,在试图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实实在在地提高人们的幸福感,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作之一么?
当然了,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我当年在课上,推演过很多模型,亲手算过「拖延症」、「价值偏好不稳定」(即朝秦暮楚)和「短视」会对人生效用带来多大的损害。不过就像韩寒那句台词说的,懂得很多道理,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一群世界的异乡人,浪游在「别处」,谈论生活、人类以及美。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更多「别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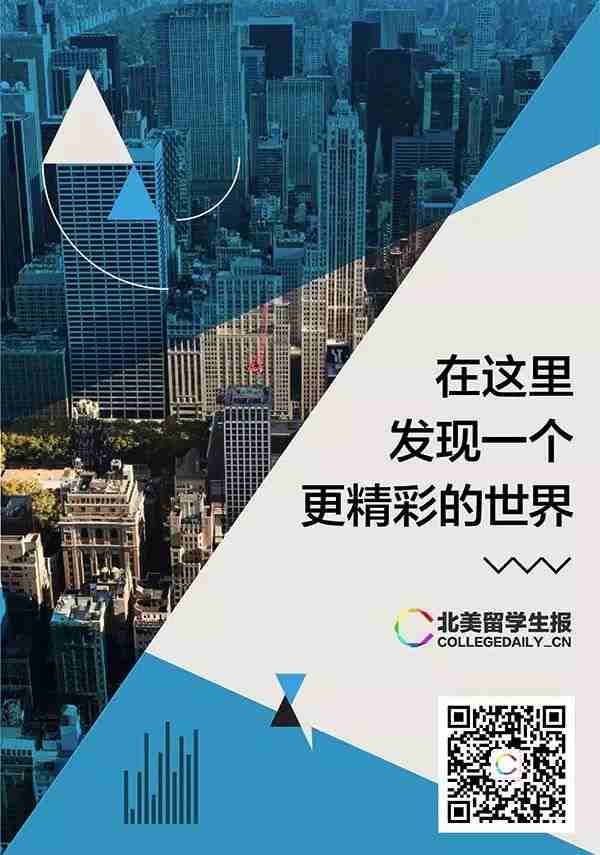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