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没有持久的传统

今年墨卡托沙龙以《传统与创新》为题的讨论里,主持人阿克曼向中、欧方嘉宾分别提出了这些问题:
创新与传统的关系在欧洲与中国分别如何理解,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在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和中国是怎样的?创新本身是否是一种价值观,创新是否必然意味着与传统割裂?
中国从来没有持久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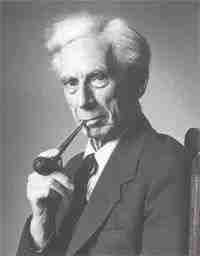
他写到: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反而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

在梁启超之后,张君劢、梁漱溟等人对此做了更加细致、更加有学术性的批评。
关于破坏和建立,传统和创新的关系,在中国具有复杂性,主持人阿克曼举了一个例子:
“山西大同是一个老城市,受了现代化的破坏性创新,所以前几年大同市政府决定恢复传统,把大同的中心地区全部拆掉,建立一个辽代的大同。他们建了一个八公里的城墙,在城墙之内把所有代表现代创新的房子,甚至最新的购物中心拆掉,开始盖辽代式的房子。”

艾伊娜因此联想到圆明园的问题:

“圆明园有300多公顷的面积,在考虑重建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在圆明园东部的地方重建一个楼,这个楼跟原来中国的传统没有一点关系,他们如果重建这个楼的话,要怎么重新注入传统呢?中国有时候希望对外形成一种形象,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有一些定式的期待,所以中国要满足国外对中国的期待。我们有时考虑在社会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样的想法也会成为一种推动力。刚刚提到圆明园和大同市这两个例子,就是使用符号来重新建造传统,这也是相当有意思的问题,我认为推动因素是中国要在国内外创造形象。”
◢ 微信合作请联系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