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银张宁:中国会重蹈日本《广场协议》后的覆辙吗?
平均阅读时长为 5分钟


张宁穿着黑色西装,清瘦的脸,镜片后的双眼闪烁着知识分子的光芒。
他走过来时,我瞟了一眼iPhoneX上腾讯的走势。我叹了一口气,关掉“自选股”App,拿出录音笔和笔记本,呷了一口冰红茶,打起百倍精神,希望身边这位畅饮苹果汁的中年男人能给我一些希望和答案。
我们在香港碰头这天,是五一长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中美贸易战剑拔弩张,双方谈判尚未启动,市场在不安的情绪中持续震荡。就连这轻烟弥漫的维多利亚港,似乎空气里也飘着一分低迷。
张宁是UBS(瑞银)中国经济学家。在他的客户心中,这是个“万事通”的角色,除了经济研究,什么领域都得懂一点。
“通胀起来,客户会问你养猪的周期多长,豆粕的成本怎么样,小猪从生下来到出栏要多长时间,猪农毛利怎么样、产能集中度如何。到贸易战了,客户就希望你懂中美贸易结构、谈判双方筹码、国际贸易法规或者是WTO规则。”他告诉我。
张宁说话语速不快,逻辑很清晰。我每问一个问题,他的回答都是用“一二三”。有时话题走偏,他也不忘把自己拉回来。
张宁服务的有海外和境内客户。对他们的提问,张宁得答得八九不离十,不能“懵圈”,至少逻辑要靠谱。一方面,他要知道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如何,煤炭钢铁去产能进展如何,另一方面,也要知道“抖音”、“B站”等新经济模式的用户规模有多大,低线城市小镇青年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倾向如何。
贸易战乌云笼罩以来,张宁从客户那里收到的问题包括:中美贸易争端如何演化、影响几何?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WTO的承诺落实了?美国总统有多少授权空间利用国内法律应对贸易战?中国会走日本广场协议后的老路吗?

张宁在Art Basel。他说这是卖方工作的写照。
老家山东的张宁,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本科四年给了他逻辑和定量思维的基本训练,但他很快发现自己空间想象力一般,“工程制图”那门课怎么学都没感觉,对经济和政策类的问题反而更有些兴趣。本着扬长避短的原则,张宁本科毕业后决定转专业,硕士和博士他分别读了管理学和经济学。
2011年,张宁从香港中文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思考良久,他决定进业界。“我知道做学术研究是什么感觉,我想去做实际应用,稍微接地气一点。”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国主权基金中投公司,接洽很多海外机构。在那里,他开始观察一些上门服务的卖方。有人讲演很精彩,逻辑严密,能抓住听者的注意力,有人内容不俗,却不太会讲,听得人打瞌睡。
等加入瑞银,成为卖方一员,张宁开始仔细体会这一行的滋味:专业能力、宏观判断很重要,需要不断地学习。
“要么你对某个问题有很深入的研究和多元的视角,要么你的分析框架更加清晰严谨,要么你有一手独特的宏观数据和微观证据。总之优秀的卖方研究要让买方客户觉得有一些新收获和附加值(value added)。当然,要么你就特别的幸运,市场和政策的方向感特别好,这个基本上是天赋。”
然而同等重要的是对客户的服务。“要放低自己,还要懂别人的需求。”在沟通中填补对方认知和需求的鸿沟。
作为一名在中国成长起来的80后,张宁发现,工作中如果可以“正本清源”,消除一些海外客户对中国问题的误解,为国内监管机构提供研究观点和全球视角做参考,就是“锦上添花”了。
经济学家要对市场和经济有一个直观理解、捕捉关键变量,并能进行逻辑推演。张宁说这是研究人员安身立命的本领。
同时,他们需要在市场中去锻炼感知政策变化的灵敏度。这往往是初出茅庐的新Ph.D最缺乏的。在学术研究领域,大家会寻找一个最优解,就是“该怎么办”。然而在现实中,卖方研究员和投资者更关心的是“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就很有意思了。有可能得到的十之八九都不是最优解,更重要的是这个事情会怎么样演化,出什么政策,什么时候会调整,这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他说。
过去几年,张宁所在经济研究团队获得了买方机构的持续认可。团队在近期的Asia II评选中排名第一,他个人在China II评选中排名第三。

张宁告诉我,工作中最大的成就感来自自己观点被市场验证的时候。判断错的时候,他会尽早反思,想想为什么错,新的变量是什么,假设或逻辑是不是变了,比如去年call错人民币的时候:
“去年最大的故事就是美元走弱,如果美元弱势是趋势性的,那么当前的人民币定价机制就决定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概率是偏强的方向。最重要的假设变了,你的call也要变了。”
我们的对话,就围绕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开始。
对话张宁
◆◆◆
春晓:交易门主编
张宁:UBS中国经济学家
春晓:我记得耳边还响着“港股今年上10万点不是梦”,结果梦还没醒,“中美贸易战”就来了。这世界到底怎么了?
张宁: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实际上是躲也躲不过去,迟早会发生的。问题在于什么时候会发生,强度有多大。中国贡献了近一半的美国总贸易赤字,假如说美国想降低贸易赤字,中国肯定是躲不过去的,贸易摩擦肯定会起来。
第二,全球供应链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最终端,它承接的是韩国、日本、台湾等其它地区对于美国的贸易赤字,经过中国的组装,然后运到美国去了。如果调整这部分影响,中国可能占了美国三分之一的赤字,当然也是最大的。这是一个大的判断。
为什么会有这个摩擦,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三个动机了。
第一个动机,美国要中期选举,需要巩固票仓,这是11月份的现实压力。这里边就是竞选承诺的兑现,和对本国产业和就业的保护。贸易政策毫无疑问要放到排头兵来做,所以是最大的动机之一。这里可能backfire(适得其反),譬如中国贸易反制措施里边最大的筹码之一就在于农产品 。如果贸易战真的打起来,可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美国农业州(川普传统支持者)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比如说大豆等产品。
第二个动机,川普有个美国优先的诉求,他是想去保护本国的利益,想去降低贸易逆差。不单单是川普本人,这也代表美国的部分人群的主流思想。这个思想是在反思整个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当然全球化的影响是美国的商品非常便宜,整个美国商品价格在过去的一两年基本上是通缩。商品没涨价,最主要涨价的是服务。这就是美国在享受全球化的福利。在那个过程里边,有些人是受伤了,因为全球化而使得美国传统制造业丧失竞争力。
第三方面,就是中期的一个考虑。回到五年前,甚至是十年前,中美的贸易结构其实互补性非常强。中国需要美国的一些技术和设备、农产品,美国需要中国制造的偏低端的消费品和加工组装的商品。但是到现在双方在贸易结构上的重叠性已明显上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会越来越高。为什么这一次的301调查,或者贸易争端核心的要素在于“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对新兴制造业发展的中期愿景和规划。这些行业还没有成为美国进口中国产品的主流,但绝大多数被美国301调查25%的关税清单锁定。美国的官方说法是,中国的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和资金支持,使中国企业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体现在强制技术转移、技术转让,授权费被低估,推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美国企业和技术,还有一些所谓的网络攻击等等。美国认为这是一个被扭曲的市场机制,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一个工具。但反过来讲,这是我们的后发优势,是我们弯道超车的一个过程。这是不同的立场得到的不同结论。
美国认为这一点绝对是一个问题和担忧。因为在一些比较新兴的行业,不需要海量专利技术积累和相应授权。比如说大数据、云计算、AI、机器人等,中国确实可以弯道超车。所以美国忧虑中国在这方面的崛起速度太快,会危及美国在这些重要行业的主导性地位。
这三个方面叠加起来,就能解释为什么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前两个诉求通过一些妥协、谈判,或多或少可以解决。但是第三个诉求,由于不同立场且调和难度很大,绝不可能迅速消失。所以即使今年贸易摩擦剑拔弩张的状态可以暂告一段落,但是第三个方面的冲突完全有可能卷土重来。这就是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中期诉求和短期诉求叠加在一起的逻辑。
春晓:我中学政治课学得不好,但我还记得,课本上写得清清楚楚,我国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只手一起用,任何一只都不能软。这是经我们改革开放40年来印证的卓有成效的经验。美国人是在装傻吗?这样的指责有一丝道理吗?
张宁: 多少有一些道理的,但是双方的立场不同。中国是一个转轨经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避免。中国引以为豪的是政策执行效率。当然中国的产业政策也有它的问题,往往对市场机制造成扭曲。不过可能正好有一些政策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因势利导成功了,但是之前有一些产业政策是失败的。
春晓:第一轮的贸易谈判似乎并不顺利。你怎么看接下来中美双方谈判和博弈的方向?
张宁:现在发生的事情叫做互相恐吓,美国恐吓中国,我要对你五百亿美元的商品征额外25%的关税,中国同样回赠一个相仿规模的反制清单,但是中国的反制清单生效时间取决于美国人最终的决策。现在中国的策略叫做以牙还牙、对等反制,并不主动多捅你一刀。即使大家看到现在嘴上往来都这么激烈,但实际的影响暂时有限。
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新的变量进来了,包括刚才说的第三方面引起的忧虑。比如说对华为的调查,以及对中国公司收购美国公司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以前我在中投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关注很多美国的并购和投资项目,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CFIU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近期来看,CFIUS主要的否决案例都是中国公司。
过去两三个月,大家会觉得中美贸易问题翻脸翻得比较快,时好时坏,情绪上的波动和对市场的影响非常大。不过最新的动向是大家终于要开始谈了。当然,5月初的中美贸易磋商几乎没有进展,美方狮子大开口,双方的分歧非常大。
我预计当前的贸易摩擦最终还是会通过磋商降温,尽量避免爆发大规模贸易战。不过这次谈判时间会比较长,双方纠结和反复的过程会比较痛苦。为什么?一方面是美国方面叠加了短期和中期的诉求;另外一方面,美方谈判的主力,鹰派色彩太重,没有太多平衡的声音在里面。

香港街头,摄影:Michelle Robinson
春晓:如果我们来看历史,日本在1985年、1986年的时候面临的困扰、压力和选择和现在中国是一样的。但是日本在汇率、出口、进口和投资等方面做了全局性的退让。现在中国会不会重蹈日本《广场协议》后的覆辙?
张宁: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现在的中国和当时的日本,有相似也有不同。相似的是我们的政策选项相似。目前比较理性的判断是中美互有妥协和退让。中国方面最终会使用“组合拳”,降低中美贸易顺差。这可能会和现在的贸易战打法基本相反。不过,美国要求2020年前降低2000亿美元的中美贸易顺差,这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即使是几百亿美元的规模仍需要通过多方努力。
第一方面,中国增加美国的进口,不过这个方面的限制不在中国身上,而在美国身上。当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规模只有150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对中国进口5000亿美元左右。这是一个极端不平衡的贸易结构。其根本原因是中美两国储蓄率、消费行为等基本面不同,但政策限制也是重要因素。一些高科技产品或是包含敏感技术的产品,美国人不卖。未来可能的中国进口扩容可以包括汽车、飞机、石油、部分农产品、不受出口限制的机电设备等。每一类产品规模都可以达到100亿美元以上。美国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十分值得期待,但存在很大难度。
第二方面,中国通过调整出口退税、减少显性的政府补贴,甚至是进行短期的出口额度控制等等,能够在对美国出口上有一些自我约束。不过这些是权宜之计,有助于减少市场机制扭曲,但无法解决中美两国基本面上差距。
第三方面,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现在的中美贸易结构是商品大顺差,服务小逆差。中国人对美国旅游、教育、金融、专业服务的消费需求旺盛,这是美国的优势。同时中国国内市场巨大,美国对此垂涎欲滴。国家领导人已经在博鳌上宣布了很多扩大开放的措施,包括开放汽车等制造业和金融等服务业市场,放松对外资持股比重限制,降低进口关税等。这是顺水推舟的举措,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步子会大一些。政府对这些举措的定位是自发的改革,但毫无疑问也受到了国内外压力的影响。这些措施的陆续执行会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美国经贸谈判中的部分诉求。
第四方面,中国增加对美国的投资。这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最主要的是美国对外国投资,尤其是中国投资的限制。这需要中美之间达成妥协和谅解。那么话说到最后一点,就是汇率会怎么样。
春晓:不是我不明白,世界变化快。我还记得几年前内地朋友排队来香港买保险的盛况。2016年人民币兑美元贬到了6.9666,大家都觉得换成美元很安全。但今年以来,人民币一路狂飙到6.3。几年前换成美元的朋友心碎了一地。好吧。我其实说的是我自己。请问,人民币会一路升下去吗?
张宁:在三十年前,日本把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方面一起都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日元升值。日元在1985-1987年升值超过90%,从240多升到了120多(USDJPY),这就是广场协议。这对日本的竞争力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这在中国不会发生。中国不是当年的日本,中国的回旋余地和政策工具的弹性比较大。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暂时不会放在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政策选项里面。美国当然会要求人民币升值,但贸易摩擦和不确定性升温会给人民币带来一些贬值压力。在2017年,得益于美元弱势,我们好不容易把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给恢复回来,汇率工具不会轻易用于贸易争端的攻防。未来更多的还是按照现行人民币定价机制,波动方向大概率上跟随美元对欧元等主要货币的走势。
春晓:我们现在是不是处在中美一个“新冷战”的开始?
张宁:这要看怎么去定义“新冷战”,至少这可能是一个大的格局变化。中美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好到像美国与英国和日本一样,也不可能差到美国和俄罗斯一样。中美之间有一些共同利益所在,也有一些理念分歧和利益冲突。中国继续韬光养晦是有必要的,也要学习、理解和“聪明”地遵循国际游戏规则。在未来的企业海外并购中,政府的角色可能会越偏向幕后越好,避免简单粗暴的直接干预。
坦白地讲,中国的崛起是大概率事件。我们的“走出去”、“一带一路”等战略中,中国是主要受益者,对其它国家地区的影响则存在不确定性。在未来战略落实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寻找合作共赢的理性策略,这是非常重要的。

北京朝阳, 摄影:Ryan Taylor
春晓:你刚刚讲到,现实世界里,我们十有八九得到的都不是“最优解”。做决策的人,也会有各种现实的约束。作为经济学家,你站在决策者的角度去看问题,怎么去把握大的脉络?
张宁:观察中国政策的大脉络,就是多重目标下的相机抉择,多重目标包括:增长就业平稳、风险防范、改革推进等。有些时候,多重目标之间是有冲突的,那政府会怎么办?我的观察是,在特定时间段内,哪件事重要和急迫,哪件事可能触发大的风险,那就着重应对哪件事情。这就是“相机抉择”的过程。
在这个多重目标相机抉择的逻辑框架下,如果各目标相安无事,政府就会争取齐头并进。为什么2017年政策偏紧、利率比较高、流动性比较差?核心原因是在于,在外需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政府发现保增长没什么压力,那么在多重目标中更加偏重于防风险和促改革,推进金融监管收紧防范风险,放缓债务扩张速度等,提前做一些排雷的工作。当然,去年政府最高层对推进防风险政策的决心是非常强的。
那么回到2014-2016年,你会发现那个时候政策偏松。当时海外市场十分担心中国经济硬着陆,在周期和结构性因素叠加下,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所有的微观指标,包括企业盈利、ROE、ROA、坏账率等,全都是在恶化。那时候最大的任务是稳增长,同时重点着手解决过剩产能问题。持续的降息降准和信贷大幅扩张,的确并非理论上的最优选择,也积累了新的风险和问题。或许壮士断腕会加快市场出清,但是政府的现实政策考虑是,通过宽松政策buying time,在相对平稳的过程中消化历史顽疾和寻找未来出路。
春晓:对于在思考进入业界做研究的年轻人,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张宁:我建议他们能够先慎重考虑一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想要实现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无论你是学经济、金融、工科或者理科,其实放长远来看,每个人自我实现的标准不单单是金钱。这要看我们的效用函数(utility)如何求最优解,金钱、生活、时间平衡、自我认同、社会价值对于每个人的权重是不一样的。
如果决定来业界做卖方研究,我觉得未来最大的趋势是中资外资会慢慢互相融合——当然现在还有很大的不同,这时候就要先权衡一下希望进入哪一类机构。
首先,外资卖方机构的特点是市场格局相对集中,比较规范,起薪较高,限制较多,上升路径相对缓慢。尤其是对于研究观点的内部评估过程相对较长、合规要求较严,估值体系更多参考国际标准,有些短期的投机性交易机会可能比较难把握。中资卖方机构崛起迅速,但市场格局很分散,研究强度非常大,研究员迭代周期也很快,职业路径有很大想象空间。一旦做出市场地位,薪酬回报十分可观。不过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需要年轻人很大的时间、精力和体力的付出。
其次,外资机构主要服务海外客户,当然海外客户也有很多中国人。瑞银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它有国内合资券商,可以海外和境内客户兼顾。大部分外资行在境内的业务非常有限。内资机构的境内客户基础非常好,它们想去扩展自己的海外业务,现在还是基本处于培育市场的起步阶段,需要逐渐建立tracking record和市场影响力。反过来讲,今年中国金融市场加快开放,已经有更多的外资机构筹划要进入中国市场。关于海外和境内客户的差异,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可以有机会再讨论。
第三,英语的重要性。外资机构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这曾经是一个重要的筛选标准,不过现在国内的年轻人的语言能力已经非常优秀,基本不是问题了。

张宁(前排左三)在香港中山纪念公园踢球
后记
◆◆◆
和张宁聊着天,一下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张宁起身和我告别。他还要回公司工作。
张宁每个周末都要抽半天时间加班。有时晚上也需要在办公室给欧美客户打电话。跟我见面的前一天,他在公司和苏黎世客户开一个视频会议,一直忙到晚上9点半。他回家时,快4岁的女儿已经睡着了。这让他颇为内疚。“小朋友的成长,错过就错过了,再也补不回来。”
我们见面前几天,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刚刚过完校庆。“无问西东”的帖子刷爆朋友圈。
张宁的本科同学里,有不少继续从事水利相关的工作,忙碌在水利工程、建筑设计、防洪抗旱的第一线,有的在当大学教授,做学术研究。张宁说他们“比自己聪明、也比自己勤奋”。
作为卖方经济学家,张宁的工作自带光环,但他更看重的是,自己在“跟随内心”,做着一份有乐趣的事业。他喜欢和客户朋友讨论问题,大家“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之下,摆事实讲道理,抠数据辩逻辑”。谁说服了谁不重要,他更珍视这个学习和收获的过程。
“当然了,赚钱养家也是很重要的。”他笑着说。
*声明:本采访仅代表张宁个人观点,不代表张宁所在机构。
张宁喜欢的经济学和历史书
◆◆◆
(前三本推荐读英文版)
《国际经济学》
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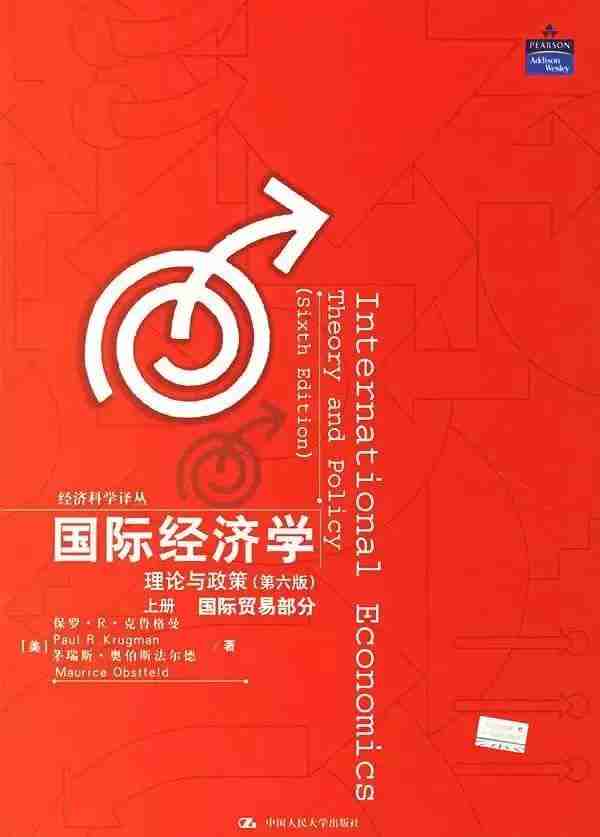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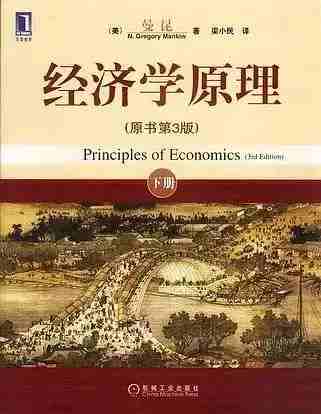
《经济学原理》
N. 格里高利·曼昆(Nicholas Gregory Mankiw, 1958- ),美国经济学家。29岁即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
《中国近代史》
徐中约(Immanuel C.Y.Hsü, 1923-2005),生于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主任、荣休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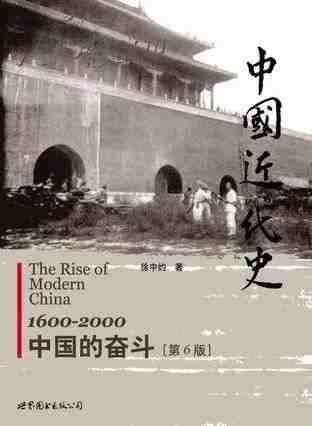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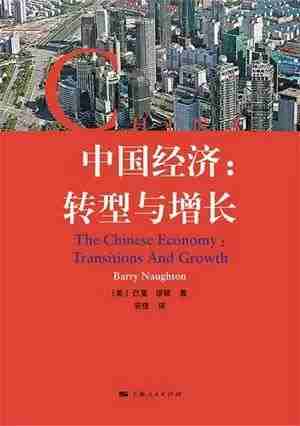
《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
巴里·诺顿,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经济学家。诺顿在中国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多集中在四个彼此关联的领域:经济转型、工业和技术、外贸、中国政治经济。
多看一眼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