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留学生:当你一往无前,别忘了身后还有人默默守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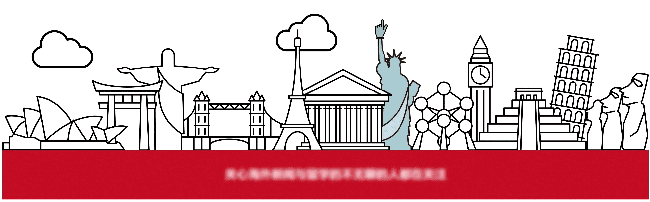
这是新媒体创作大赛的第十一篇作品
点击这里阅读往期作品
▼
候鸟
—陈恺宁—

后来我曾做过一个梦,梦见我置身于夜晚灯火辉煌的城市。忽然,满城的灯火消失了,我看见一片漆黑的森林突现在漫天星河的照耀下,回荡着我那传不出两侧山谷的呐喊,遮住了我那本不该醒目的影子。
我是姥姥姥爷带大的,他们是我最亲的亲人。
在我初中毕业那年,我来到了美国,告别了熟悉的同学和亲人,面对全然陌生的环境。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我剩下的能和姥姥姥爷相见的日子,恐怕真的不是很多了。

前年他们试着办签证来美国看我,被拒签了。姥爷告诉我签不过去也就这样了,他们看得开,他说就算过来了也是给我妈妈增添负担,还说了些美国的不好。
我知道这是说辞而已。我内心的矛盾就在于既想略带自私般地不用天涯相隔就能看到他们,却也不希望他们来这里被连语言都不通的土地所囚禁。
我姥爷说他们都看开了。古稀之年,他们都看得开。
人老了,是不是就都看得开了。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总觉得舍与得之间总是放不下该去的那一个。长大总是有代价的,或许在经历一定的事情之后我也会划向对岸,踩在湿软的泥土上,向过去的患得患失挥一挥手。
我在美国,与家乡相距千万里,从前的同学变成了通讯录上的虚无,家人变成了手机上每个月几百分钟的通话时间。
多少次在回美国与姥姥姥爷离别之前妈妈都嘱咐我在机场要坚强,千万不要哭,不能让姥姥姥爷看到。

今年9月22日,又是离别之日。我们仨看上去都很开心,姥姥姥爷和我。
“该过安检了”,我没走,我总是把这个时间压到很晚。“再不过就晚了”,我走过上面写着“送机人员止步”的自动门,那里是姥姥姥爷最后能目送我的地方。“再呆一分钟”,我说。
他们很平静地告诉我,“走吧,到那边好好学习,我们身体好着呢,不要想我们”。
我向通道走去,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看他们,使劲招了招手。我连忙扭过头又走了几步,直到确定他们看不到我几乎止不住的泪,然后转身,胡乱地拍了几张照片。

每次离别的照片,我一直在留着,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是最后一次真正见到他们了。
最后一眼,是在我过安检的地方,回头望,目光似乎穿过好远好远的时空,却也够不到十分钟前的身影。我尽可能克制着自己,却也几乎是哭着过的安检。
安检人员没有说什么,或许没有注意,或许早已习惯了他人遮掩着眼泪的一次次生离死别。机场和车站见证了比婚礼教堂中更多更真挚的祝福与眼泪,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
天底下是没有不散的筵席的,我知道的。
所以每一次与姥姥姥爷的聚散,我都会记着,当做一生里为数不多的珍藏。韩寒的《后会无期》里说过,“爱是克制”。

爱是克制住眼里的泪,不要让在意的人心疼;《后会无期》里还说过,“每一次告别,都要用力一点”。我们不知道还会再见到几次,所以请珍惜每一次的告别。
我曾经的语文老师告诉我们,所有伟大的文字都是在情绪达到顶峰的时候写下的,比如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坐在飞机上的我,试着把那时的心情写下来,可是我做不到。心情凝结成了一滴一滴的泪水,弄皱了我那迟迟下不了笔的纸。
似乎曾经的,所有的告别在一瞬间全部涌现在了我的脑海里,从第一天上学那个清晨的学校门口,到下午机场的安检通道,相同的背影对应着相同的目送。只是,背影长大了,目送老去了。

可他们也是从未离开我的。
有天夜里,通宵赶作业的我有点学不下去的时候,走出图书馆给姥姥姥爷打了电话,在那之前由于学业负担重,我已经有两三天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了。姥爷接起电话,听到是我,他很高兴,说我要是再不打电话他就打过来了,怕我出什么事。
没聊几句,姥爷对我说,“姥爷想你啊”。我顿时说不出来什么话,只觉得如鲠在喉。五个字,印入我的心底,触动了最脆弱的那根神经。

或许不知道哪一天我也会适应一次次的相聚离别,看做家常便饭。我只希望我总可以在夜里,茫然地拨通家里的电话,有人能立刻接起,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只是想你了。
作为留学生,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像候鸟一样,在每年的盛夏从大海的另一端飞回来,再在初秋飞回去。
而总会有一些人,会按时守候在灯火阑珊处,数着夜空中闪烁着的机翼,默默期盼着这一切。

我只希望,在那些凝望云端的日子里,你我安好,不见不散。
机窗外的白云遮住了我回望的视线,遮住了家。人都要有家的。如果没有了家,那么灵魂岂不是很孤独。
而我们,终究会经历孤独的。
不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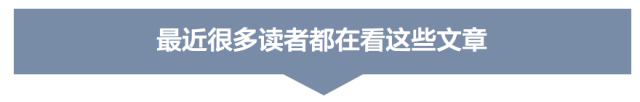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