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聊出内伤,谈话谈成吵架,有话好好说,为什么就这么难?



谈话不仅谈的是利益,谈的是情感,也谈的一个面子。
借对方的口,说出自己的想法,给对方一个面子,这才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有时候,你本来是想跟对方好好说话,可不知道为什么,说着说着就变了味儿。明明你的想法对大家都有好处,可为什么对方就是不领情呢?
今天,我们来看看《围城》里三场很难谈的对话,之所以说它很难谈,因为这三次,谈话的目的,都是领导想让对方(方鸿渐)走人。
我们知道,方鸿渐是个很有脾气人,那这三次谈话会不会变成吵架,聊成内伤呢?
第一次,想炒方鸿渐鱿鱼的人,是他的老丈人。
方鸿渐留学回国,暂时在老丈人的银行里做事。当然,这个老丈人只是挂个名,因为未婚妻早已过世。
这翁婿俩之间,一直很和睦,但挂名丈母娘与女婿之间,却始终矛盾不断。最后,丈母娘一发脾气,头疼病犯了,老丈人权衡再三,只得想办法送走这尊大神。刚好此时,方鸿渐收到了三闾大学的聘书,这就给了老丈人一个好理由。
老板要辞退员工,这本来就不是个好沟通的谈话。老丈人是生意人,认为没有钱办不到的事,大笔一挥,准备四个月的补偿金。鸿渐才做了半年,按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低了。
当然,这次谈话的真正困难不在这儿。这翁婿二人虽是假亲戚,却是真同乡,又是长辈对晚辈。老丈人的生意还要靠同乡多多支持,传出去,对自己的名声有损,这才是他真正担心的。
老丈人不愧精通世故,他的策略是先拿钱铺路,再讲人情。
于是,他精心准备了一套说话的剧本:先垫几句话,询问鸿渐是否答应了三闾大学的聘书,这是很重要的前提,如果女婿已经回复,这话题就可以很自然地转到旅行费用的问题上。
上海到内地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想必鸿渐也是在发愁,他肯定在想,怎么跟老头子要。
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说到这儿,老丈人设想的剧本是顿一顿,以加重下面的话的份量:“你听我说,我教会计科一起送你四个月的薪水,你旅行的费用,不必向你老太爷去筹——”
这话转得妙啊,从钱的现实问题,非常自然地转到人情的问题,接下去,就可以换成长辈的语气了:
“你回国以后,没有多跟你老太爷老太太亲热,现在你又要出远门了,似乎你应该回府住一两个月,伺候伺候二老……”
明明是要赶别人走,却要变成对晚辈的关心。他大概在想,里子你已经有了,面子总得给一个吧。
老丈人还设想了一套配合的肢体动作,“说到此地,该哈哈大笑,拍着鸿渐的手或臂或肩或背,看他身体上什么可拍的部分那时候最凑手方便”。
可惜啊可惜,剧本写得好,也要靠演员的临场发挥,偏偏好戏一上演,对方就不配合了。

老丈人刚问了一句“你回复了三闾大学的电报了没有”,就立刻感到接下来的话风不对了,书中说鸿渐“忽然省悟,一股怒气使心从痴钝里醒过来,回答时把身子挺足了以至于无可更添的高度”。
老丈人万万没想到,这个平时一向有礼貌的年轻人,此时正处于失恋地打击中,失恋中最痛苦的,莫过了自尊扫地。但失恋是私事,所有的气都在自己心里憋着,偏偏此时有人要捅着这个快要爆的气球。
鸿渐剌耳地冷笑,问是否从今天起自己算停职了。
老丈人赚钱的本事不错,但在与年轻人的沟通上,还是差点火候。他对自己准备的剧本太过自信,明明话风已经不对了,还是硬抛出“四个月薪水的补偿方案”,还让他“不要误会”。
鸿渐拿出“四大银行全他随身口袋里”的傲气,很硬气地回了一句“我不要钱,我有钱”。
此话一出,再无挽回的余地。
在很多关键的谈话前,我们通常会准备一套方案,这些方案往往都是利益交换,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对方是“理性人”,能够对利害关系作出全面的判断。
在老丈人看来,鸿渐住的是老丈人的房子,用的是老丈人的钱,他应该知恩图报,没有理由不给自己面子,这就是“理性人”的假设。
但实际上,正是因为鸿渐住的用的都是别人的,他的自尊也就特别敏感,以至于做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非理性决策。
就像他对老婆说过的一句话:“你总是一片大道理,就不许人称心傻干一下。你愈有道理,我偏不讲道理。”
“你愈有道理,我偏不讲道理”,就好像在说“老板你说得天花乱坠,还不是要我给你卖命”,这种心态,还能好好聊吗?

方鸿渐没想到,到了三闾大学,最后还是有人要赶他走,只不过这一回,那个人却没有老丈人那么喜欢讲道理了。
第二个要赶他走的人,是高校长,因为不喜欢他。
高校长面临的问题比老丈人简单一点,因为他要解决的是“合同到期不再续聘请”时的沟通问题。
我在《你和领导的差距,首先就在演技上——读《围城》,品职场》中分析过高校长,这是一个资深的演技派领导。但影帝绝不会轻易表演,比如这次,他就用了一个“躲”字诀,既不下聘书,也不谈话,希望鸿渐自己灰溜溜地滚蛋,就连例行的辞行,都避而不见。
对于鸿渐这种死要面子的人,这真是一个好办法。换成别人,早上门评理去了,大学里的教授,别看平时满嘴道德文章,一遇上利益,还不是“赤膊上阵”?
但方鸿渐太要面子,担心“自己冒失寻衅,闹了出去,人家说姓方的饭碗打破,老羞成怒”,最后还是选择了精神胜利法,“还他一个满不在乎,表示饭碗并不关心”。这下正中高校长下怀。
高校长比老丈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是学生物的,知道人有了情绪,就不能正常的聊天。而情绪是不稳定的,时间长了,就变成了酸楚,酸楚的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水和二氧化碳。
当然,高校长并没有把事做绝,鸿渐出发不久,便派人送去两样东西,一封是信,说明自己的难处,并告诉他已经向别的机构写了推荐信;另一封是红包,以结婚贺仪的名义。
所以高校长的不说话,是怕对方把话说绝。莫欺少年穷,凡事留余地,谁知道哪天还会再见面呢?

你可能觉得方鸿渐的憋屈,是命不好,因为他总是遇上那些小肚鸡肠的领导,但在《围城》里,他第三次丢了工作,却正是遇上了一个“正直”的领导。
方鸿渐的第三个领导,报馆的王总编,看上去是个很正直的人,顶着租界当局和股东的压力,发表激烈言论。
不过,一个看上去很正直的人,却不代表他没有私心。
方鸿渐收到好朋友的信,邀请他到重庆做事,而报馆的内部斗争又很厉害,就动了心,去跟王总编商量。总编认为不错,却劝他暂时别辞职,因为“他自己正为了编辑方针在向管理方面力争”,报馆说不定会有转机。
可王总编真正的考虑却是,自己正与股东谈判“编辑方针”,谈判都要有筹码的,他的筹码就是这帮跟他“同进共退”的手下。“同进退”意味着现在不希望方辞职,但一旦斗争失败,却又希望方辞职,以壮声势。
但问题是,方鸿渐并不是他的心腹,只是“多多益善,凑个数目”,一无交情,二无好处,王总编拿什么来说服他呢?
所以说,这次对话的难度,远超过前面的两次。
如果说高校长是个“阴谋高手”,那这位王总编算得上是“阳谋奇才”。
所以王总编接下来首先坦诚了自己的处境,又打消他的疑虑:“辛楣把你重托给我,我有什么举动,一定告诉你”。
虽然王总编没有什么好处可给方鸿渐,但有一样东西,王总编却给足了,就是面子。
谈判时,面子是什么?不是为对方着想,也不是给对方更多好处,而是要把自己的方案,包装成对方想出来的,至少是双方一起想出来的。
王总编是这么说的:“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各人的自由,我不敢勉强你”,这话是摸准了方鸿渐脾气。方鸿渐一直觉得自己“不能照原意去做,不痛快得很”,这次终于正义感爆棚,“自己单独下个决心,大有小孩子背了大人偷干坏事的快乐”。
结果,王总编斗争失败,鸿渐就很讲义气地“跟着国内新闻,国外新闻,经济新闻以及两种副刊的编辑同时提出辞职”。
相反,如果当初他跟鸿渐权衡利弊,竭力劝他跟自己走,说不定方鸿渐一跷二郎腿:“你讨论你们的编辑方针大事,与我何干?”
总结一下这三个人。
老丈人是个世俗商人,只知道以利诱人,却不能理解人,遇上话风不对,又拿出长辈对晚辈的老一套,聊天直接聊成内伤。
高校长是个奸滑政客,演技作做,略显浮夸,虽然避免了谈话谈成吵架的结果,但他做事太过滴水不漏,让人觉得自己老是被他算计,就算赔上个大红包,人家也丝毫不领情。
王总编是个精明文人,很了解方鸿渐这种“本领不大,脾气不小”的知识分子的心态,轻描淡写的一番话,就能把方鸿渐拉成自己的同盟。
所以说,谈话不仅谈的是利益,谈的是情感,也谈的一个面子。借对方的口,说出自己的想法,本质上就是给对方一个面子,这才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本文为“读《围城》品职场”系列第八篇)
近期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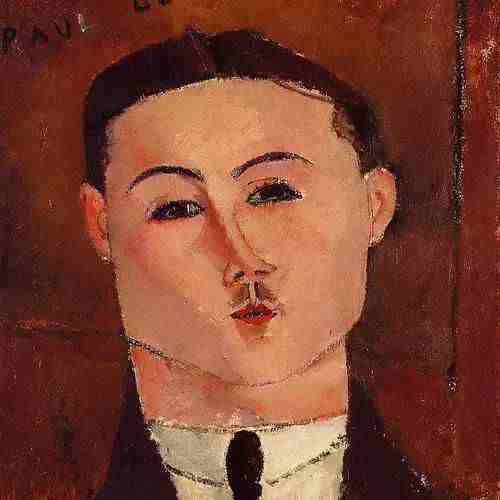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