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恐怖的少年犯:他跟踪女检察官整整三天,就为了咬她一口 | 较真的检察官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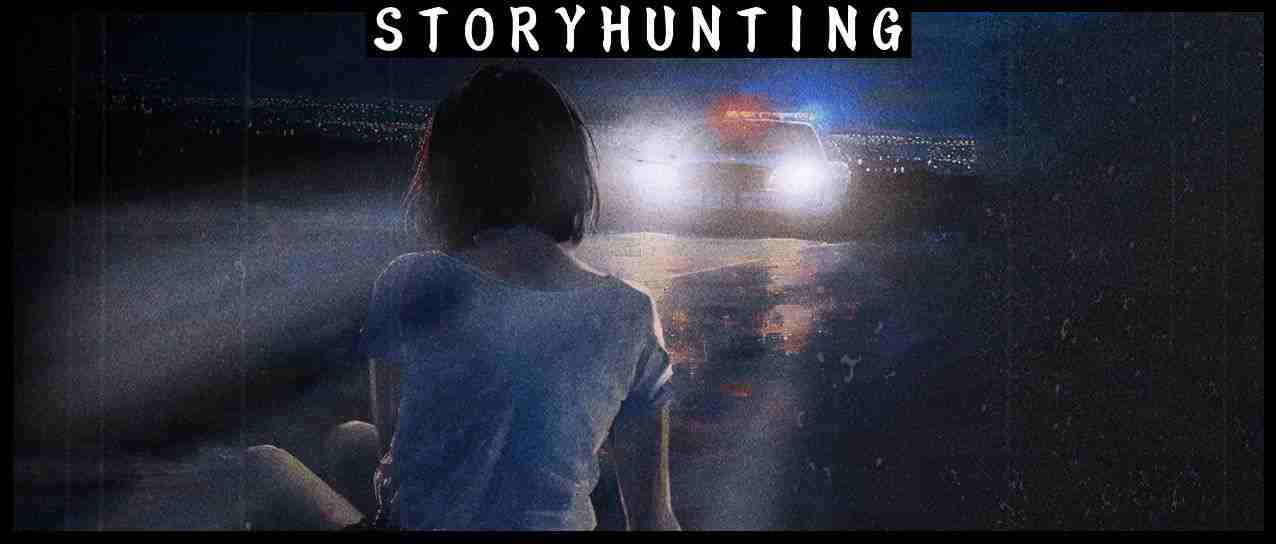
大家好,我是陈拙。
天才捕手有段时间没发关于孩子的案件故事了,这个群体一般不出事,出了就是大事儿。
我举两个自己还记得的例子。
几年前,我们写过一名少年劫匪,他带刀恐吓出租车司机,逼迫对方讲故事。他说自己太寂寞了;
更早一些的时候,还讲过一群绑架自己的未成年,恐吓父母给钱,想去看一眼电视剧里的西湖美不美。
孩子们是可爱的,但偶尔又是怪异的——分不清对错,闯出了大祸。
今天的故事来自检察官沈对对,同时也和一个需要分清对错的“孩子”有关。
她讲述这个故事之前,跟我这样感慨:“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遭遇袭击,没想过会出自一个那么小的孩子之手。”
2011年秋天,在我这十几年的检察官生涯中,是一段意义很特殊的时间。但如果要向他人讲述,我首先想起的会是那个夜晚,我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突然“袭击”了。
字面意思的袭击,先是听到有人从我背后跑过来,脚步声从快到慢,由远及近,我以为是夜跑,可那脚步太慌乱了,我带着疑惑回过头,就看到一个黑影已经冲到我跟前,径直朝我扑过来。
我下意识地弓下身把手护在身前,但还是被黑影带倒重重地摔在地上。
我的眼镜片儿飞了出去,先着地的脸颊骨被顿得生疼,左脸被压在地上,只能看见水泥地面。撞倒我的男人压在了我的背上,脸贴着我的后脑勺。
我能感受到他在喘着粗气,气流带着他口腔里陌生的气味,喷在我的后脖颈处。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我生活在这个世界最繁华之一的大都市,经常穿着制服出入看守所、面对穷凶极恶的罪犯,但这一刻,我好像突然才发现,这段小路、这个时间点,这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矮矮的一丛绿化带就把我和车水马龙的文明世界隔开了。我背朝着一个陌生男人,被压在地上,眼前一片漆黑,手脚都好像不是自己的了,什么反抗都做不出来——
突然间,我的肩部感觉到一道钝痛,伴随着湿热的触感。
他在咬我!?
这突如其来的攻击让我原本懵懵的大脑瞬间清醒,我用尽最大力气大叫起来,奋力地扭动身体。
男人似乎被我吓到了,我感觉到身上一轻,他爬了起来,接着是跑开的“哒哒”脚步声。
我左脸还压在水泥地上,听着脚步声越来越小,胸腔里像被扔进了几百只弹力球,突突乱跳不停,身体像在筛糠似的控制不住地发抖。
不知自己就这样在地上躺了多久,我试图挣扎着坐起来,手脚像被电过,僵僵麻麻的,脑子里一直在嗡嗡作响,胸口闷闷的。一阵凉风吹过,我忍不住哇地一声吐在地上。
我必须做点什么。我摸索着从裤袋里掏出手机,手指头因为发抖而不太听使唤,试了好几次才划对屏保解锁。
“您好,这里是110报警中心……”
和接线台小姐姐说话的时候,我才发现脸上已经布满眼泪和鼻涕。
我的大脑好像此刻才开始迟钝地运转:“他是谁?”“他为什么要袭击我?”“为什么是咬?”“他究竟想干什么?”
当时的我完全没法想到,这场袭击,竟然只是一个开始。
拨通电话10分钟后,一辆警车停到了我的面前,车头正对着我,车灯直直地射着我的眼睛,车上下来两个民警。
其中年纪大一点的民警拿着手电筒冲着我晃了几下,问我能不能自己站起来。我点点头,挣扎着想起身,但腿还像棉花似的软作一团,踉踉跄跄又差点摔倒。另一个年轻的民警用力地托住了我,把我扶上车。
两位民警把我带到了派出所。这家派出所我很熟悉,不记得有多少次和公安会商案件的时候来过。只是没想到这次自己坐在了被害人的位置上。
两个民警不认识我,只把我当一个普通的女性受害人,我正感到一丝庆幸,就听门外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你们两嘎头(方言:两个人)这么晚还有桑物(方言:工作)啊?”
是吴队。我不自觉地把头低下,但很快那个声音就钻进了房间:“哟,这不是沈大检察官吗?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驳回过吴队不少案子,他对我说话总是阴阳怪气的。但此刻我没心情回嘴,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张张嘴想说点什么,嗓子还是哑的,没发出声音。
看到我的脸,吴队的分贝马上降了下来:“你怎么脸都花掉了?”他快步走到我的跟前,微屈着身子,眼睛像个扫描仪似的把我从头到脚反复打量,“发生什么事儿了?”
我清了清嗓子,尽可能用最简短的语言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听到我被咬了时候,吴队顺着我指的方向,用两根指头小心翼翼地捏起衣领朝伤口看了一眼,“不好,伤口被咬破出血了。”他立刻吩咐民警带我去医院验伤、查传染病,再打个狂犬疫苗。
我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唾液传播艾滋病,这是一线民警都最恐惧的一种职业暴露。
凌晨12点,我被送到了急诊室。抽完血,我坐在检查台上,静静看着医生拿着尺在对着我的几处伤口比划拍照:
脸搓破皮,手肘和膝盖有些淤青,肩上的牙印变成了皮肤上两道不规则的半月形红圈,其中一处咬破了表皮,但伤口不深,表面出血已经凝固。
我很清楚,这些伤肯定都够不上刑事标准,但这就意味着这是件小事吗?那个黑影想做的到底是什么?
胡思乱想之间,吴队的电话打了进来。他告诉我,袭击我的人已经抓到了,“不过……”他欲言又止,让我做完检查过去再说。
走进提审室前,我已经想象过好几次黑影的形象,是五大三粗、凶神恶煞,还是面目狰狞、牛高马大?
我怎么也想不到,蹲在提审室角落里的,是一个不到1米5,稚气未脱、十分瘦弱的男孩。
一头短发凌乱地散落在他的额头上,脸和手上密布着许多伤疤,身上穿着T恤和牛仔裤,都是又破又脏,分辨不出原本的颜色。
听到我们走近,男孩抬起头,一眼在围观的人群中发现了我。一瞬间,他的脸上似乎掠过一丝喜悦的神色,很快又掩饰性地转开目光。
他认识我?
我转头看了看吴队,吴队用眼神示意我跟他上楼,去他的办公室。“这个小孩叫刘民,今年才16岁”,吴队一边说一边将UKEY插入电脑:“你看看他到底想做什么?”
吴队点开播放器,播放列表里是他下载好的十几段监控录像,录像显示,刘民在袭击我之前,悄悄跟着我走了一段路。在我倒地挣扎之后,他沿着马路跑掉了,但是每到路口就会停下来抬头张望。
“你再看看这个,这里是我们抓到他的地方。”吴队又打开一段录像,画面里刘民一个人坐在公园前的长椅上,眼睛盯着朝天四十五度的地方发呆。“你猜他在看什么?”吴队问我。
我一把夺过鼠标,用滚轮将高清视频的镜头放到最大,刘民向上张望的目光准准地和监控的镜头对上。
“监控!”
“他在确定摄像头拍到了他才继续往前走,然后又找了个离案发地点很近且有监控的地方等我们。”我盯着屏幕一字一顿地说,“他认得我,他在等我们来抓他。”
作为一名检察官,我的日常就是面对威胁恐吓:有申诉人每天下班在院门口等着我,说不帮他立案监督就要天天“护送”我回家;有杀人犯在栏杆那头一字一句地叫出我的名字,说“我记得你”、“我会找到你的”;也有纵火犯在我发言完后大喊冤枉,用最肮脏的字眼诅咒我全家。
我几乎从来没有害怕过,不仅因为我当时年轻毫无牵挂,还因为我相信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我做的是对的事情,他们只是困兽犹斗,我有什么好害怕的?
直到被扑倒在水泥地上的那一瞬间,我才发现,我是检察官,但我还有那么多赤手空拳、毫无防备的时刻。我的生命和其他人一样脆弱。
而最恐怖的,就是未知。我不知道刘民为什么认识我、袭击我。
户籍资料显示刘民是外地人,直系亲属均已经不在人世,没有案底。其它社会关系里也看不出有谁和我或者我办理过的案件有联系。
提审室里,这个男孩沉默地低着头。
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在本市有无住所?是否实施了袭击行为?……不管侦查员问什么,他始终紧紧咬着嘴唇。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如果审不出其他可疑的地方,拘传时间一到,我们就得放人。但我们又明明知道,他就是冲着我来的,只要走出这扇门,他随时可以再次找上我。下一次,还会是咬一口这么简单吗?
吴队抽了一烟灰缸的烟,终于同意让我亲自进去见见他。
我询问过的嫌疑人不比任何人少,早就不会紧张了。但这也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伤害过自己的嫌疑人,和一起没有任何线索的“案子”。
讯问室的墙面因为常年被香烟熏烤而显得发黄,我让另外两名民警先出去,关上门,和刘民一对一面对面坐着。
残留的烟味还在提审室里四处蔓延,身后的电子设备时不时地发出“滴——”的声响。我将胳膊摆在桌上,认真地观察刘民的一举一动。
从我进来后,刘民的脸就开始涨红,十指交叉放在胸前,右手大拇指在拼命揉搓左手食指指跟的关节,左腿不停抖动。
“你是想找我吧?”我率先开口打破了沉默。
刘民讶异地抬起脸看了我一眼,张张嘴,又低下头,我听见他接连发出几次吞咽口水的声音。
等待半晌,我再次打破沉默,“你有什么话可以对我说。我相信你有你的理由,也许……也许我能帮到你。”
听到这里,刘民舔了舔干燥的嘴唇,脸憋得更红,终于,他像鼓足了勇气似的盯着我,开口道:“你什么时候把我送进去?”顿了顿,继续说,“我会被关在A看守所的,对吧?”
刘民的话让我心头一动。我之前办过一个嫌疑人,因为生活无着,主动实施犯罪,想进我们辖区的看守所吃牢饭。“里面条件真的不错,比别的看守所好多了,冬天很暖和,铺位也宽敞,最关键的是,晚饭居然是三菜一汤。”这是我提审时,那个嫌疑人的原话。
刘民会是这样的原因吗?可他为什么选择袭击我呢?
我顺着上面的猜测试着跟刘民聊起来:“A看守所的条件是全市最好的,你之前有了解过吗?”
“没有,”刘民摇了摇头,“我……我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想进去呢?”我趁热打铁追问。
“我想找……”突然间,刘民似乎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突然抿了抿嘴,语气变得冷淡:“是我咬的你,你抓紧把我送进去吧。”
说完这句话,刘民就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之后无论我问什么问题,说什么话,他都沉默不语。
和他僵持了快一个小时,胸闷的感觉再度袭来,我赶紧起身,捂着嘴冲到门口,示意同事进去接棒,然后一头冲到派出所的卫生间里,吐个不停。
从卫生间里直起身,没有人发现我的异常,我又回到办公室。
虽然只说了几句话,但是刘民透露了许多信息。显然他知道我的身份,并且认为我“有权”把他送进看守所,看来这次的事件多半与我之前办理的案子有关。
我问吴队能不能让我查一下监控,在袭击我之前刘民在干什么,而他又是怎么知道那个时间点我会出现在那里。也许这样,能找到我们之间的交集。
审讯室里,吴队和两名民警还在和刘民拉锯,我睁大眼睛,一帧一帧看着重复的镜头。
猛然醒来时,我才发现自己在办公室里睡着了。已经是第二天早上9点,吴队敲了敲门进来,我们一对视,知道彼此都没有收获。
吴队试探性地问我,要不要先给刘民下个拘留,“关他一个月,看他还能憋得住不。”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只是咬我一口还构不上刑事案件的标准,吴队只是不敢把刘民放了,怕他再对我做什么。但我当然不能以这个理由破坏规定,立刻义正言辞地拒绝。
吴队脸色变得有点难看,阴阳怪气地“啧”了一声。
我心里有些愧疚,还是用冷静的语气说:“吴队,他是未成年人,诉讼流程本来就很麻烦,如果拘留还要通知适格成年人到场,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又补了一句:“这几天我先住单位办公室里。我会加倍提防这个小孩。”
吴队摆摆手,算是答应了。我精疲力尽地走出派出所,给科长打了个电话,请了一天假。
虽然不能拘留,但吴队还是帮我出了个主意,他说送刘民出所的时候,他们可以给他蒙上眼睛,把他直接送到救助站,然后告诉他要在这里好好改造。刘民没有案底,没蹲过“号子”,赌他会把救助站当成看守所,一时半会不敢往外跑。如果他有异动,救助站的护工会打电话告诉我们。
在这之前,我还是安全的,但时间非常紧张。当天下午,我就坐上了一辆开往郊区的公交车。
我的目的地,是在监控里最早一次看到刘民的地点,一个位于本市城乡结合部地区的路口。
原本我想找的是他从哪间房子里出来,也就是说他住在哪里,但时间有限,我不是警察,不能一直呆在派出所看监控。在我看到的监控再往前,确实没有找到他的身影,只能赌一把他就住在这附近的街上了。
这几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想要发现真相,线索常常藏在当事人曾经活动过的地方。
换了两趟车,在公交上吐了一马夹袋,我终于到了地方。午后的太阳晒得让我发昏。我走到监控录像所在的路口,顺着刘民出现的路径往反方向走。
那是一条坑洼不平的水泥小道,地上的裂缝里长着杂草,路的两边是两排低矮破旧的老式平房,大多数房屋的门窗都已经掉漆褪色,多处外墙的墙皮已经脱落,裸露出暗红色的墙砖。
我以最缓慢的速度在小路上行走,左顾右盼地观察每一户人家的情况。刘民认识我,大概率是和我办的案子相关,我想是不是有可能在这里见到我曾在案卷里见到的场景,启发一下我的记忆。
突然,两张贴在门上的白色长方形纸抓住了我的眼球——是公安的封条,有一间房子被我们查封了。
我小心翼翼地围着这户人家走了一周,贴着后门的窗户往里面张望,屋内乱七八糟,几张木头凳子歪七扭八地倒在地上,地上散落着纸张、衣物、塑料袋和一些生活用品。
我心跳得很快,我有一种强烈预感,这里是刘民住的地方。
我拿起手机,打电话给吴队,想让他帮我查查这个房子是因为什么被查封的,吴队接起电话却抢先开口了:“我们把刘民带回来刑拘了。”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埋怨,“沈大检察官,侬早点讲出来嘛,差点害我们放错了人,搞来(方言,意思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我没有说话,电话里安静了一会,吴队又补上一句:“侬别搞了,好好叫保重身体才是要紧事。”
就像昨晚被扑倒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一样,我的脑子里嗡嗡作响,只有一个念头:“他们知道了。”
刘民咬我的行为,没有带凶器,没有造成我的轻伤或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没有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唯一刑拘他的正当理由,就是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里的第五条,“随意殴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受害者的身份会构成加重情节。
唯一刑拘他的正当理由,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孕妇。我怀孕了。警方调取了医院的检查报告,得知了这件事。
而我之所以没有早说这件事,不是因为不想把刘民多拘一会弄清真相,而是因为我要隐瞒这个孩子的存在。
在所有人眼里,我还是一名刚刚工作三年,连恋爱都没谈过的单身女检察官。
根据内部管理纪律,未婚怀孕不仅仅意味着我之前一切为工作所做的努力可能都化为泡影,甚至还可能让我受到纪律处分。
而且,我是沈对对啊,一个从小到大只做“对”的事情的姑娘,一个别人想帮我刑拘袭击我的人我也会拒绝的铁面无私的检察官,这样一个我,竟然在没有男友的情况下怀孕了。
这多可笑啊。
阅读原文 关键词
检察官
民警
看守所
救助站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