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越久骂声越多,票房女王该见人了

贾玲减肥100斤的新闻,抢走了内娱开年的所有风头。
但为了在新电影上映前吊住期待,她本人已经躲了公众视野半年有余。
前阵的微博之夜,也是由张小斐拿着她的玩偶代为出席。
与此同时,许多质疑的声音也随之出现。
《热辣滚烫》翻拍自高分日影《百元之恋》,而原版女主则是亚洲现役最强女演员之一的安藤樱。
如何复现乃至超越原版,成为贾玲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加上一直伴随着贾玲的“无原创能力”争议,贾玲似乎越来越陷入毁誉参半的舆论旋涡。
已经坐到娱乐圈最高的导演席位,专业能力却不受广泛认可。
作为行业最有价值的女星之一,却始终被当成笑话。
明明在每个阶段都已经站得足够稳,却总冒着扑街的危险在开拓新领域。
这种矛盾感是贾玲总给人惊喜的根本原因,却也成了她在现阶段的困境。
贾玲啊,你究竟怎么了?
“女谐星”三个字,对一个女性艺人注定是沉重的包袱。
她们中许多人的上限只是同行当男艺人的下限,且永远不会得到观众的正视。
贾玲是其中极少数的破局者。
且在告别旧形象时,她的姿态是非常决绝的。
早在多年前,她就开始有意弱化自己相声演员的身份,嘴上说的是“走不下去了”,像是被逼退,但实则更有种主动转型的机敏。
来源@羊城晚报
贾玲试图在反抗大众对她的定义。
一方面她因为”搞笑”的标签打开了市场,建立了的事业,但另一方面,她又总在积极转型,好像压根志不在此。
而矛盾的背后,和她性格有关。
出生在湖北襄阳一个农村的贾玲,本质是个一心想出头的小镇做题家。
12岁时她被武汉艺校的老师看中,踏上表演之路。
为上中戏连考两年,第二年,就被戏剧和喜剧专业双双录取,成了那一年襄阳的明星考生。
后来师从冯巩,她大二就拿下北京相声大赛一等奖,在相声这个女性不友好的圈子,算是很难得的成就。
在这场比赛中还有另外两个我们很熟悉的人:郭德纲和于谦,他俩只拿下当年的第三。
会发现,小镇做题家的惨和足够优秀在她身上同时呈现着。
然而,她走的又不似一个标准做题家的人生路径。
一个把人生关卡都当做考试对待的人,不会给自己留太多旁的念想,反而会把抓到手里的每道题都想办法做得明明白白。
贾玲不是的,她是有心气儿的。
当初艺考时,她甚至没把这考试看得有多重,玩也似的就去了。
再到大学毕业时,姐姐贾丹又给她在老家找了份公务员的工作。
月薪3000多块,在当年不说大富大贵,也够过上中产生活了。
但当时毫无经济来源的贾玲却拒绝了这肥差,她选择留在北京追梦,坚决不回家。
这选择就不太“做题家”。
真的被贫瘠逼急了的人,很难这么轻易地让出好容易得来的稳妥,转而继续奔向虚无。
但你说贾玲是那种不顾一切的野心家?
又不太像。
在毕业后,她足足有五六年的时间在北京漂泊、迷茫,四处打工过活。
那段时间,姐姐贾丹每月要拿出一半的工资接济她,这也不算什么,难的是看不到出头日。
一直没能扎根北京的贾玲,一年又一年地哀求姐姐多给她些时间。
面对看起来永无出头之日的妹妹,贾丹直接崩溃了,但还是把她供到了27岁。
27岁,是贾玲登上《春晚》的年纪。
这在大部分艺人看来,都是不敢想象的年轻有为。
但之于贾玲和她的姐姐,已经是无法支撑的极限。
于是,贾玲身上呈现出一种模糊的底色——
比起做题家她太理想了,比起野心家她又太踏实了。
她相信世间有飞升的神话,却选择了用最朴素的“熬”字诀去接近天际线。
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她为何走出这样起伏的事业轨迹。
这背后,多少有种自我补偿心理——
在未成名前,贾玲是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自我压抑的。
妈妈没去世前,她是家里那个最受宠、最不懂事的小女孩。
二十多年前,她的生活费就有两千。
十八岁了,还大大咧咧躺在爸妈中间,给他们描绘着蓝图,“我将来成大腕了……”
但妈妈李焕英的离去,也带走了她不长大的资格。
一个让飘印象深刻的片段——
当贾玲拒绝姐姐要她回老家的请求后,贾丹的反应是不断追问,万一走错一步可怎么办?
只有少年才能莫问前程,成人的世界总是得步步为营。
这是一种对现实无法控制产生的焦虑。
而这种焦虑,如今不得不由贾玲自己背负。
高三考学时,姐姐和她分别考上了中传和中戏,但因为家里只供得起一人,姐姐便把名额让给了她。
妈妈去世后,姐姐又继续供贾玲上学。
当时她一个月工资1300,通常是先给贾玲寄500块钱生活费,剩下的大部分还要攒起来,只留给自己一两百开销。
所以贾玲的优秀往往带着一种“交卷”的意味:看,你的牺牲没有白费。
但压抑久了的人,很难在放榜后还在考场老实坐着。
起码,会想着办法换个考场。
其实,贾玲一直是想学表演的。
当初考中戏时,妈妈给她误报上了喜剧表演专业,让她与自己的初心擦身而过。
时隔多年,她依然对这件事无法释怀。
我学了这么多年表演
你给我报了个相声班
我一窍不通啊
怎么能不遗憾呢?
贾玲从初中就开始学表演,自青少年时期起,所有荣耀皆来自于此。
12岁就得到专业老师赏识,时隔一年正式考武汉艺校,当时武汉在下属县市只开放三个录取名额,她又成为珍贵的三分之一。
所以第一年没考进中戏戏剧专业,她独自留在北京打工一年,筹到报考费,坚持二战。
这时,就能看出她不顾一切的轴劲了。
本质,贾玲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她可以是做题家,但她只做自己想做的题。
唯一的问题只是,表演和导演都是天赋+训练的事业,仅凭执念不足以攻克。
贾玲是一个很好的喜剧表演者,但在戏剧与电影领域的修炼却是有限的。
对比马丽,看似与贾玲的事业轨迹类似,都是从谐星逐渐往影视圈发展。
但毕业于中戏表演系、曾于北大戏剧研究所深造、常年活跃在话剧舞台上的马丽,走的其实一直都是严肃的科班路线。
因为有这层背景,马丽从来不会对“谐星”这个身份有抵触,也很少给自己摘标签、撇关系。
瞧她谈喜剧时自信的神色,她觉得自己是因为戏剧素养足够好,才有本事演喜剧。
但之于贾玲,她永远没办法带着这种底气去谈喜剧。
在她的认知里,演喜剧是误打误撞、身不由己,类似于高考掉档或是服从调剂,她没得选。
正因此,她才会这么急迫地追求转型,弥补遗憾。
马丽骄傲于科班出身,所以自信也能玩转喜剧,条件好的人自然更容易自洽。
贾玲则是遗憾没能科班出身,所以搞喜剧怎么也不得劲,这又得是委屈过的人会懂的心理障碍。
我从来都觉得贾玲是国内水准颇高的喜剧演员,但她自己不认同。
她总觉得陷入瓶颈、无从突破,但这究竟是实情,还是她说服自己重拾影视梦的心理暗示,我们不得而知。
来源 羊城晚报《贾玲:相声是男人的天下》
总之,后续她产生的各种创作问题,也让大众不得不接受了她的转型。
相声小品这套,贾玲好像真的玩不转了。
此时的贾玲已经奔四。
年龄对一个喜剧演员的约束相对不大,但对一个女明星却是实实在在的危机。
也就是那两年,她自己的娱乐公司也正式成立了。
所以此时贾玲的转型,除了有个人意志原因,也掺杂了更多的现实因素,是尽力在市场和个人喜好之间的平衡和不断调整。
那时她接拍了不少质量平平的电视剧,可视作积累演艺经验、加强新身份的无奈之举。
连她自己都说,并不爱演电视剧,只是拍着拍着习惯了。
2019年,影视作品厚度还没攒起来的贾玲,突然宣布自己要执导筒。
按事业线来看,这多少显得有点急功近利,追梦不是问题,可不会走怎么就起飞了呢?
那时贾玲给出了一个情感上没人能拒绝的解释——
她等不了了。
过去还在吃苦,还在艰难求生时,她可以暂且把这份遗憾放一放。
但如今已经与理想无限近了,她必须完成这部作品。
但这一部呢?
我能理解理想主义的贾玲此刻对新事业的渴望,但在这条路上老天已经眷顾了她两次,27岁登上春晚,37岁成为导演。
我不确定这次她能否延续辉煌。
当一个导演的门槛真的很高很高。
当然,贾玲不是没有她的优点。
作为女性对群体发自内心的共情,作为弱势群体对普通人的敏锐感知。
更别提《李焕英》里饱满到几乎要溢出的情感,这是用什么高超调度技法都难以实现的。
而在她一路折腾,绝不认命的过程里,我又看到了一个女艺人蓬勃的生命力和对向上的冲劲。
说到底,《热辣滚烫》是贾玲不得不迈的一道坎。
若成了,她的理想便落成现实,多年来的执着可以兑现。
若不成,也算是给她一个契机,去重新审视一路来的选择。
前半辈子,贾玲都在为“李焕英”而当理想家。
而这一次,她必须为了自己去拼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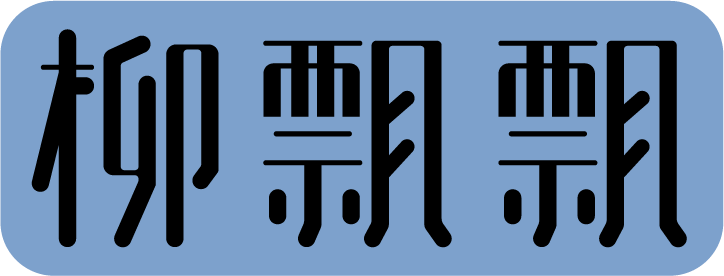
贾玲的困境,还需她自己来解决
↘↘↘
阅读原文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