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里的科学家活在2023年,能搞出什么惊人的名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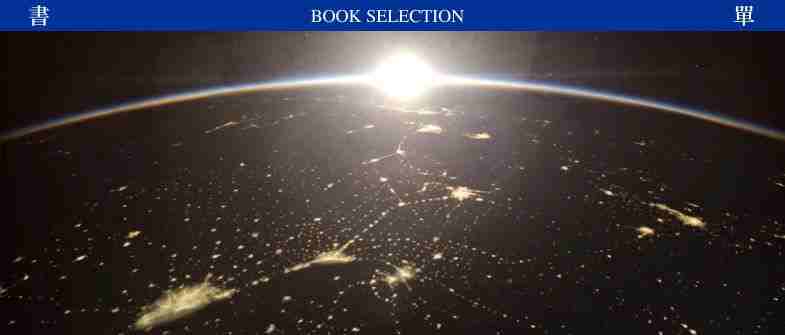
在很多人心中,《三体》就是中国科幻小说神一般的存在,刘慈欣描画的未来世界也唤起了很多人对于科技大停滞深深的恐惧感。
在《三体》故事中,人类之所以无法同三体世界正面较量,其中有一个重要设定就是三体人向地球派出了几颗可以操控的微观粒子,也叫“智子”。
三体人利用智子,干扰地球上的粒子加速器等重要的科学设施,让人类没法继续探究物质的本源,从而彻底锁死了人类的基础科学发展水平。
● 《三体》中物理学家杨冬所留遗言“物理学不存在了”
在此后几百年,人类的物理学水平长期停留在牛顿三定律、相对论、量子力学的水平,没有任何实质性突破。
等到地球真的面临三体人进攻时,人类毫无还手之力。
虽然刘慈欣创造的三体世界不是现实,但我们很清楚,人类的物质世界发展到今天,从硅基芯片到量子计算,从零碳能源到抗癌药物,如果没有科技水平的提升,就没有扎实的产业升级——想要实现社会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抬升,无异于痴人说梦。
因为如果没有牛顿三定律,我们就无法了解物体运动的规律,就不了解物体受力和物体质量、加速度的关系,那么从汽车到火箭,一切现代化的交通运载工具都不可能实现;
如果不是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首次做出了理论诠释,太阳能电池就不存在任何科学基础;
如果没有普朗克为量子力学的大厦奠基,我们去医院根本没办法用上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来做检查。
这些科学家的思考和研究,在他们当年或许只是形成了一篇篇论文,但经过漫长的时间,最终都有力促进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如此,它必须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的进步。
但基础科学研究必然要面对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当它处于脆弱的萌芽阶段,它经常被人忽视,甚至遭人嘲讽,它的缔造者——那些籍籍无名的青年科学家们往往是孤独的,是不被人理解的。
比如今天我们把孟德尔称为“遗传学之父”,他提出的定律奠定了遗传学这门学科的基础,但在1865年,他把这些定律公布出来的时候,根本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甚至有统计学家在重复实验时,觉得孟德尔的数据太完美了,怀疑他涉嫌伪造数据。
● 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
孟德尔在1884年就去世了,直到20世纪初,也就是孟德尔定律问世三四十年以后,主流的植物学家才力挺他的学术成果,让他在后世被公认为遗传学的奠基人。
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科学家,他们没能在最年富力强的年纪得到同行的认可,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因此而抱憾终生,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些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们没能在生前得到更多学术资源的倾斜,没能站在自己的原创性成果上更进一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突破。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起点上,我们知道,他们和他们的事业,都值得被更多人看见,都理应得到全社会更广泛的支持。因为人才是科技和产业变革过程中最关键的因素。
最近我读到了一本新书,名叫《问道前沿:科技如何构筑我们的未来》,它记录的正是这样一批杰出的科学新星突破前沿、不辍创新的故事。
这本书的作者是腾讯集团高级管理顾问、青腾教务长杨国安。作为顶级的商业管理专家,杨国安教授这一次将目光聚焦于生命科学、能源环境、数智科技这三个与普通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领域,用一年多的时间,访问在这些领域内进行前沿研究的科学家。书中以科学家的视角进行讲述,通过记录15名优秀青年科学家的故事,让读者在探寻未来的同时,也看到科学思考和行动的轨迹。
其中有两位科学家的故事格外有趣,充满了偶然与意外。他们分别是鲁伯埙和杨玉超。
鲁伯埙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他并不是医生,却在很多病人中间出了名,因为他要为一款“无药可救”的疾病寻找新药的研发路径。
●鲁伯埙,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科技部“863”青年科学家。
这类病就是神经退行性疾病,是大脑和脊髓的细胞神经元逐渐退化所直接导致的,其中最知名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
鲁伯埙研究的是另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叫“亨廷顿病”,它无法根治、无法延缓,也无从预防。随着病情加重,患者身体运动的不协调会越来越明显,直到运动变得困难,甚至无法说话,通常发病10~15年后就会死亡。
一般来说,对抗这类疾病的思路是找到小分子阻断剂来作用于致病蛋白,很难用这种方法对付亨廷顿病。
于是鲁伯埙想,能不能找到一种全新的策略来根治这种疾病?
2012年,他从一家跨国大型药企回国,开始从底层的基础研究出发,寻找新药的研发思路,终于锁定了一种叫做“ATTEC”的突破口,全称“自噬小体绑定化合物”。
我们的细胞在饥饿状态中,会降解自身材料,维持自己的存活。在“自噬”过程中,有一个细胞器叫“自噬小体”,它会包裹细胞中的一部分蛋白,把它们消化掉以后转换成细胞的营养物质和能量。
鲁伯埙希望能让自噬小体去定向清理亨廷顿病的致病蛋白,但现实是这种东西是个“一视同仁的杀手”,会把一整块地方的物质都吞噬掉。如果用来做药,那它的杀伤力和副作用就太大了。
他开始研究的时候,全球学术界对这个领域的报道几乎是空白,所以没有人告诉他,选这个方向来攻克亨廷顿病是不是对的。有可能研究了数年,连方向都选错了。
但他没有放弃,而是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给这个“自噬”过程加上一种“胶水”,把自噬小体和致病蛋白拉到一起,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定点拆除”?
他瞄准了自噬小体膜上的一种LC3蛋白,希望致病蛋白经过LC3的时候,“胶水”能像“粘知了”一样把致病蛋白黏住,然后让自噬小体吞噬它。
为了研发“胶水”,他查阅论文、参加自噬大会、跟药企同行讨论,还设计了一个化合物库,但是尝试了很多方法,都不成功,筛选化合物的速度也太慢了。
眼看试验走进了死胡同,到2015年,他偶然间听了一场“光科学”的讲座,一位专家分享了一种小分子芯片光学筛选系统,能够快速检测出不同化合物跟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于是鲁伯埙找到这位专家,对近4000种化合物进行筛选,到2016年找到了4种符合条件的小分子,既能与LC3蛋白结合,又能与变异了的亨廷顿蛋白相结合。
但是结合在一起了,就能降解、吞噬致病蛋白吗?
鲁伯埙带着他的团队反复验证,结果发现自噬并不显著,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发生。
鲁伯埙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路了。
有一天中午,他跟妻子在学校食堂吃饭,妻子也是生物学家,二人聊着聊着就说起妻子的项目。妻子吐槽说,她实验的时候发现有一种化合物明明符合要求,但是化合物浓度高了反而没用,只有降低浓度,才能把两个蛋白拉到一起。
鲁伯埙笑着说:“你是要靠这个化合物把两个东西拉到一起,浓度过高会导致它分别和这两个东西结合,反而拉不到一块儿去啊!”
就在那一瞬间,他自己也开了窍。
他马上把这个思路用在了自己的试验里,夜里11点,结果出现了:浓度降下来,致病蛋白被降解了——成了!
就这样,一种全新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诞生了。2019年10月,《自然》杂志刊登了鲁伯埙和合作者的研究成果,这也成为中国科学家掌握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项核心技术。
●《Nature(自然)》刊载的鲁伯埙及其合作者的研究论文
但这还不是鲁伯埙故事中最激动人心的地方。
生物学家对于他的这项研究反响非常热烈。有的研究者改造了他发现的化合物,用来降解癌症蛋白,从而把“自噬”纳入了抗癌药物的研发轨道。
而鲁伯埙的想法也大大拓宽:如果这东西可以降解亨廷顿病的致病蛋白,那么它能不能用来降解其他对人体有害的(非蛋白)物质?
比如,细胞中储存脂肪的——脂滴。
我们可不可以用自噬的方法来减脂,来治疗过度肥胖、脂肪肝、动脉粥样硬化呢?
鲁伯埙的实验证实了,这种方法可以为肥胖的小鼠来降血脂。
在做自噬研究的过程中,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模拟了人类神经元从发病到死亡的全过程。
原本这只是研究亨廷顿病过程中的一个实验而已,但却让他意外发现,一些已经进入死亡程序的神经元竟然“复活”了!所谓的“复活”,就是把神经元死亡的程序逆转了过来,像正常神经元一样执行功能。从此,鲁伯埙又锁定了一个新的、更具有挑战性的研究方向:他想搞清楚细胞到底能不能“复活”,“复活”的机制到底是什么。
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他的神经元死得很快,但如果我们能够“复活”神经元,对于很多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可能会产生极大帮助。
虽然鲁伯埙的研究还处在实验阶段,基础研究距离成药,还非常遥远,但他期待着未来相关研究成果能进入临床,帮助到更多病人,让这一系列“不治之症”成为历史。
类似这样精彩的科学家故事在《问道前沿》当中还有很多,比如北京大学长聘教授、人工智能研究院类脑智能芯片研究中心主任杨玉超。
●杨玉超,博士,北京大学研究员,国家杰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项目首席科学家。
杨玉超在读博阶段有过一段郁闷的时期,因为他的实验总是失败。
当时他在寻找性能更好的绝缘性材料,但是做出来的样品总是漏电,而且他还发现,施加电压以后,正向和反向的“电流-电压”曲线不一致、没有重合,也就是说,这个导体的电阻值不是固定的。
通过查阅文献,他发现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叫做“忆阻器”,于是他兴冲冲地去找导师,开始研究这个新方向。后来他的研究还刊登在了《自然-通讯》期刊上。
在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的过程中,杨玉超和同行们意外发现,忆阻器这个东西,跟人类大脑中神经元的突触特别像,突触是神经元之间进行信息传递和交换的重要部分。
于是学术界提出了:我们可以不可以用忆阻器,来搭建一个类似人脑的模型,实现“类脑计算”呢?
他和他的课题组利用忆阻器制作了一个优化器。一般的优化器在求解问题的时候,容易只找到局部的最优解,但是加入忆阻器以后,就像给计算机里加入了神经元,让计算体系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活跃地在全局寻找最优解,这一点和人脑很像。
现在,他正在攻克忆阻器从三阶到四阶复杂性的跨越。虽然忆阻器和类脑计算的研究还在路上,但他认为,忆阻器引领的类脑计算,未来可以同脑机接口相连。
● 科幻作品中对脑机接口的经典设想
脑机接口可以把人脑和机器相连,采集人类发出的神经元放电信号,如果脑机接口再跟类脑计算结合,类脑系统就能够“解密”——破解这些信号,得知这个人究竟在想什么,就像“读心术”一样。
这正是忆阻器未来发展一个诱人的前景——“双脑融合”。杨玉超预测就在5~10年后,这个领域会发生一场巨大的变革,机器智能将同生物智能有望“双剑合璧”。
类脑计算一旦获得突破,当年他在实验室里做出来的忆阻器——那种所谓的“失败样品”,将迸发出现如今并不存在的崭新应用,它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
这就是《问道前沿》书中的两个精彩故事,而类似这样的故事在书里还有十几个,让我们看到中国科学家们在生命科学、能源环境和数智科技方面的研究突破简直是异彩纷呈,让人大开眼界。
虽然科学研究总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与挑战,但是科学成果不是无迹可寻的,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苹果,而是科学家在抱着强烈好奇心和使命感在探索之路上孜孜以求,用前人的已知和未知去开辟自己的战场,再把自己的战果投入到新的探索中去,从而不断深化、开辟出全新的科学领域,推动整个人类科学的进步与发展。
这些人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去尊敬、去崇拜的明星,他们探索前沿的神奇与壮丽,理应被更多人看见。
早在5年前,本着“面向未来、奖励潜力、鼓励探索”的宗旨,杨振宁、饶毅、施一公、潘建伟等14位中国科学家与腾讯联手,发起公益奖项“科学探索奖”,迄今已资助248位优秀青年科学家。
“科学探索奖”是由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出资、科学家主导的一个公益奖项,它是目前国内金额最高的青年科技人才资助项目之一,支持在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全职工作、45周岁及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心无旁骛地探索科学“无人区”。每一位获奖人将得到连续5年共300万的奖金,完全由他们自由支配。他们拿这些钱来补贴生活,或者投入科研都可以,没有限制。
2022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突破2000亿元,较之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规模,“科学探索奖”这类民间奖项的定位在“补位”,发挥社会资金灵活的优势,摸索社会力量长期稳定资助基础科研的创新模式。获得这个奖项的科学家都是其领域中极具潜力的学者,他们所从事的基础科研工作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将拓展整个人类的知识边界,造福全球。
最近出版的《问道前沿》一书正是为记录这些“科学探索奖”获得者突破前沿路上的故事而作,它记录了15位优秀青年科学家的探索故事。在科学浩渺的夜空之上,这个由企业出资、科学家主导、基金会运营的公益奖项,将陪伴一颗又一颗璀璨的科学新星冉冉升起。
什么是问道,什么是前沿?就是像鲁伯埙和杨玉超一样,在科学未知的边界探索,把自己探索出来的成果当成新的“基础设施”,把自己作为方法,为国家、为全人类开拓知识的新边疆。
就像“科学探索奖”发起人之一施一公院士说的:
“‘科学探索奖’所关注的,就是青年科学家的工作是否在本领域代表世界最前沿,支持他们做其他人想做但做不出、不敢做,具有原创性和引领性的研究。”
总有人认为,科学家的研究,离我们很遥远。
但《问道前沿》里面的精彩故事让我们看到,科学家们探索前沿的成果,与普通人的未来息息相关。他们攻坚克难、探索不息的心路历程,更是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
就像《三体·黑暗森林》当中,当人类得知400年后三体舰队即将到达地球以后,全世界都陷入了恐慌,各国开始为400年后的末日之战做准备,大力投入太空备战,结果人类的生活水平显著下降,环境急剧恶化,粮食减产,储备粮也耗光了,生活水平倒退到19世纪,短短半个世纪,世界人口就从83亿降到了35亿。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想开了:我们为了末日战争的胜利,牺牲了这么多,到底值不值得?怀里快饿死的孩子,跟延续人类文明,哪个更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幡然醒悟:如果只是为了安然活到400年以后,泯灭了人类的文明,那么要这样的人类社会有何意义?
人类社会的光辉与不朽,不在于人类这个种族的永生,而在于人类文明的赓续与升华,在于人类永无止境地探索与进发。
刘慈欣借书中人之口,说了这样一句名言:“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文明不是未来某一天才会到来、才会成熟的结果,文明体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分、每一秒,体现在社会发展进程的点点滴滴当中。
或许“科学探索奖”最大的意义,也不在于这些青年科学家在前沿领域取得了多大的突破,而是在于他们让我们看到了,在人类科学的发展史上,永远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只想回归科研本身,秉持着最纯粹的探索精神,去追求科研的真善美,无比笃定地去尝试、去钻研、去攻克。
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
因为科学探索的意义,就展现在探索科学的每一分、每一秒当中。
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END-
撰稿:书单君
编辑:右一
图片来源:电视剧《三体》《我的三体:岁月成碑》
《黑客帝国》、Nature、Unsplash、科学探索奖官方
关键词
蛋白
自噬小体
科学
化合物
亨廷顿病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