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丨育儿中的数字化劳动:隐形的夫妻分工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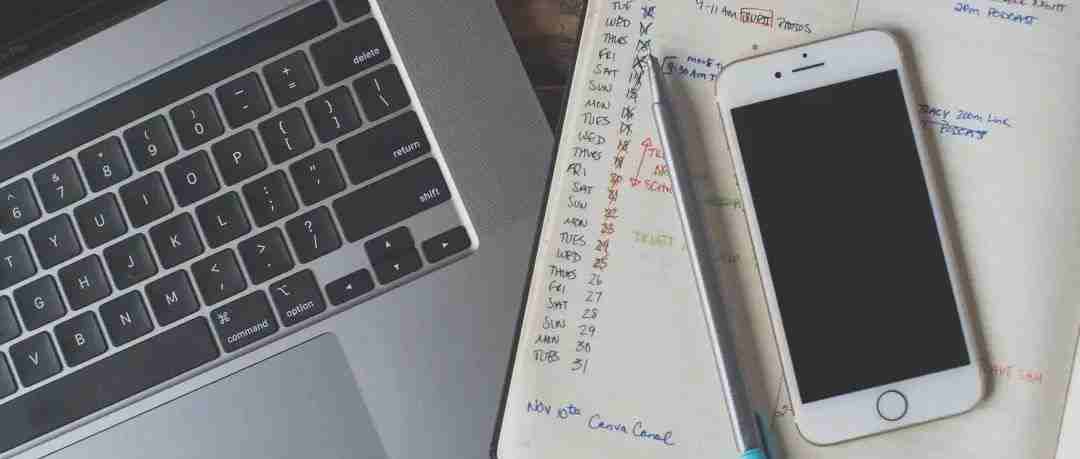
▲来源:www.pexels.com
撰文:
马欢(澳大利亚凯斯林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博士生)
杨嘉文(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高级研究助理)
责编:彭铟旎(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导读:数字科技和媒体为父母们的育儿带来了积极的转变还是隐形的负担和不平等?
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的育儿正体现出照料精细化和资源密集化的趋势。与此同时,随着数字科技和社交媒体对家庭的不断渗透,中国城市家庭的育儿也呈现出数字化的特点:网购、线上教育和在线家校沟通成为城市父母育儿的日常活动。如何理解这一转变对育儿中夫妻分工的影响呢?
彭铟旎博士发表在最新一期Sex Roles上的文章《育儿中的数字化劳动和性别分工:聚焦中国城市家庭的定性研究》探讨了这一问题。彭博士引入了“育儿中的数字化劳动”这一概念来描述这些通过数字科技和社交媒体所进行的育儿活动。她指出,育儿中的数字化劳动包含大量隐性的、非物质化的劳动,涉及信息、知识、沟通、协调、规划与统筹等多方面,要求父母具备数字化相关知识和能力来满足孩子的需求。这些数字化劳动与父母在育儿中的体力和情感劳动互相交织,消耗父母的时间、体力和脑力,并且呈现出隐密性、碎片化和繁琐性等特点。
那么,谁在育儿中承担了这些繁琐隐形的数字化劳动呢?彭博士在2019-2020期间,于深圳、厦门及泰安先后开展多次调研,对来自84个城市家庭的147位父母进行了深度访谈。这些父母大多数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年龄介于26岁到49岁之间。
通过比较80位母亲和67位父亲在育儿中对数字科技和社交媒体的使用,彭博士发现,在大多数家庭中,母亲是该数字化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她从育儿信息检索、在线家校联系、网购与线上教育三个维度探究了育儿中数字化劳动的性别分工机制。
▲来源:www.pexels.com
1
育儿信息检索:妈妈的“兴趣”?
城市父母崇尚科学育儿,互联网成为了妈妈们获取孕育知识的主要渠道。彭博士发现,大部分家庭中都是妈妈在关注育儿信息。研究中,有76位妈妈定期追踪微博、微信上的育儿公众号,加入线上“妈妈群”,使用百度、知乎和小红书获取与育儿相关的各种资讯:小到如何给孩子做辅食和挑选玩具,大到儿童心理健康、亲子沟通以及如何选择孩子的课外兴趣班。妈妈们关注这些信息是为了吸收有用的育儿知识,以促进孩子的健康发展。然而,搜索育儿信息并不是简单的检索,妈妈们需要从庞大的育儿资讯中,甄别来源可靠且适用于自身情况的信息,以优化自己的育儿实践。
相反,爸爸们在育儿信息检索上表现消极。除6位爸爸比较主动外,大多数爸爸很少关注育儿信息。爸爸们普遍认为关注育儿信息是一种性别化的“兴趣”:妈妈们的“母性本能”使得她们对网上的育儿资讯更感兴趣,而忙于工作的爸爸们对小红书等“女性化”平台兴致寥寥。妈妈们体谅丈夫工作辛苦,不仅“自觉地”搜索育儿信息,还乐于与丈夫分享自己的搜索成果,致使爸爸们依赖妻子去获取育儿资讯。
搜索育儿信息这项看似轻而易举进行的工作——划一划手机、点一点鼠标——实则耗时耗力,隐藏了妈妈们在此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关注力和信息分析能力。而她们的劳动和付出也未被认可,甚至有些爸爸认为,妈妈被商业化的育儿博客“洗脑”,从事的是无意义的活动。
▲来源:www.pexels.com
2
在线家校联系:忙碌的妈妈和“潜水”的爸爸
线上家校群已经成为父母与老师沟通的基地。彭博士发现,有53个家庭的线上家校沟通由妈妈负责。妈妈们不仅要关注和及时回复家校群中大量的信息,定期汇报孩子的情况,还要协助孩子按时在线提交作业和完成各种打卡。
疫情期间,妈妈们的这种数字化劳动因为孩子上网课而变得更加繁重。不少妈妈一边在线办公,一边实时关注家校群中的消息,一边还要督促孩子的线上学习。不仅如此,妈妈们在家校联系中力求维持良好的家长形象以增进老师对孩子的关注,因此她们必须深谙网络沟通的规则,注意语言表达技巧,时刻保持得体与礼貌。
然而,大部分爸爸选择在家校群中常年“潜水”。很多爸爸妈妈会用“妈妈与老师都是女性,方便沟通”来解释这种分工。在工作领域,幼师和教师多由女性担任。在家庭分工中,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擅长”照顾和沟通工作,而男性工作忙又没耐心。这种公私领域的性别机制导致由妈妈承担家校联系工作看似更为恰当。其次,老师也会优先选择和妈妈沟通,老师与家长的这种互动模式为爸爸的逃避提供了借口。还有一些爸爸以自己工作忙和不善言辞为由,回避与老师的线上沟通。
少数爸爸即便自己参与得少,但对妈妈高标准严要求,希望妈妈能时刻关注家校群并及时回复老师的信息。而当为数不多的爸爸在家校联系中表现积极时,妈妈则会给予感激和肯定。
▲来源:www.pexels.com
3
网购与线上教育:妈妈的主场
随着电子商业的发展,父母们一方面依赖便利的网购为孩子挑选零食、文具和衣服,另一方面也给孩子选择各种线上兴趣班和辅导班,为孩子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
别小瞧网购:摸不到的实物、差距大的买家秀和卖家秀、真假难辨的货源……每逢“双十一”,各种复杂的折扣和优惠券使得网购成为一门难懂的学问。在彭博士的研究中,由妈妈主导网购的家庭有54个,爸爸主导网购的家庭仅有2个,另有6个家庭爸爸妈妈共同承担这一线上劳动。
在网购中,主导者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筛选成百上千的产品,并综合考虑家庭经济能力和需求,最后做出购物决定。然而,妈妈们通过网购满足孩子各种需求的劳动常常被视为“剁手党”的乐趣,变成了一种有性别色彩的技能,或者一种母爱本能的体现。兴趣与特长,成了将网购加之于妈妈们的理由。爸爸们偶尔在网上给孩子买礼物,来表达他们对孩子的拳拳父爱。
给孩子选择线上兴趣班和辅导班也带来了类似的数字化劳动,包括筛选合适的课程、报名、安装APP、注册、与客服联系等细碎繁琐的工作。彭博士发现,在52个使用线上教育资源的家庭中,51个家庭以妈妈为主导。妈妈们不仅需要陪伴孩子上网课,帮助他们和老师交流,还需监督孩子保持注意力。低龄孩子的妈妈,更要时刻准备着辅助他们使用复杂的APP。爸爸们很少参与,他们大多知道孩子正在使用线上教育服务,却很少能说出细节。“能者多劳”成为爸爸们偷懒的理由。线上教育不是一项单独的工作,需要信息检索和家校沟通的能力,妈妈在前两项工作中的优良表现,使得其顺势承担起与线上教育相关的劳动。
▲来源:www.pexels.com
4
数字化时代的性别与科技
彭博士从性别与科技互相建构的角度分析了育儿中数字化劳动性别分工不平等的成因。性别意识、性别关系和性别机制塑造科技的发展与应用,与此同时,科技变革会体现、强化、或者挑战既有的性别关系和机制。
在育儿的数字化劳动中,性别从三个维度影响科技使用。
- 首先,性别本质主义使得这种不平等的分工看似自然而然:女性更加细心、耐心、善长沟通与照顾他人;男性缺乏耐心、粗心且不善言辞。由于父母内化了这种对于男女的刻板认知,他们惯于用“生而不同”理解彼此在数字化劳动中的角色和分工。
- 其次,公共与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和制度对育儿中数字化劳动的分工产生影响。教育职业的性别偏好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导致老师与照顾者往往同为女性。同性沟通的恰当性成为由母亲负责家校沟通的理由。
- 第三,父母的日常育儿活动、夫妻间的互动和家校间的交流,例如夫妻间育儿知识的分享、对配偶劳动的不同评价和老师优先选择与妈妈沟通等,维系了育儿中数字化劳动分工的不平等并将其合理化。
科技同时也影响性别关系的建构。数字化劳动的特性改变了父母育儿活动的呈现方式。
- 首先,人们普遍认为,科技令育儿变得简单便捷,实则带来了繁重而隐密的数字化劳动。母亲在育儿中付出的数字化劳动看似轻松,而掩藏其中的难度和琐碎却常常被忽视。
- 第二,数码技术的多功能性模糊了育儿工作和娱乐之间的边界,因此当母亲通过手机、电脑进行育儿劳动时,她们常被误认为是在娱乐。
- 第三,数字化劳动多是散布在其它日常活动中,很多母亲见缝插针地利用工作和生活中的碎片化时间完成各项线上育儿任务。数字劳动的隐密性、边界模糊性、繁琐性和碎片性,使得母亲繁重的育儿工作被低估,也让父亲在育儿的数字化劳动中的缺失显得顺理成章。
通过对育儿中的数字科技持续性地差异化使用,中国城市父母们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新的性别分工不平等。
因此数字化技术和媒体的运用并没有将女性从繁重的育儿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带来了一种新的育儿责任,并且强化了育儿分工的性别不对等。然而,彭博士也发现,少数父亲在数字化劳动中承担了更多的工作,例如主动承担家校联系工作和给孩子海淘奶粉,从而佐证了母亲的付出并非本该如此以及科技与性别的互相建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研究发现不仅为家庭育儿中的性别分工提供了新的方向,亦展现了在数字化时代挑战父权制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Peng, Yinni. (2022). Gendered division of digital labor in parenting: A qualitative study in urban China. Sex Roles, 86 (5-6), 283–304. https://doi.org/10.1007/s11199-021-01267-w.
制版编辑:杨楠
- 更多相关文章 -
权威、严谨、客观
我们带你体验不一样的
情感婚姻生活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