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珠夜未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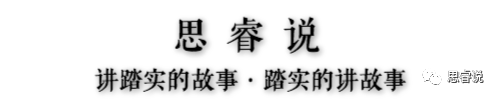
我来的时候是迫不及待的,蹦蹦跳跳的来,我走的时候也是迫不及待的,蹦蹦跳跳的离开。
春分
在18年的冬至签下了香港的relocate offer,一个月之内办好了签证,一张单程机票伴随着四个托运箱,一转眼我就到了香港,在19年的春分之前。下榻酒店的那一晚,还依然觉得这一切仿佛梦一场。

25岁的我带着所有的幻想,满心期待给自己设限的两年会发生什么以及是否会如我所愿。世界就是很神奇吧,所有的好朋友一转眼间全部都来了深圳,哪怕是我到香港的第一周,也有要从新加坡去深圳工作的朋友在转机的间隙,陪我在公司的公寓住了两天。
刚来时,正好APEC gathering,原team 在亚洲的同事一个不少的都出现在了香港。那一周充满了酒肉八卦。在我老板的rooftop开party,可以从下午6点一直到午夜,是我在美国的team从未经历过的爽朗,于是感慨于同事之间的游离刚好的关系。
那晚我很安静,拿着一瓶气泡水站在阳台的一角看夜景,2月底的港风多少还有些凉意,但湿度不减,从发梢拂过几千几万次,头发一定会黏黏糊糊。12层楼下晚上9点的港岛西区,依然车水马龙,我看着楼下逐渐安静,对面酒店的灯光慢慢亮起,身后是同事们偶尔的欢呼和被调大音量的音乐,眼前是对未来两年的无尽畅享。
那晚结束凌晨两点,我和两位喝的晕乎乎的男同事一起回到公司附近。Rob仍然清醒,倒是另外一位从澳大利亚来的同事拿着酒瓶边走边喝,非要拉着我们两个去蹦迪。我走在他们身后,像旁观者一样观察着眼前的一切,心里对自己说,香港生活,就这样不知不觉的拉开序幕,无论好坏,要让自己保持着随时抽身的能力。
夏至
第一次经历回南天的东北人全靠抽湿机吊着,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是倒掉抽湿机机箱里那满满登登一箱水。可是在美国南方过了四年的我,其实已经习惯了南方的天气,温暖,或湿润或干燥,但总之会经常拥有太阳,天寒地冻都再与我无关,我可以在衣柜里放心的买一排短袖和裙子。
四月初的那一晚,天色轻烟细雨中,水色氤氲梦相融。原来深夜10点半以后的置地广场前也人员寥寥,除了加班的中环民工,还有在楼下风雨无阻等中环民工下班的出租车司机。而那天穿的浅棕色小皮裙和四月的濛濛细雨呼应的完美无缺,却也第一次在细雨中知道了四月青梅的酸甜背后的原因。
转眼间,我的新书发布。没有时间顾忌其他,那年三月中到四月中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都在和出版社敲定最后的封面设计,前两场重要签售的嘉宾名单和座位列表,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的宣传,和供销商敲定周边产品的最终设计和产量。

感受了一个月香港的凌晨三点,静谧,润物细无声,湿润,充满希望,但我并无法从中感到心安。一如它或许只是每个人生命中的一站一样,人来人走,千帆万过。
后来,两天北京上海跑了3场签售,回到香港时,整个人到家直接瘫倒在床上,从早睡到下午。但总之,无论我最初香港的目的是什么,在给自己预期的两年时间里对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很圆满的完成了,所以接下来的几个月的周末,都奔波于深港之间,不停的签售,不停的演讲,回了一趟纽约和旧金山,在这本书开始的地方做了几次活动,一切都像是一场梦。

夏至之前,人生中第一次晕倒,第一次上了救护车。当我在铜锣湾维密门口90度垂直倒下时,我没有任何知觉,直到路人们把我托起,没有人让我以脸抢地耳,我才忽然意识到自己过去几分钟的无意识。紧接着来和我汇合吃饭的小伙伴就拨通了救护车的电话,几分钟后随着一阵长鸣,救护车层层突围,冲开铜锣湾密密麻麻的人群,扎向了我。我被护士们麻利的抬上了车。医护人员一遍帮我冰敷崴到的脚踝,一边说这大概是刺激到了神经,要去医院看看。
我对医院有莫名的恐惧,婉拒后本想回家休息,却从出租车下车时觉察到脚踝骨的肿胀和撕裂,随即找了路边的跌打损伤,老师傅一摸我的脚踝直接说需要正骨,吓得我哇哇大哭,直喊着要去医院。
于是,人生中第一次挂了急诊。拍了片子,放心了一大半,被室友搀着回了家,之后陆陆续续针灸了一个月,现在左脚踝走路时间长的时候还是会有所察觉,竟没想到,在香港体验人生新际遇。
秋分
从大学开始保留了一个习惯,每年生日前会尽量找地方给自己慢递一封信。26岁生日前,我深知25岁的三个愿望终究要落空一个,但还是给自己写了一封信,投递日期是生日前两天。收到时竟然还有些许惊讶,迫不及待打开,自己却被逗笑,怎么会这么傻,傻到快要丢失了自己。
所以,生日前那趟东京之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不只是去东京见纽约的好友,更感谢的是她一针见血的,不留任何情面的指出了我那段时间生活状态的问题。感谢我仍然有这样的朋友,可以随时把我点醒,不需要有任何顾忌。而这趟旅行也为现在的生活埋下了一段伏笔。
虽然注重仪式感,但我很少大张旗鼓的给自己庆祝生日(比如超过2个人),我喜欢在一个私密的环境里和亲近的人慢慢享受着一切,说着对方或许可以理解又或许不能的故事。来到香港后,出于一些原因,我办了暖房趴,办了生日趴。因为不熟悉香港的烘焙面粉和自己刚买的烤箱,为了烤出湿度、甜度最合适的蛋糕,甚至提前练习了两次。落空了一次,半落空了一次,算是满意,也算失望。
但依然记得那时在已经不太太平的香港,老赵下班从深圳急忙赶来,帮我摆盘,帮我把所有的菜肴都变成最好看的样子。记得瑞瑞在阳台帮我挂上星星灯,记得晚饭后我们喝着我从日本买来的抹茶酒,徐老师坐在我家她最喜欢的抱枕上慢慢说着她和香港的故事和即将离开的种种复杂情绪。那是一种杂糅,兴奋,不安,期待,不舍,还有对青春的几分留恋。
我大概永远无法体会港漂七年以上的感觉,但让我一直在这里生活,我是不愿意的。层层高楼之下是无尽的压力,生活,工作,交友,金钱。海港城的奢侈品店在光景好的时候永远门庭若市,你也永远无法想象半山的富人区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富豪。你也永远不知道要赚多少钱,才可以在这座房子贵、生活贵的城市里体面的或者按自己最想要的方式活着。
七月起每周需要小心翼翼出行的香港在逐渐丧失它的活力,内部和外部的因素正在逐渐把它撕裂,还可以回到过去吗?或许可以接近,但一场疫情的到来,让一切全部归为零。于是化内销为动力,海港城和时代广场争先恐后的发着优惠券,即使如此,每次出门前还是要仔细看一下香港01的行程预告,偶尔收到一些提示短信,于是取消所有计划,乖乖在家躺尸。收起所有的某一颜色的衣服,恨不得把自己穿的花里胡哨的出街,早上8点出门,中午12点回家,错峰出行更有安全感。
好一个秋天,还没有来得及体验香港的山山水水,就这样噼里啪啦咋咋呼呼的结束了。
冬至
在香港最喜欢喝的咖啡店在公司附近。它小小的甚至容纳不下5个人,三个人就会显得挤挤插插。还记得第一次走进店里的那天,是香港的初冬,原本只想在进公司前清醒一下,却口误要了燕麦拿铁。然而那一杯入口的那一刻,是这两年在香港唯一温暖过我的瞬间。

杯子简单的设计,轻盈的奶泡不紧不慢的铺洒在表面,燕麦奶打泡后没有争夺咖啡豆子的醇香,入口香醇,意犹未尽,像是一股暖如潺潺流水般淌进了心里。
咖啡师告诉我他们每三个月就换一次豆子。他还说他们原本有三家店,倒闭了一家,就剩下了上环和尖沙咀。我怕我失去这口味道,便从那以后见到同事就安利这家店。
它陪我过度过了很多焦虑的时刻,拿不到lead,挖不出信息,被采访对象一次一次兜圈子。可但凡我踏进那个小屋子,这些心理上的焦躁就慢慢被消逝了。哪怕我只是坐在小巧的吧台上,看咖啡师认真的拉花,又或者我背对着他一个人对着墙发呆。那里仅有的恬静、舒适、不争不抢不浮躁让我迷恋。
后来,请了半个月的假,独自去了台北,伦敦,曼彻斯特,谢菲尔德,爱丁堡,在巴黎和学妹汇合。然后我们去了佛罗伦萨,罗马,梵蒂冈,塞维利亚,巴塞罗那,最后一站落回了伦敦。
那大概是我这两年最开心的时间,在台北一个人消磨时间,一边逛一边吃,日行三万步,竟然还可以在台北和高中同学重聚,然后他骑着他的小摩托,带着我在深夜的台北兜风,像导游一般的报地名。
在伦敦和好朋友四处乱逛,喝了好喝的咖啡,聊了很多故事和八卦,在我出去独自吃晚饭的一晚回来后聊了这一年的所有心路瞬间,是彻底的放下当时的执念。她担心我的情绪,却想不到我意外的洒脱,有的时候说再见比想象中的容易很多。
去曼彻斯特是真的因为看到大家都在推荐一个柬埔寨女巫,那段时间迷恋算命的我决定去试试,于是一股脑的买了车票,拖上我的粉色小箱子,满心期待的踏上行程。不得不说,是准的,或者90%是准的,疫情好些后,我还得再去一趟,这次是为了还愿。
谢菲尔德吃了两顿很棒的brunch,和小伙伴聊了近况和她听到的一些八卦,于是所有人都给了我同样的答案,向前看,别回头。
爱丁堡的日落让人心安,在白夜最短,黑夜最长的那一天,我去看了一个人的日出和日落。日出十分,人还稀少,于是看着天边慢慢泛起鱼肚白,陪着城市慢慢苏醒,听着山坡下的卡车开始逐渐欢腾,是另一种浪漫。而日落时分,有很多情侣,只不过大部分都在打卡周杰伦MV的场景,同款拍照。

我不会想到2019年看的最美的日落是在佛罗伦萨和巴塞罗那。佛罗伦萨的日落是温和的,伴着意式音乐的浪漫与柔情,一切旅途中的疲惫都会被揉进那晚的粉红色里。离开之前又刚好遇见两个3岁左右的小孩子在追着吹出来的大泡泡,一手一个想要去戳破它,童年的梦幻美好,在正在转黑,还有些许粉色,和转色交融时产生的深蓝色天空中显得格外触人心弦。
而巴塞的日落是欢腾的。是一群年轻人,爬上山坡,嚼着薯片,喝着啤酒,摊着吉他,跳着舞,等待日落的到来。他们准备好三脚架和相机,找好最佳拍摄地点,自拍,大笑。当天色逐渐变暗,太阳慢慢落下,在地平线以上露出粉红色的浪漫,他们亲吻,拥抱。青春不过如此,身后是欢快的吉他弹奏和荷尔蒙的气息,眼前是粉红色一片映满人间,旁边是好友相伴,最幸福的瞬间也不过如此。

塞维利亚是过去这两年的一个高峰时刻,那一株墙角的植物见证的一幕幕如果它有一天成精了希望它可以写成剧本拍成剧。我不后悔我来过,但我现在要离开。西班牙广场的黄昏,路边的木偶戏,抵达后的第一口橘子酒还有走之前吃的最后一颗橄榄,都尘封起来,未来再见,和爱的人。
春去秋来又一年
2020年初的疫情像往太平洋里丢了一颗炸弹,危机四伏。在大年三十晚上踏上飞往旧金山的航班时我又怎么会想到未来一年有一半的时间会在美国度过。
一年的工作已经足以让人失去最初的热情,越走越窄的空间再往里走很可能就会窒息而亡。黑云压城城欲摧。从哥大新闻毕业的那天起,就做好了未来的五年规划,只是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继续读书。阴差阳错,去年就自然的发生了。所以人生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计划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遇见什么人,然后你的一生或者一段时间都将会被改变,彻头彻尾的改变。
每一次从美国回来落地后总会觉得焦虑扑面而来,可怕的是你不知道它的源头究竟是什么。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狭窄的职业发展道路,还是羡慕已经转行成功的小伙伴,是除非跳槽否则涨幅遥遥无期的工资,还是香港楼市即使有所下沉但依旧动辄千万的三十平米小房间,是高楼耸立下给人的压迫感,滞留于香港产生的厌倦。
西环码头见证了我2020年的所有焦虑,每当工作到几乎快崩溃的时候,我就会去码头看日落,看着太阳逐渐落下,隐入海底,给海面上留下一片平静的金黄,远处的渔船慢慢悠悠的驶向离岛,这个时候才会觉得香港还是些许闲适的。但一旦打开电脑就会回到现实。

低迷的市场,不足料的deal,挖不出的信息,完不成的稿件,一件一件加起来会越发质疑自己:为什么要做新闻?曾经为了拿到一个独家,险些害的一位刚刚毕业的投行工作者丢了工作,幸好他最后是换了组,赶上去年在香港IPO的火爆,损失和收获直接hedge相抵。
当我接到banker的电话焦虑的来问,如果deal 最后fail了,谁来承担责任时,我也说不出一二三。周一和公司的compliance开会,做好所有公司被起诉的准备时,我不禁想问到底是谁错了?他和我都没有错,他告诉我他知道的信息,我把他告诉我的信息一字不差的以最快的速度发给特定的群组。资本市场也没有错,大家依靠信息赚钱。
离开新闻行业,不算偶然也非必然。Live deal下追scoop的巨大压力,没有匹配的pay,,一眼可以望到头的上升空间和时常质疑自己到底产生了什么价值,真正学到的东西又有多少可以leverage到下一个阶段。所有市场Hiring freeze,离开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最优解,无论你愿不愿意。
回顾香港的两年,没有很好,但也不算太差。结交了一群在外媒工作的伙伴,还有一些纽约的老友Relocate过来,拥有几个探店的好伙伴,虽然大家最后不约而同的都选择离开。
有一些瞬间,我很想安定下来,但也只是希望出去玩时可以放心的买回喜欢的纪念品,给他们安个家,不用因为担心搬家的不易而不得已放下喜欢的物件,只在脑海里留了个念想。
曾在一次伦敦飞回香港的飞机上勾勒出了自己想要的家的模样。
客厅将有一个很宽的淡绿色布艺沙发,撞色的抱枕一排。沙发上面将有三幅我自己画的装饰画,很可能是抽象派的渐变色或者彩色泼墨系。90度靠墙的沙发另一侧可以竖着躺下的那面墙上将有一副很大的手绘世界地图,上面扎满图针,是我走过的地方。茶几的样子还没有想好,但上面一定有一个自己做的琉璃花瓶,夕阳的时候阳光照射下来最好看了。沙发旁边要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外面是一个阳台或者天台,可以放得下一个木制摇椅或者蛋形吊椅,让我可以盘着腿写稿子、看书或者睡觉。
客厅要有一颗圣诞树,上面挂满了我每年许下的一个愿望和从全世界带回来的圣诞挂饰,圣诞树的顶端要有一个星星。
我创作的地方需要一张很简易的桌子,白色,不能是木质的,木质的东西会限制我的灵感。会有一个大屏苹果电脑,和可以按下去的老式键盘,windows的键盘会让我灵感迸发。椅子一定要舒服,既可以盘着腿也可以向后靠着拖着我的小脑袋。桌面上方会有一块板,要方便贴便利贴,我喜欢把灵感都写在便利贴上。旁边会是一排四层开放式黑色木质书架,我不喜欢书柜,隔着玻璃会让我产生距离感。其中的一层会有一个很好看的宝箱和几个复古盒子里面藏着我这些年的日记、信件、明信片还有planner。
我要一个很大的开放式厨房,厨房要有很多内嵌式壁柜,里面装满了我喜欢的碗碟杯子,瓶瓶罐罐,各种锅和烘培工具。还要有一个两层的内嵌烤箱,最好是在灶台下面。灶台要用电的,我不喜欢明火。冰箱要很大,因为我很喜欢囤食材,冰箱上贴满了我从世界带回来的冰箱贴。灶台正面的墙上有一面玻璃装饰,玻璃内层是各式各样带着各国特色的杯子垫,装饰起来应该很好看,做饭的心情都会变好。
要有一台很好的咖啡机,因为越来越喜欢手冲,周末的早上给自己做一杯咖啡是一件太幸福的事。
灶台另一面是一个吧台。上面有两盏不算太亮的吊灯,旁边还会有一个落地灯,供我来调节灯光。吧台侧面是一个具有设计感的木制酒柜挂在墙上。
吧台后面是一个伸缩式餐桌,配色没有想好,但一定不是宫廷风。厨房的色调应该是暖黄色或白色大理石,这样拍出来的菜品照片很好看。餐桌上面要放一个我做的陶艺花瓶,花瓶上会画一些对我比较重要的图案。
卧室的配色暂时没想好。大概会是比较明亮的颜色,可能是很淡的柔和绿,但要有一个至少一米宽的飘窗,可以让我很舒服的靠着墙壁观察楼下的路人。
卧室的角落会躺着一只一米五的大熊,我难过的时候可以靠着它或者抱着它,我会给他买一个纯色的地毯,但绝对不会是白色。
谁也不知道未来安定下来的地方和这份畅想之间到底差了什么,但有个念想总归是好的,至少它是我26岁时曾经最希望的家的模样。
那我喜欢香港吗?
这趟不到850天的行程即将画上句号。几天前朋友问我以后会不会想念香港。我不知道。就像我当初从纽约走的时候多么大义凛然的说,纽约,我终于走了!可还是在2019年6月回去的那一趟败给了公寓楼下Doorman的那句Welcome Back,紧接着有关纽约的所有记忆就如泄洪般汹涌而至,再也逃不出我的脑海,我也跑不出纽约在我身上留下的烙印。

我不知道香港给我的生命里注入的到底是什么,或许3年5年10年后当再回想25-27岁这两年的光景时,才会恍然大悟。
我终究还是要离开了这里,奔赴天使之城。
但Origin的燕麦咖啡、GC的可颂、新兴食家的流沙包、Louise的烤鸡、九记的牛腩、生计的皮蛋瘦肉粥、Mamaday的鳗鱼饭、鲜入围煮的花胶鸡、坤记的煲仔饭、方荣记的沙爹火锅….上环的猫、西环的日落、嘉顿山的黄昏、女人街的夜、尖沙咀的大排档,凌晨的兰桂坊,还有皇后大道东最后一号的水果摊男老板给老板娘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的歌声都封存在了记忆里。
一月阴冷,二月湿润,三月春风,四月绵绵,五月洋溢,六月叶茂,七月蝉鸣,八月炙热,九月台风,十月落叶,十一月气爽,十二月干燥。
东方之珠夜未眠,希望未来它可以清醒的愈合,也希望下一次回来时,我们都焕发着新的生机与希望。
再见。
有缘,再见。


--- E N D ---
往期文章:
思睿说:25岁,更自由
思睿说:半山腰太挤了,你得去山顶看看
思睿说:什么是真正的勇敢?
思睿说•Threeshow


前财经记者,正在转行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很开心遇见你,不如交个朋友
微博@邵思睿_Daisy,微信threeshow33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