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走失后,他们再无正常生活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很早之前我就听说过李静芝的寻子故事,也曾经在一些寻子电视节目里看到她的演说。在每个节目里,她满脸“苦相”,眉头总是蹙着,一遍又一遍地讲自己寻找孩子的伤心往事,两三分钟后,情绪开始失控,在镜头前哭了起来。
幸运的是,去年母亲节,李静芝终于找回了儿子嘉嘉。半年过去后,重新做这个选题,
一方面是想知道,走失了32年的儿子的归来,给母亲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更重要的是想关注李静芝背后的“寻子联盟”,那些已经花了二三十年时间寻子的父母们,如何奔波在路上。

儿子回来后,李静芝不再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里。但她从来不拒绝媒体的采访邀请,不是为了自己能露脸说点什么,而是想给其他寻子的父母们创造曝光的机会。起初,我请李静芝引见几位寻子联盟里的父母,她过了半天给我发来消息,“八九户家长会从各个县市赶来,一起在家里见,我在群里说了一句,结果大家都想来。”
我和摄影师在约好的时间到达时,屋里已经坐了十几位家长。眼前这些家长大多来自农村,讲蹩脚的普通话,表达能力并不强。他们那么像曾经的李静芝,蹙着眉头,脸上写满了悲伤,聊着聊着就会哽咽起来。
他们的孩子全都丢失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距今有二三十年了。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一方面,宗法社会的影响依然强大,执着地“想要一个男孩”成为一些家庭的执念。事实上,大多数家庭丢失的孩子,都是两岁到五岁的男孩。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经验,比如,找孩子必然是要到各个农村去,越偏远、越不发达的农村,找到的希望越大。
另一方面,有孩子的家长养育孩子时,也还遵循着熟人社会的传统,甚至放心让孩子独自上幼儿园,算得上散养,这在人口爆发式流动的年代,为拐卖活动提供了条件。
没有手机、没有监控、没有实名制,照片都稀罕,人贩子带着孩子隐身,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个孩子丢失了,就像一滴水,汇入了茫茫大海中。

父母们执着于找回自己的孩子,买家们也执着于“藏孩子”,似乎双方都在为“有一个孩子”拉锯着。和李静芝一样,许多家长在寻子中,都有过在陌生的村庄里被联合起来的村民欺骗的经历。在那些村民的心里,没有孩子的人家花钱买来孩子“延续香火”,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们很容易达成某种心照不宣的约定,共同守护这个秘密、这桩买卖。
受制于年代的技术手段,在寻子路上,丢孩子的家长们,所能使用的资料往往都是古早的,孩子两三岁时的照片和特征、走失的地方、“能说爸爸妈妈的名字”等等。我脑海里无数次冒出,“这能找到吗?”但我不忍心说出来。
和正文里写到的贾正博一样,许多父母都是在自己的“一时疏忽”中丢了孩子,我十分容易地感到了他们的自责。一位姓赵的妈妈在1992年独自带着两岁的儿子到北京玩,返程时在北京西站遇到了搭讪的陌生女人,她喝了对方买的饮料后沉沉睡去,醒来后儿子早已不见了。因为记得对方是个漂亮的四川女人,29年里,她抛下丈夫和其他几个孩子,独自到四川边打工边找人,过着最低质量的生活。我问她,你一个人怎么找人呀?她拿出一张红底的寻人启事说,“我拿着这个到处问。”
这是客厅里最漫无目的的一个妈妈,随意地挑选打工的城市。四川那么大,她甚至不像其他父母一样,打听附近的村庄是否有人家曾经买过孩子。“这样怎么能找到啊?”这是我唯一一次不小心说出口。她的眼眶里很快充满了眼泪,开始抽泣,只是反复嘟囔,“我的错,我得找,我得找。”

夜深人静时,这个疑问他们一定思考了无数遍,他们也一定知道,靠新技术是最有效的方法。我后来意识到,为什么有了DNA采集技术后,许多父母还是主动放弃了正常的生活,搭上自己的半生,用一种低效的寻子方式时刻奔波路上。
驱使他们的不仅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也是父母们需要的一种赎罪感。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自责,通过让自己吃苦,惩罚自己犯下的滔天大错,能让他们心里好受点。如果他们过着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也许会加重自己的负担和痛苦,“我弄丢了孩子,怎么还能像没事人一样呢?”我也才理解了李静芝为何在客厅里苦口婆心地劝同伴们,一定一定要好好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这是一场可能持续终身的拉锯战,不仅是寻子父母与买方之间的争夺,也是他们与自己的抗衡。只有在寻回孩子时,两场对峙才会结束,父母才能与自己和解。
在外人看来,每个家长的故事似乎大同小异,粗心的家长弄丢了孩子,从此开始深一脚浅一脚地寻找,期间吃尽了苦头。
我很想帮助眼前每一位压抑、绝望、痛苦、挣扎的父母,把每个人的故事都详细写出来,给他们附上一张寻子照片。但心里又知道,其实我也无能为力。

寻子的父母们聚在李静芝家里,他们总是随身带着寻子启事(缓山 摄)
这很现实,又很残酷,外人眼中所谓的“大同小异”故事,落在眼前每一个家长的身上,都是掏空了他们三十年心血、折磨了一家人三十年的具体悲剧。当我坐到他们面前时,会迅速地被这种痛苦感染,当我远离他们时,他们又成了群体中面目模糊的个体。有的家长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会尽量待在离李静芝更近的地方,在摄影师给李静芝拍摄个人照片时,悄悄地在一旁打开自己的寻子启示,或是在李静芝招呼家长门拍合照时,假装不经意地抬起手中的寻子卡片。
在李静芝的劝说下,每个家长都做了DNA采样,期待着有一天能匹配上孩子。
李静芝有一个想法,国家应该给所有适龄青年采集DNA,与寻子父母们比对。“做流调能这么详细,采集DNA就是一滴血,也可以的。”我没法回应这个提议,除非自愿,否则人们并没有义务把个人生物信息上交,这是一个庞大的个人信息库,谁来保护它不被泄露?
对寻子的家长们而言,这也许是一个救命稻草,但在没有契机的情况下,受到法律和道德的限制,这并不是一个具有现实性的想法。我只能拿着手机和摄影师一起,尽量地多给这些父母拍照,给他们的寻子启事拍几张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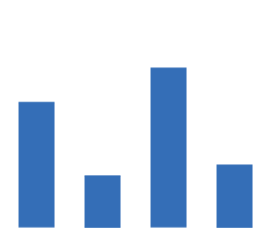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吴淑斌
微信编辑:小风
监制:L.L.
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转载请联系后台。


点击图片,一键拥有它!
▼ 点击阅读原文,一键下单本期新刊「 默克尔 」。
阅读原文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