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读了30本书,推荐这5本

过去两年,每年都刚好读了51本书。今年读得少了,快年终了,只读了30本书。

之所以读的少了,一来因为工作太忙,不仅平日里完全没有时间阅读,即使是双休日的时间也会被挤占。二来是对读书数量的目标,也没有那么执著了,阅读的计划安排,都更随性。此外,今年还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阅读之外的事情上,比如读佛经、学佛学课程等等。
今年读过的30本书里,有五本值得重点推荐。
1.《大河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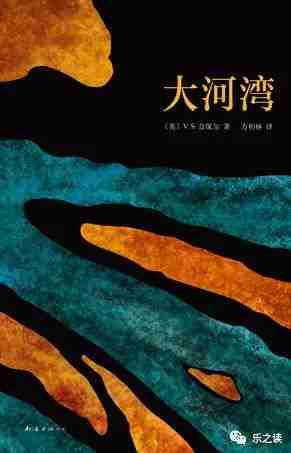
V·S·奈保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今年八月逝世。
纪念作家最好的方式之一,是读他的作品,并尽可能地理解他。
《大河湾》的知名度,远远比不上它在文坛的地位。它被媒体评价为“最后一部现代主义的伟大史诗”。奥巴马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书评》的采访时,在谈到自己读过的虚构作品里,重点提到了《大河湾》。
和一般的小说不同,《大河湾》的精彩之处,不在于情节。这本书就像一条大河一样,从始至终静静地流淌着,无论是情节的冲突、转折,情绪的压抑、释放,都是克制的。
《大河湾》的主基调,是流浪。书中的主角萨林姆,是奈保尔内心的映射,他一直在流浪,一直在找自己的家,也一直无法找到自己的家。
往更深了看,奈保尔在寻找的,是内心带来充实和满足的归属感,是对抗虚无主义的出路,是支撑着生存的渴望的本质答案。奈保尔在流浪中寻找着答案,生存的终极意义,到底是什么。是获得感官上的满足吗?是获取丰富的人生阅历吗?是迎合生而为人的宿命感吗?
都不是。奈保尔没有找到答案。旅行让奈保尔获得了一定的慰藉和平静,但答案,并不在旅行中。
奈保尔的意识浸淫在世俗中,一边追求物质和中庸,一边力求在生活和超脱之间找到平衡。问题是,在没有哲学和宗教的前提下,这样的平衡是缺乏支点的。这种尝试的代价,是平衡的随时崩塌,是不安全感,是周而复始的挫折和迷茫。
《大河湾》里的萨林姆没有找到答案,生活中的奈保尔同样没有找到答案。
但至少,他从未放弃过寻找。
2.《围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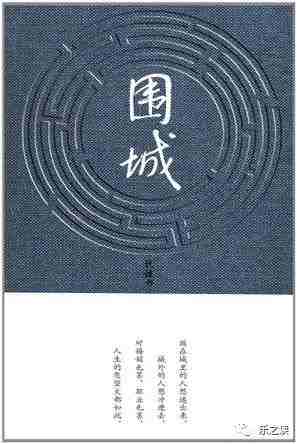
钱锺书先生大才,学富五车,精通多种语言,过目不忘,遍览经史子集,集中国古典文化之大成。 余英时先生曾评价说,钱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最后一个风雅之士,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
钱先生一生致力于学问,以文学研究为主,著有《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篇》等。除学术著作外,钱先生另著散文若干,小说最为稀有,仅《围城》一本。
看似仅此一本,实则韵味无穷。峰峦叠嶂,寓意深远,道尽了人生百态,苦乐滋味,刻骨铭心。
《围城》是一本讽刺之书。书里几乎所有人都戴着面具,所有人都在伪装。无论是主角方鸿渐、苏文纨、孙柔嘉,还是配角曹元朗、李梅亭、汪处厚……钱先生用精妙戏谑的幽默笔刀,把他们的伪装一件件地撕下。
与其它角色庸俗的虚伪相比,方鸿渐显得另类些,他既虚伪,又虚伪得不够彻底。他是我们芸芸众生中常见的那类人,既有些良知,厌恶虚伪,又不得不和现实妥协,虚伪作态;既受不了虚伪的人环绕周围,又缺乏和虚伪决裂的能力和勇气,只能一直在压抑、愤懑、纠结和不甘之中苟且地活着。
在所有人物中,只有唐晓芙是异类。她是《围城》里暗无天日的虚伪阴霾中唯一的光亮,让我们相信,无论世间有多少人是那么的功利、虚荣、猥琐、肮脏,也仍然会有一些人,坚守着真实和纯粹——就如同永远埋头于书堆中,不问世事,不求功名的钱先生本人一样。
《围城》的第一层解读,是婚姻,“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第二层解读,是人生。无论婚姻、事业、生活,得不到时,心心念念;得到之后,意兴阑珊。
第三层解读,是众生。多少人执假为真,虚荣媚俗地活着;多少人带着面具,虚情假意地活着;多少人在厌恶虚伪和不得不虚伪中挣扎彷徨地活着;多少人又能像唐晓芙一样,真实而纯粹地活着。
“一切伪装的假情假意都是思索的产物,但是不能继续持久而不露破绽。”
3.《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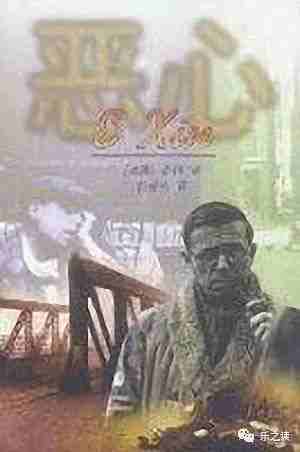
20世纪有三位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萨特和加缪。海德格尔是存在主义的先驱,萨特和加缪是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加缪的《局外人》长期在畅销书榜占有一席之地,《鼠疫》的知名度也不低,相比之下,萨特的代表作《恶心》的传播度要差的多,在各大图书网站上都难觅其踪。
《恶心》是一本小说,同时也是一本哲学图解。如果说加缪的《局外人》是他的哲学著作《西西弗神话》的图解,那么萨特的《恶心》也可以说是他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的图解。
恶心是什么?当世界在某一天突然在眼里变化了模样,世界的有序和必然性突然失去,只剩下以偶然性为基调的荒谬,一切原本看上去理所应当的事物,突然都变得不可理喻——这种变化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感,就是恶心。
这种感觉,在《黑客帝国》中出现过。尼奥选择了回到真实世界的红药丸,于是他看到了机械世界,喝到了包裹自己的营养液,摸到了自己脑后的插管。他吐了,恶心地吐了。
萨特说荒谬,加缪说荒诞,这两个大概是同一个词。只是加缪所说的荒诞,是指“非理性和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非理性是不断再生、无限的;而萨特所说的荒谬,根植于偶然性——
“一切存在物都是毫无道理地出生,因软弱而延续,因偶然而死亡”;“偶然性不是伪装,不是可以排除的表象,它是绝对,因此就是完美的无动机。一切都无动机,这个公园,这座城市,我自己。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你感到恶心。”
如果存在是偶然,那存在必然无意义。随机事件是无法产生本质层面的意义的,骰子里只有听天由命,没有自由意志。
意识到“存在无意义”的萨特,愤怒得喘不过气来。他无法想象这一切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存在一个世界,而不是虚无。这毫无道理。
在《恶心》这本书里,萨特只抛出了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这本书是萨特早期的著作,他有一些头绪,但并不坚定。萨特在他后期的作品——《存在与虚无》、《自由之路》里,逐渐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如果觉得以上这种恶心的感觉不可理喻,很正常。只要不思考存在的意义、真实和虚假这类哲学问题,我们永远不会感受到这种恶心。
但这是一种幸福吗?不是。无知不是幸福。无知只是假装幸福。
4.《了不起的盖茨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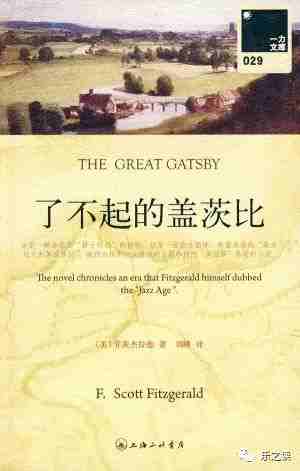
《了不起的盖茨比》在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榜上高居第二位,能在文学巨著层出不穷的这一百年里跻身如此高的地位,这本书必然有其独到之处。
从表面上看,这本书描写了“美国梦”,纸醉金迷的时代,焦虑迷茫的人们。盖茨比是追逐美国梦的脆弱而虚妄的代表,黛西和汤姆坐拥金钱和资本的冷漠而无情的代表。
往深里读,这本书所蕴藏的意象,要深刻而丰富得多。
一方面,《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所展示的价值观是跨越时代的——把追求物质的成功装点成“财富自由”,把追求世俗的名利美化成“在我实现”,把拜金理想化,把物欲合理化——在缺乏信仰的大多数时代,这样的“X国梦”,都是时代的基调。
另一方面,盖茨比和黛西的形象,是具有普世意义的——盖茨比代表的是人性里永不枯竭、永远在膨胀的欲望;黛西是盖茨比欲望的对境,是幻梦的图腾。
“幻梦”,是藏在“美国梦”里的更深一层的意象。幻梦里有物质,有精神,有光鲜的爱侣,有完美的自我,有“宏大的、世俗的、华而不实的美”,是承载着所有欲望的地方。幻梦的诡谲之处在于,当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得到所求之物时,预期中的狂喜稍纵即逝,紧接着产生的,是不真实的虚幻感和求得之后的失落感。
求不得时,魂牵梦绕;求得之后,怅然若失,不得不做起新的梦,来填补人性里的欲望空虚时发出的渴求。盖茨比、黛西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求不得和求得的无尽循环中,永远沉浮在苦海里。
盖茨比所代表的无限膨胀的欲望,和黛西所代表的无常的幻梦,构成了世间的苦。人世间的痛苦,大多来自于无限的欲望增长和有限的满足欲望的能力之间的矛盾;也来自于对幻梦的执着追求和世界的无常本质之间的矛盾。
深挖人世间痛苦的本质,在我看来,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最值得细细品味的部分。
5.《变色龙》

这是一本契诃夫的中短篇经典小说合集。
如果从字面上去读,契诃夫是一个标准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以犀利、幽默、智慧的笔触,剖析着社会的畸形和冷漠、人性的虚伪和迷茫;但在笔者看来,契诃夫的文字,并不囿于现实主义的表象,而是深入到了存在主义层面的本质。
书里的主打篇《变色龙》、《套中人》等等,耳熟能详,不提。反倒是几篇不常被评论所提及的,比如《第六病室》、《醋栗》等,值得推荐。
《第六病室》对于意义的灵魂拷问,直击存在主义的内核:“为什么要有视力,话语,自我感觉,天才呢?所有这些岂不都是注定了要埋进土里,最后跟地壳一起冷却,然后随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几百万年,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吗?”
如果事物终将消亡,如果人人都有一死,在这些短暂的存在里,意义何在?目的何在?
《第六病室》里没有给出答案。在小说的结尾处,契诃夫写到:“安德烈·叶菲梅奇因中风而死。起初他感到猛烈的寒颤和恶心,仿佛有一种使人恶心的东西浸透他的全身,甚至钻进了手指头,由胃里涌到头部,淹没了眼睛和耳朵。”
这种恶心的感觉,看上去像是小说主角对命运不公的控诉,实则是契诃夫对存在主义的思考所触及到的荒谬感的反射。
可以说,这种感觉,和萨特在《恶心》里所描述的感觉,是大同小异的。
本文对此观点,暂不深究。之后会写长书评另作详述。

往期文章:
阅读原文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