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盖茨比》:“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菲茨杰拉德是村上春树最爱的三位作家之一,《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他的代表作,在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榜上高居第二位。能在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卡佛、冯古内特、托马斯·曼、伍尔夫等等一众20世纪文学大师的经典传世作品中脱颖而出,这本书的含金量可想而知。甚至可以说,这本书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大大高于菲茨杰拉德本人在作家排行榜中的地位。
一般来说,长篇作品更有可能成为传世经典,比如排名榜单第一位的《尤利西斯》,是一百多万字的皇皇巨著。而《了不起的盖茨比》,仅仅只有十几万字(中译本)。这样的篇幅在同级别的文学经典中,是十分罕见的。
为什么《了不起的盖茨比》会有这么高的文学地位?
1
大部分评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文章,都会提到这本书的时代背景——二十世纪初美国的爵士时代,沉迷在追求物质享受中的迷茫的一代。这个时代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关键词——“美国梦”。
评论者们认为,菲茨杰拉德生动地描写了这个时代的纸醉金迷和美国年轻一代的物质、焦虑和迷茫,通过盖茨比展示了“美国梦”的脆弱和虚幻,通过黛西和汤姆展示了资本的冷漠和无情。
在笔者看来,这些评论就像在做中学语文课的阅读理解一样,着眼处过于微观,理解上浅尝辄止,对于经典作品的伟大,只能随大流地鼓鼓掌,很难感同身受。
菲茨杰拉德确实是把“美国梦”描写地最准确、最深入的作家,但仅仅是“美国梦”,是不可能撑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经典地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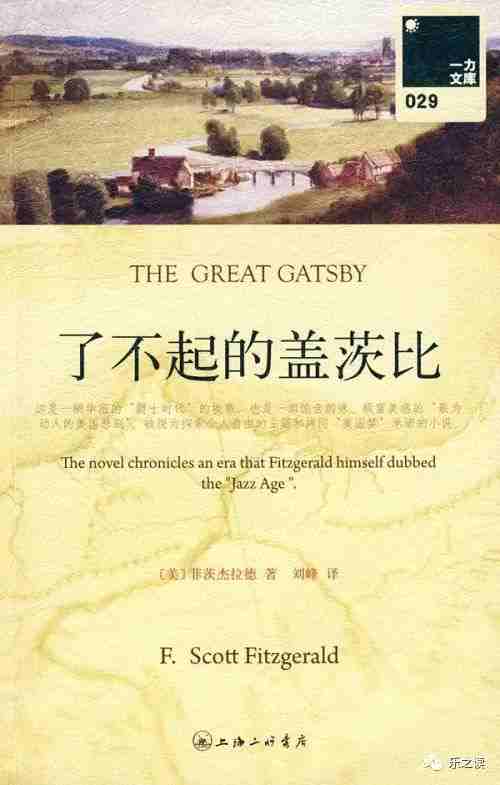
能被称为经典的文学作品,至少会有两层意象。
一层是现实性的。情节的主体——爱恨情仇、矛盾冲突;节奏的设计——起承转合、大起大落;人物的勾勒——动作、心理、选择;故事场景的设置——历史背景、时代特征……这些都是读者对作品的直观感受。
另一层是哲学性的。为什么会有爱恨情仇,为什么会有矛盾冲突?它们是因人而异的还是普适的?它们是时代的特定产物还是跨越时代的?它们的发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它们的背后都有些什么意义?
被人们奉为“伟大”的作品,往往都有着丰富的哲学性意象。这些作品大多更关心“本质”层面的问题,比如理性和道德的边界、真实和虚幻的区别、存在和虚无、人生的意义,等等。
关心这些问题,并非文学家们刻意地阳春白雪、无病呻吟,而是当我们以理性和审慎的态度对世俗的问题进行层层盘剥式的解刨时,必然会殊途同归地来到这些本质问题的高墙之下。
2
当我们穿越文学作品的现实性意象,探究其哲学性层面的意义时,会发现经典作品们的哲学意义是永恒不变的,它们跨越时代、跨越地域、跨越种族,凌驾于现实的差异之上。
比如《包法利夫人》,表面上的背景是法国七月革命和第二帝国,但我们在阅读时不能把包法利夫人的悲剧简单归结为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的腐朽,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包法利夫人执拗与幻想的欲望、认知的局限、信仰的羸弱、叛逆的本能、永不知足的心态,是跨越时代的人性。
比如《双城记》,表面上写的是法国大革命“以自由之名”的血腥暴力,但我们不能狭隘地认为自由的罪恶之花仅仅绽放在那个时代,“屠龙少年以正义之名战胜恶龙,然后自己成为新的恶龙”的故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屡屡发生,是不尊重程序正义、将“自由”简单化的革命的习惯性悲剧,是历史规律冷冰冰的轮回。
其它诸如《暗店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百年孤独》等等,这些作品的时代和社会背景,都能帮助读者们更快地进入作品的虚构世界并理解其中人物行为的动机,但更有价值的,是观察并思考其是否具有跨时代的普适意义。
回到《了不起的盖茨比》上来,什么是“美国梦”?认为物质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个人的奋斗是成功的主要原因,只要努力赚钱就是成功的人生赢家的想法,就是“美国梦”。
“美国梦”是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独有的价值观吗?显然不是。在缺乏主流信仰的大多数时代,“X国梦”都是时代的基调。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者前言中提到:“美国梦的第一个体现者和鼓吹者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编纂的《穷理查年鉴》就是第一个在美国文化史上全面地宣传了个人奋斗、发家致富的扬基精神。”
有趣的是,《穷理查年鉴》,也就是《穷理查宝典》,是当今畅销书排行榜的常客,自媒体上泛滥的教人如何上进、如何理财的文章,都喜欢推荐这本书。
我们这个时代,把追求物质的成功装点成“财富自由”,把追求世俗的名利美化成“自我实现”,把物欲合理化,让拜金套上皇帝的新装来遮羞。
如果盖茨比生活在今天,将成为商界明星、全民偶像,人们会狂热地追捧他的财富奇迹,迷妹们将集合在他长岛豪宅门口日夜守候,同时还有一群自媒体为他洗白——《盖茨比:山寨并不是假货》、《盖多多的世界里,藏着最真实的美国》、《盖多多为什么崛起?这是迄今为止解读最深刻的一篇》、《盖茨比向左,比尔盖茨向右》……
所谓的“美国梦”,和如今的“中国梦”相比,如果真要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我们今天拜金拜得更纯粹,更猛烈,也更彻底。
3
当我们在阅读时,把故事的悲剧归咎于时代和社会背景,其实是一种傲慢。这种傲慢源自于事不关己的看客心态,和“五十步笑百步”的自命不凡。
比如很多人对包法利夫人嗤之以鼻,认为她愚昧、庸俗、贪心,可自己在生活中汲汲钻营的势利目标,和包法利夫人全无两样;有人觉得《双城记》里参与法国大革命的民众冲动、狂热、缺乏理性,可自己平时却喜欢关注伪爱国主义公众号,在无脑的民族主义鸡血里意淫高潮。
同样的,在阅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时,有人会幸灾乐祸,认为盖茨比的经历是浮华奢靡的必然结果;有人会义愤填膺,认为黛西和汤姆是资本主义阶级的腐朽代表。而同样的这群人,放下书本,回到生活中时,又会以所谓的梦想之名拼命努力,希望自己能拥有像盖茨比、黛西和汤姆一样富足和糜烂的物质享受。

经典的传世之作们是一面面照妖镜,照出我们自身的短视、矛盾和无知,照出人生的虚无本质,照出人性深处的龌龊和阴暗。
可惜大多数人错把照妖镜当成了显示屏,以为那些只是别人的不幸,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幸运不落窠臼。
这也是我为什么很少在书评里分析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原因,当阅读的注意力过多地聚焦于此时,我们会自然地将书本里的世界和身处的现实世界对立起来,而失去代入和反思的机会。
如果我们在阅读时足够谦卑,足够敏锐,就不难发现——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法国大革命的参与者,就是我;《暗店街》里的失忆者,就是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的托马斯和特丽莎,就是我;《黄金时代》里的王二和陈清扬,就是我;《围城》里的方鸿渐,就是我……
《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盖茨比、黛西和汤姆们,又何尝不是“我”呢?
4
从盖茨比身上,我们能看到太多自己的影子。
他在自我介绍时会小心谨慎地遣词造句;他在和人对话时会尽量显得善解人意;他西装笔挺,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鞋子一尘不染——他总是希望把完美的状态展现在别人面前。
除了最后摊牌时的失控外,盖茨比唯一的一次失态,是在尼克的小屋等待和黛西见面的时候。被雨淋湿的头发、不知该往哪儿放的双手、语无伦次的对白。他局促、紧张(莱昂纳多在电影里把这个感觉表达得淋漓尽致),甚至想要逃离:
“这是个愚蠢的错误”,他把头摇来摇去地说,“大错特错。”
紧张的背后,是他对黛西的在意:
“我们多年不见了。”黛西说,语气尽可能地平和。“到11月就整整五年了。”
盖茨比不假思索的回答至少让我们大家又楞了一分钟。

从始至终,我们都能看出黛西在盖茨比心中的地位,也能看出,黛西对盖茨比来说,并不仅仅是爱情的对象。
盖茨比对黛西的欲望是不断增长的。最开始,“他很可能只打算玩玩而已”,然后,“他发现他已经把自己投身于追求一种理想”,再然后,他吻上了她,她像鲜花一样绽放,“一个理想的化身就完成了”。
这个理想从表象来看,是穷小子通过努力逆袭赢取白富美的理想,是跨越阶级鸿沟跻身上流社会的理想;从本质来看,是人性里永不枯竭、永远在膨胀的欲望。
黛西是盖茨比欲望的对境,是理想的象征,是幻梦的图腾。
5
《了不起对盖茨比》真正的关键词,不是“美国梦”,而是“幻梦”。
幻梦里有物质,有精神,有光鲜的爱侣,有完美的自我,有“宏大的、世俗的、华而不实的美”,是承载着所有欲望的地方。
黛西只是幻梦中的一部分。盖茨比自己也知道:
“黛西远不如她梦想中的那么好——这倒不是她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他的幻想过于精彩,这种幻想已经超越了她本身,超越了一切东西。”

在长岛西半岛上每周举办盛大party的盖茨比,并不只是想吸引黛西的注意力,这些豪宅和聚会所塑造的盖茨比的形象,是他为自己营造的柏拉图式理念的派生物。这个派生物并非美国梦的产物,而是在所有时代都存在的,沉浸在痴念和贪欲的幻梦中的每个人,所共同凝望和追求的对象。
幻梦的诡谲之处在于,当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得到所求之物时,预期中的狂喜稍纵即逝,紧接着产生的,是不真实的虚幻感和求得之后的失落感。
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绿灯”的意象。绿灯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一共出现三次。第二次出现是在盖茨比和黛西在尼克家见面后——
“盖茨比突然想到那盏灯对他的巨大意义已经永远消失了。与他跟黛西分开的要远距离相比较,那盏灯曾经离她那么近,近得几乎可以碰到她,就好像星星和月亮那样近在咫尺。而现在它又变回了码头上的一盏绿灯。他为之神魂颠倒的宝物又减少了一样。”
求不得时,魂牵梦绕;求得之后,怅然若失,不得不做起新的梦,来填补人性里的欲望空虚时发出的渴求。“他的内心一直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盖茨比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求不得和求得的无尽循环中,永远沉浮在轮回的苦海里。
6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微型《红楼梦》——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总有人会想,如果盖茨比没有对黛西那么痴情,或是黛西和汤姆没有那么自私麻木,是否故事会转向美好的结局?这就好比是研究红楼的人们会想,如果贾府把那些做错了的事纠正过来,是否就可以千秋万代地矗立不倒?
并不可能。无论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是《红楼梦》,所要表达的都不是对特定人物或时代的惋惜和批判,而是面向整个人生的究竟的悲哀,这种悲哀源自于人力所无法改变的世界的本质特征——无常。
没有什么是恒常不变的。花易逝,情易尽,人易老。中国古代诗词里,描写无常的佳句俯拾皆是——
梅尧臣的“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王国维的“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耽离别。”周邦彦的“恨春去、不与人期。弄夜色、空余满地梨花雪。”苏轼的“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
生死无常,得失无常,聚散无常。世事无常。
无常在佛教里,是核心理论——四法印之一,“诸行无常”,一切和合事物皆无常。
道家也讲无常。“易传”里强调,宇宙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处处透露着对无常的叹息:
“夜色依旧美好,花园依旧灯光璀璨,而欢声笑语都已经逝去。一股突如其来的空虚似乎正从每一扇窗户、每一扇门里倾泻出来。”“我既在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对人生的变幻无穷和五彩斑斓,既感到陶醉又感到厌恶。”
盖茨比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对抗无常。他总是制定一些这样那样的决心或处事原则,试图在有迹可循的规则里驱逐无常。他固执地让黛西承认她从没有爱过汤姆,他想把被无常带偏的人生轨迹的一切都恢复原样。可是他得到的回应,却是黛西的怒吼:“你的要求太过分了!”
我们都不喜欢无常。我们只喜欢无常的一部分——那些按照我们心意变化的,能受我们主观控制的那一部分。可是,无常并不在意我们的喜好,它就在那里,冷冷地辐射着万物。
7
“汤姆和黛西,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人——他们砸碎了东西,把别人给毁了,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金钱或者麻木不仁、漫不经心当中。”
汤姆和黛西通过麻木和自私,确实为自己建立起些许防御的屏障,但他们也并未因此离苦得乐。
对汤姆来说,他再也找不回橄榄球比赛里扣人心弦的激动与刺激,出轨、酗酒、挥霍,都无法回到他曾经感受的快乐巅峰,他所能做的,只有失落地缅怀过去,惆怅地将就生活。
黛西在出场秀是这样的——“她忧郁而漂亮的脸庞上荡漾着明媚的神采。”
黛西是忧郁的。她缺乏安全感,因此对汤姆极其依赖——“如果他离开房间一会儿,她就会心神不宁地四下张望”。她与白色为伴,白色的衣服、白色的小汽车,以及生活里的大片空白。她连言语中都充满了金钱的味道。
作为全书主视角的尼克,说过一句有点突兀的话:“我三十岁了。新的十年在我面前展现,那是一条布满荆棘、凶多吉少的人生道路。”

书里并未描写尼克任何的不幸。所谓的“布满荆棘、凶多吉少”,是尼克在旁观了盖茨比、汤姆和黛西的生活之后,对苦的感同身受。
众生皆苦。
苦,来自于无限的欲望增长和有限的满足欲望的能力之间的矛盾,也来自于对幻梦的执着追求和世界的无常本质之间的矛盾。
8
《了不起的盖茨比》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全书的最后一句。
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于是,我们努力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被浪潮推回到过去。”
这句话除了英文韵律的优美外,单看起来并没有特别的力量。但当和上文结合起来读时,所构筑的反差令人心悸——
“盖茨比相信那盏绿灯,相信那个年复一年渐行渐远的令人沉醉的未来。它以前从我们身边溜走了,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将会跑得更快,胳膊也伸得更远……总会有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
是的,努力地积极乐观,努力得跑得更快,努力得把手伸得更远,结果却发现,小舟不进反退,我们和那个令人沉醉的未来,渐行渐远。

为什么会这样?励志鸡汤不是总告诉我们,努力就能获得成功吗?
努力本身并没有错,努力的对境错了。小舟所试图划向的目标,是幻梦;小舟所环绕着的浪潮,是无常。
“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
这句话在书里是对盖茨比说的。可实际上,我们这些沉浸在对幻梦的执着里,天真地试图改变无常的人们,同样可怜。
何去何从?
接受无常,思维痛苦,放下我执,脱离幻梦。
这一切的前提,是认清我们所追求的与贪嗔痴有关的世俗目标,都只是幻梦。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阅读原文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