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一点,你才能大获全胜│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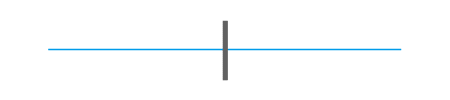

商品经济确保了在必需品的负担面前,物质主义之轻的胜利。
如今我们正处于高科技电子数码革命引领下的轻时代,我们的日常生活被“轻”重塑,轻已经成了“一股世界性的动力,一种颠覆全球的范式”。
——————
这是一个“轻”大获全胜的时代。
法国哲学家吉勒·利波维茨基在著作《轻文明》中,为我们再现了如今被“轻”所掌控的现代社会。“轻和速度一样,都被一种夸张的力量左右着,那些最日常的物品在追逐超轻、超精细和超小巧。我们以前幻想的是飞毯,却等来了电子芯片。从诗意的轻进入了‘智慧’、微型、联网的轻。”
与轻相比,“重”曾一度唤起敬意、庄严、财富。“曾经的‘轻’令人想到粗劣和廉价。在过去,轻是一种风格理念或一种道德瑕疵。”

曾经的“轻”令人想到粗劣和廉价。
“然而我们眼前的世界已非如此。我们正经历着物质世界的一场巨大变革。”在这个物质世界中,技术与市场更倾向于“轻”的逻辑而非“重”的逻辑。这种变化同时也是一场符号上的变革,曾长期受到贬低和轻视的“轻”,如今承载了正面的价值,成了“一股世界性的动力,一种颠覆全球的范式”。
“轻”的影响力表现在各种领域:时尚、设计、装潢、建筑。这种影响力也投射于肉体,对轻盈与“线条”的热爱爆发了。在空中,盘旋着滑翔伞和三角式滑翔机;在海浪间、滑雪赛道和柏油路上,可以见到一个个醉心于滑翔类运动的轻盈的身体。而时至今日,有谁不希望永葆青春和苗条呢?饮食类书籍迅速传播,各种“轻食”出现在每一家超市的货架上,吸脂手术成为普罗大众的选择,健身馆遍地开花,超模们个个一副得了厌食症的模样,平滑、纤细的身材占据了杂志和荧屏。在这种“厌恶脂肪”的文化里,时尚偶像凯特·摩斯说了一句名言:“没有什么比瘦更好的了。”

英国超模凯特·摩斯:“没有什么比瘦更好的了。”
吉勒·利波维茨基认为,商品经济确保了在必需品的负担面前,物质主义之轻的胜利。“到上世纪70年代末,超过3/4的工人家庭拥有汽车、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正是从那时起,轻的原则开始在细节和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家务的机械化促进了大众旅游,因为它令更多的人走出日常生活,走向大千世界。”
如果把轻对重的抗争比作一场现代战争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由技术政治的意志主导,意在减轻基本物质需求的束缚,为生活减负的进程已经开始,但仍受到社会的局限;第二阶段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标志为物质福利的社会传播、大众消费主义,以及对社会教条的抗争、针对集团框架的束缚的个人解放;如今我们正处于高科技电子数码革命引领下的第三阶段,它在创造一种摆脱了时空重负的机动的轻。

到上世纪70年代末,超过3/4的工人家庭拥有汽车、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正是从那时起,轻的原则开始在细节和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
但是,眼下的“轻”同样也在滋养着“重”的精神,因为轻的理念带来了一些强迫的规则,它们往往使人疲惫,有时甚至使人消沉。我们的世界已经诞生许多对快乐的欲求,这些欲求注定无法被满足。因此,当娱乐文化和超轻的物质设施占据上风,生活的轻盈之感反而消减。一种新的“沉重精神”侵入了这个时代。
“真正的‘轻’呼唤勤奋、守纪和承受痛苦的勇气;它在于用严格的要求来自我约束,‘戴着镣铐起舞’。正是在对抗世界的躁动和狂热中,我们才能真正变‘轻’。”利波维茨基说。
“轻”到极致便是“重”
——————
《新周刊》:你在2015年出版了《轻文明》一书。“轻”已经成为一种文明了吗?
利波维茨基:这本书的法语书名,直译应该是“关于轻的”。引申一下的话,也可以译作“以轻的名义”。最终翻译成“轻文明”,效果真是出乎意料的好,它切合了我长期以来对“轻”的观察和思考:这是一种崇拜、一种趋势、一种文明。不是吗?我们如今的一切都在变得简单、轻盈且便捷,但内心更多时候被不安、迷茫甚至脆弱所占据。

移动互联网正在使一切变轻。图/新浪
《新周刊》:你是如何理解“轻”的?
利波维茨基: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的一句诗令我印象深刻:“应该像鸟儿那样轻盈,而不是像羽毛。”
我认为,对于轻,应该像黑格尔提出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那样,用哲学思想辩证地看待。轻是什么?诗意的说法,轻是无忧无虑地漂浮在云上;通俗的说法,轻是“小的更好”“少即是多”。我敢断言,轻会成为一种覆盖全球的模式。
《新周刊》: “轻”已经遇上属于它自己的黄金时代了?
利波维茨基:不管怎么说,“少”与“轻”的乌托邦时代已经到来。好生活如今和“轻”密不可分:从移动支付、云科技到轻饮食、娱乐至死,“轻”在对“重”的战争中大获全胜。

中国的移动支付市场规模是美国的90倍,移动支付甚至被称为是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之一。图/智通财经
《新周刊》:你在书里提到了北京的雾霾,很多人好奇雾霾怎么也能和“轻”扯上关系。
利波维茨基:在我们这个时代,技术产品之“轻”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但随之出现了工业发展之“重”,空气污染正在加剧影响大城市人口的健康。
轻的革命正在各产业间发生,但由此付出的材料危害、环境污染以及社会代价正在变重。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生产如此多垃圾,重金属元素被无休止地以“变轻”的名义投入水中,工业废物、肥料也要变轻,于是它们都进入土壤里。我们希望某方面变“轻”,造成的后果却是另一方面变“重”。
《新周刊》:如今是移动互联网时代,“读屏时代”似乎已经取代了“读书时代”。你如何理解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轻”?你认可这种“轻”吗?
利波维茨基:远程办公、视频会议、网上冲浪,这些早已是生活的主旋律。中国就在移动支付方面遥遥领先嘛。如今已经不存在任何一个没有被电子系统改造的活动产业,这是我在书里谈到的观点。
这些当然都是轻的表现。至于认不认可,我想跑题问一下,在“读屏时代”,文章、视频内容好坏的标准如何界定?

移动互联网时代,“读屏时代”似乎已经取代了“读书时代”。
《新周刊》:中国的一些社交软件在点击量、转发量等数据方面的权重较大。
利波维茨基:这种考量方法其实全世界都存在。我想说的是,当轻过度膨胀,它便会扼杀生活中其他重要的维度,比如思考,比如创造,再比如伦理责任或政治责任。一旦“轻”过度,我们可能会失去某种厚重感。
这是一个“轻”大获全胜的时代。统治我们的,是一种由大众传媒传播的日常的轻文化,这种文化煽动人们利用那些直接、简易的愉悦。诱惑代替强制,享乐主义代替严苛的义务,幽默代替庄严。
但我觉得,只有在对抗现代世界的躁动与狂热中,我们才能变得轻。如果只是沉湎于轻佻的快感,我们必然无法变轻,必然无法走向轻文明。
《新周刊》:你提出的“轻文明”是否也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在变轻吗?
利波维茨基:没错。法国社会学家让·克劳德-考夫曼就提出“轻同居”的概念,婚姻前的同居生活让人感到自由,人的心情和状态也自然变轻了。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由过去的“强硬式教育”过渡为“放纵式教育”,孩子的自由空间在扩大,这是教育方面的“轻”。“世界上如今大约有1.4万个机场,几乎每秒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每年大约会有2920万次航班。所有人都渴望流动,计划着悠闲假期。”这是我在《轻文明》中提到的,流动性也是轻文明的一个切面。

澳大利亚一位12岁的男生,在与父母争吵过后,独自一人踏上了去巴厘岛的旅途。
《新周刊》: 《轻文明》出版时,法国社会正笼罩在恐怖袭击的阴影下。这本谈“轻”的书,为什么会诞生在这么沉重的背景下?
利波维茨基:有时通过分析一些截然相反的意象,会得出一些出乎意料的结论。让法国社会恐慌,在巴黎、尼斯这些城市制造恐怖袭击的那些人,都是极端组织的极端分子。首先我得明确一点,所有人都谴责这种不人道的行为,我们必须抵制这种行为。
从另一个方面看,我想说一个自己的论断:这些人都是被“轻社会”抛弃的人群,是在互联网和轻文明背景下,被扭曲了的、信奉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群。
“轻文明的轻,由科技、市场、个人主义支撑”,这是我在《轻文明》里的一个观点。此前在著作《超现实时代》(Les Temps Hypermodernes)中,我发表过另一个观点:“当下个体历史正在受到集体历史的强烈影响,但集体所认同的参考点极不稳定。原因就在于,个人产生的价值意义比以前重要得多。”不幸的是,互联网和轻文明让以上这个人群造出了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
这个人群长期被社会歧视,他们或因宗教,或因种族,或因个人问题,被整个社会遗弃、抵制、嘲笑和边缘化。他们希望以极端方式制造流血事件引起社会的关注,接着他们想到了快速、便捷的“轻传播”——互联网。毫无疑问,这些行为其实和互联网的技术革新以及轻文明的不断发展有关。这就是我想说的“轻到极致便是重”。

在互联网和轻文明背景下,存在着一些被扭曲了的、信奉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群。图为2016年法国尼斯恐袭。
《新周刊》:你对轻文明持正面还是负面评价?
利波维茨基:不能因为轻文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武断地认定它是“灾难性”的。至少在我看来,我们应该赞扬轻文明:它让生活便利,让消费迅捷,让身体悬空,让身心舒畅。
但我们同样要提防轻文明变异为重文明。这也是我在书中反复提及的。
《新周刊》:你害怕“轻”变成“重”的那一天吗?
利波维茨基:害怕。我害怕那些“轻”达到一种极致后,会变为“不可承受之重”。
以上内容首发于《新周刊》499期
《<新周刊>2017年度佳作·生活太重,让我飞一会儿》
漓江出版社出版

活动规则
1.在下面留言区中说说“你对‘轻生活’的体会”,我们将为评论
点赞数最高的5位用户随机赠送一本新书。
2.活动时间:2018年4月26日— 2018年5月1日(仅6天)。我们会在5月2日联系点赞数最高的5位用户,到时请获奖者及时向后台发送姓名、地址和联系电话,以便送书。
欢 迎 分 享 文 章 到 朋 友 圈
作者 / Junitaille排版 / 刘强
新周刊——中国最新锐的生活方式周刊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