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布什总统家的悼词来,这位留美生物博士怀念父亲的文章也很催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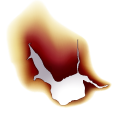
春天应该很好
倘若你在身旁

前几天,芭芭拉·布什葬礼上亲人们对她的致辞《老布什总统夫人葬礼上亲人的欢乐致辞,让人们懂得家族传承要义!》被转载在我们平台上并引起广泛讨论,网友们纷纷留言说,致辞的内容虽然轻松幽默,可未读完就已经让人感动落泪。
其实,不只是美国总统的妻子、母亲,全天下的父母都是伟大的,不管是身居高位的天佑家庭,还是我们老百姓的普通人生,对父母的爱,永远是心中最难以言喻的感情。本文作者讲述了自己与父亲之间的经历。这是一个最普通的故事,最让人感动的情感、也是最质朴无私的爱。
原文作者:长大不容易
文字编辑:Lor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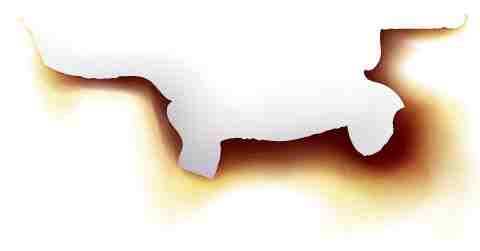
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背影》朱自清
无言不怨天·我的父亲
上个月我在海边露营时梦到他,之前也梦到他好几次。这让我觉得一直不抽时间写他,确实有点说不过去。远走的一切一切,溶淡模糊、多杂分散,总不知从何写起,如何提炼。
他死于09年9月9日,今天是六周年祭,倘若尚在人间,今年八十岁。姐在朋友圈发了他的脸,我的脸,我外甥的脸,并列在一起,传承情怀:老排长,二排长,小排长。我愧对这世界许多感情,这是最大的一份,喝他的血长大,滴水未还。补几个字,感激被给予的探索人间的机会,感激被给予的沉默的榜样,感激被给予的体会卑微人类无限可能的可能。
09年7月,姐在电话里说:“他病重了,年初肚子痛,饮食困难,以为是小病,社区医院按感冒治,但每况愈下。最近去医学院诊断,说是残胃癌,身体底子太弱,做不得手术,只能姑息治疗,住院眼看好一点,出院回家又反复,常常痛得不能吃饭。这次入院住在医专,恐怕就要撑不过,要不回来看看吧。” 我定了一张机票,转了三个飞机,落地泸州。

他住在肿瘤病房,瘦得不到七十斤,手臂挂着大输液,鼻子插着氧气管,只吃液体半固体。病房没空调,与二三十年前的设施,没有本质区别,无外乎楼更密,人更挤,夏天更热。记得他以前麻利得紧,比划起来动作迅猛,能晃瞎我的狗眼。我比较快的的反应、判断、决策、移动,这跟他的闪电手不无关系。病床上的他,每个动作都慢下来,和记忆里相比,都是慢动作回放。每次稍有活动后停下来,他就会沉默一会儿,仿佛在思考人生。他是聋哑人,没有受过教育,勉强会写几个字,不知语法,不懂逻辑,我不觉得他有资格思考人生,沉默顶多算是有闲发呆。
很久很久以前,同一家医院,我得过一次痢疾。在家折腾几天后,我基本虚脱,站也站不住,生活不自理,土法子用尽,只好送医学院。医学院在泸州的最高山。那一天天没亮,只有裸街袒着肉色,任由路灯在它胸口玩树影。我的意识里,只有他的脚步声,长长短短,刷刷刷刷。80年代没有出租车,公交车还不到发车时间5:30。五更天可以叫到的,最可靠的交通工具,只有他的罗圈腿。我趴在他的背上,强壮实贴,爬四十分钟上山,没有休息过一次,偶尔站定,将我往上一耸,搂紧了继续爬,白背心下的胸口,装着老栓般的心。
肿瘤病房住院,似乎让他有所好转,一周之后出院,回到家里,小猫花花很欢快,以为饲养员又回来了,围着他嗷嗷的蹭,完全不知道可能将他蹭倒在地。他已经有心无力,不能再照顾任何人。不过他依旧热心给大家安排伙食,一三五,二四六:鸭子要的仔姜应切片,鱼要泡姜海椒切丝,豆瓣要剁细再下锅炒香,葱不能省并且要切碎花。他刚刚能走动,就率领我去菜市场,亲自指导我采购食材,指挥操作。他自己只吃一丁点,作为参与评价的依据。先吃完也不下桌,看我们吃,他间或转开脸,目光落在脏黑的墙,沉默中仿佛在思考人生。他没有经历富贵坎坷,不曾目击波澜跌宕,没有阅读经史子集,哪里有深邃人生的机会,沉默无非是因为大脑一片空白。

很久很久以前,同一个家,他是我们的炊事员。在四川,吃的传统高于一切,他示好的方式,就是在家做吃的。每次回去的第一天,他已经将一个周的伙食,都在心里安排好。菜单熟悉而新鲜,既不脱旧时口味,还总有创新点。他常常抱怨出去吃不好,几百大洋味道顶屁,非要在家里做的才是顶呱呱。他当面想说什么说什么,背地里想说什么说什么,这常会招人烦,甚至招我烦,让我不好承认他是谁,谁是他,不仅仅是我羞于做残疾人的儿子。但他逢人便宣传谁是我,我是谁。所以在那个狭小拥挤的街区和城市,我的基本代号是“哑巴的儿”,不好的时候是龟儿“哑巴的儿”,好的时候是争气的福气的“哑巴的儿”。我名气的顶峰,竟然与我绝顶聪明,才华横溢无关,被简单粗暴到无处躲藏。
医院肿瘤科回家以后,除了关心伙食 ,他依旧喝茶加糖,在昏灯下看报纸,数枕头下藏的钱,开着电视打呼噜。他的这些习惯一度也在我身上,离家出走15年,多数已经没有了,而他还保持着这些惯性,我在一旁看书,陪着观察,时不时落入思考的人生的游离状态。
很久很久以前,他是个被动工作狂。他没有单位,没有老婆,只会裁缝,有两个孩子。他早上五六点出门兜售手艺活,留两毛钱在我床头,让我买早饭。我在学校上课,他卖完小货,买菜回家,开始裁裁缝缝,到点做饭。等我们中午放学回家,就有饭菜摆在桌子。午饭后睡一觉去上学,他继续干活,晚饭做好等我们回家吃。好吃的吃完我接着耍,不好吃摔锅砸碗要吃肉。无论好歹,饭后他收好一切,又继续干活,有时候赶工到临晨,缝纫机突突突突伴我整宿。次日一早多半要送货上门,有记忆的10年,这个pattern基本不变:他永远在突突奔忙,永远没有几粒存款,永远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生意。那时候没有见过他发呆,每个下一分钟都要谋生,或为谋生做准备:三条人命相关,一顿都不能省,真没有见过他思考人生。
医院回来一周后,我看他逐渐好转,于是回美国。当时我也有很多责任,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寄托考试,是被动的工作狂:永远在忙,永远没钱,永远未知明天,永远在思考人生时感觉在浪费生命。
9月9日,姐来电话:“他痛得不行,又不能好好吃东西,上次出院说开吗啡止痛,他也都不愿意,总是扛着,也不吱声。饭一天比一天吃得少,觉一天比一天睡得多。醒来说他枕头底下有些钱,他要是人没了,都给了我。他无论多虚弱,都要自己下床,自己上厕所,不要人帮。最近几天坐不起来,帮一帮他,他很自恨这种无力感。今天早晨帮他小便以后,问他要不要点别的,他侧躺着,背对着我,伸出右手弱弱的摆了两摆,似乎是不要帮,又像是告别。六点多再去看,他不能应,感觉已经没有气,赶紧叫了有经验的人来,说是已经归天。”

很久很久以前,他娶过我妈。我妈姓林,排行第九,大家叫她叫林九。林九说他年轻时帅得一塌糊涂,篮球打得好,穿军装,戴军帽,洋气非常。我两岁时,林九被迫寻求别样的生活,留了他穷极孤身,和我姐弟相依为命。他有怨但不变初衷,说他一生见过的最好看的,莫过于林九。我们多次尝试挑拨离间拉仇恨,都无法动摇他的观念。我不知道农村菇娘林九,年轻时候得有如何高颜,才能让一个受伤的人三十三年审美不变。传说我小时候长得像林九,所以被宠得很坏。又因为我外甥长得像我,也被宠得很坏。传说我爷爷的眼光会黏我,看着我一举一动,会双眼迷离,表情老年痴呆。同样,我爸爸在我远走之后,眼光会黏住我外甥,看着小人一举一动,眼神迷离,表情老年痴呆。
他一生七十四年。年轻时,只与面前的吃喝拉撒应战,简单粗暴:球约起就打,酒来了就灌,喇叭流行就穿,文革来了就战,弹片入眼就挑,胃溃疡一切再切,一言不发,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干,没有机会受教育,谈不上人生,无需思考人生,干脆不屑思考人生。感觉无论多简单的生物活到六十,也多少都开始有“思考人生”的能力。或者有貌似思考人生的姿态,让人错觉他们具备思考的能力,像树荫下乘凉的大象,石滩上晒背的老龟。他也许脑里仍然只是处理最表面的画面,体验着最简单的情绪,满足于最基本的幸福,却有貌似思考人生的庄严外表。但我无法排除,他思考过人生可能,只不过没有表达的工具。
现在,写这几百字散碎,勉强浓缩父亲的一生。回忆里落笔处,尽是老病死,孤独离,欢少悲多。父亲没废话,跑满全程,冷倔穿透命运赏给他的七十四年无语的旅程,接受花样繁多的磨难和挑战,最后任性离别。怎么看,都象征高冷无言,对喧嚣恶劣的鄙视。
还有什么比父母心中蕴藏着的情感更为神圣的呢?父母的心,是最仁慈的法官,是最贴心的朋友,是爱的太阳,它的光焰照耀、温暖着凝聚在我们心灵深处的意向。
——马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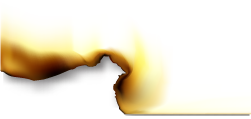
相关文章阅读:《老布什总统夫人葬礼上亲人的欢乐致辞,让人们懂得家族传承要义!》
阅读原文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