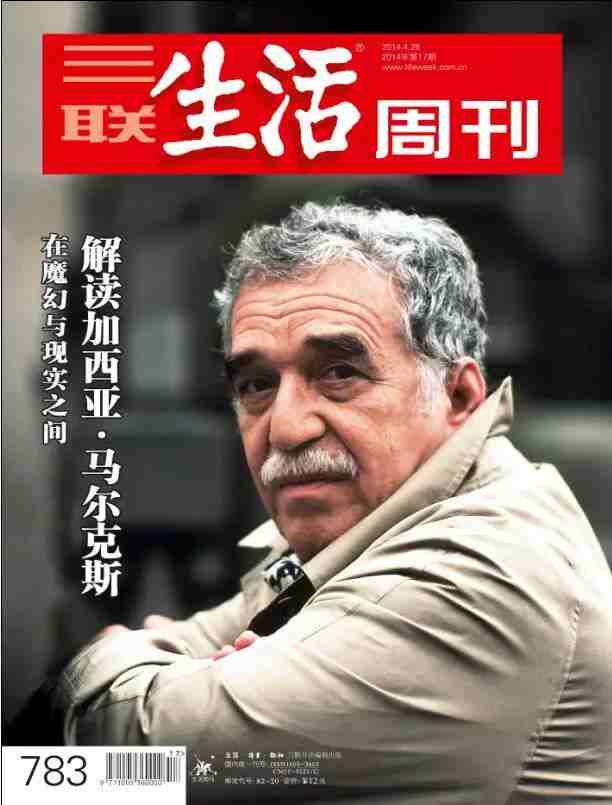马尔克斯去世4周年 | 朱伟:他有敏感的性感

-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第17期封面故事「解读加西亚·马尔克斯」,原标题为“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我们”。(文末可购买旧刊)
我们几乎都是在80年代,通过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的《外国文艺》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编辑的《世界文学》这两本杂志,接触了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与他们的作品。马尔克斯只是其中之一。正是这些作品,哺育了一整代80年代的作家,不断滋养了80年代高潮迭起的文学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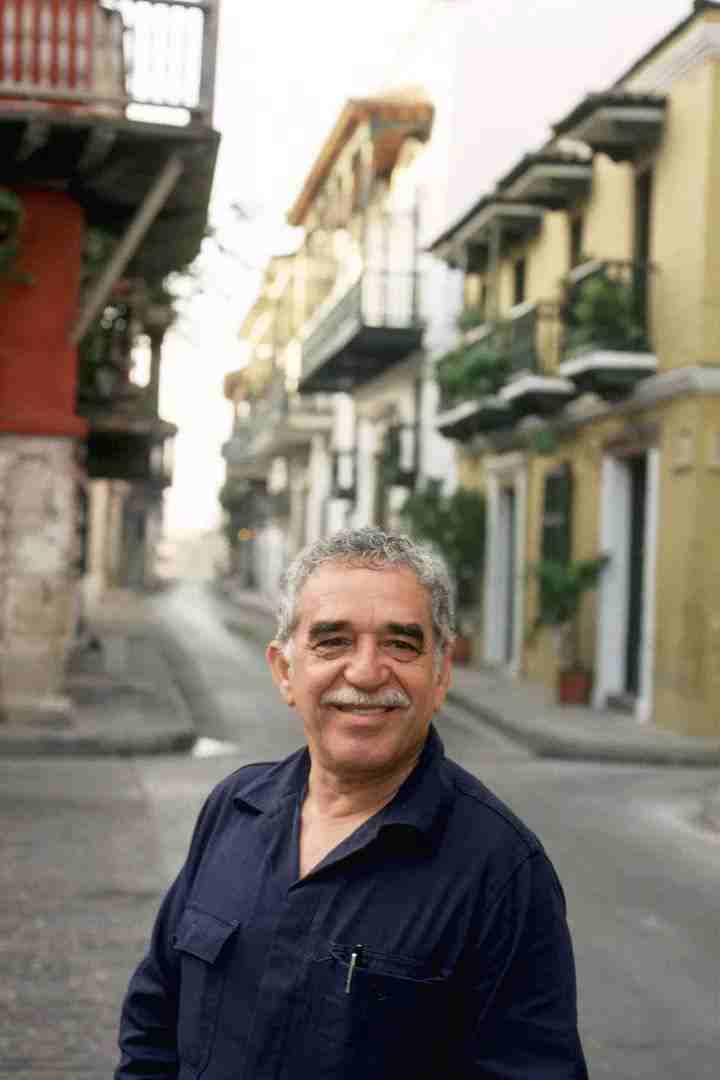
《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记忆中,拉美文学最早进入我们视野的是博尔赫斯,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的1979年第一期《外国文艺》上就介绍了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的四篇短篇小说,为首的就是著名的《交叉小径的花园》。通过这篇小说,我们看到了当时我们所热衷的美国文学之外的另一种文学可能,它让我们看到表象与意象的关系能够构成扑朔迷离的时空关系,这种时空关系就能构成引人入胜的故事悬念。通向悬念的“交叉小径”于是也就变成了一种认识论,对我而言,那其实是最原始的哲学启蒙。
第二位认识的拉美作家是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主办的《世界文学》1979年第六期就发表了由黄志良、刘静言翻译的阿斯图里亚斯的长篇小说《总统先生》的选译本。而首次读到马尔克斯,则是在1980年第三期的《外国文艺》上,在我记忆中,那是马尔克斯第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那时候《外国文艺》轻视了马尔克斯的地位,所以,这组由周子勤、刘习良、刘瑛翻译的四篇短篇小说排在了目录最后,开头有关马尔克斯的简介是陈光孚由先生撰写的。陈先生最早告诉了我们:马尔克斯的代表作是《百年孤独》,它被誉为“当代的《堂吉诃德》”,他是“聂鲁达之后最伟大的天才”。陈先生也是最早引进告诉了我们“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标签,他这样介绍——
马尔克斯的文学创作,一方面受到乔伊斯、卡夫卡和福克纳等欧美现代派作家的影响(当时还是以欧美为对照坐标),另一方面又继承了阿拉伯东方神话和印第安人民间神话传说的传统。他的作品往往把幻境与现实、人与鬼糅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风格。他是当前风行于拉丁美洲最重要的流派——魔幻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性作家之一。
但是,什么叫“魔幻现实”?这个标签其实对真正接近马尔克斯无益,当然,这是我真正进入马尔克斯所叙述的世界之后才认识到的。

这一期《外国文艺》推荐的四篇小说选自马尔克斯196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格兰德大妈是一位女族长,她主宰着马孔多这个近亲繁殖构成的族圈,是马孔多权力的象征。这篇小说有关格兰德大妈的生前其实只用了一个细节:每到下午,她就会在“摆满海棠花”的阳台上眺望她所拥有的一切,一切都属于她,于是她“全身的重量和权势像要把她坐的那把旧藤椅压成粉碎”。她从20多岁的少女变成一个符号后,在小说中一下子就成了面对葬礼的90多岁的大妈。马尔克斯所结构的葬礼是一个等待的过程:格兰德大妈的遗体在不断腐烂中等待仪式的诞生,而仪式本身其实并不重要。读完小说之后你才会意识到,小说中真正有价值的是她临终前威严地口述的那个她所留下的无形资产的清单:
地下资源、领海、国旗的颜色、国家的主权、传统的各种政党、人权、公民的权力、最高法官、第二和第三审判、第三次辩论、介绍信、历史的证据、自由选举、选出的历届美女、那些有影响的演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漂亮出众的小姐们、举止端庄的先生们、拘泥呆板的军人、尊贵的阁下、最高法庭、禁止进口的商品、自由派的女士、肉的问题、语言的纯洁性、世界的樊篱、司法程序、自由而又负责任的新闻事业、南美的女神、公众的舆论、民主选举、基督教的道德、外汇的短缺、避难权、共产主义的危险、国家的库存、生活费用上涨、共和派的传统、受损害的阶级,以及联合通报公众的选举。
这些都是她的财富。而与这个清单对比,才是葬礼的意义:
坟墓用铅板加封后,人们都舒了一口气。
在场的人也有些头脑比较清醒的,预感到自己参加的是一个新时代降生的洗礼。
现在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格兰德大妈这块广漠的庄园里占领地盘,搭上自己的帐篷。因为那位唯一有权压制他们的人已经在铅板之下开始腐烂。
这篇小说中什么是“魔幻”呢?你只能说,格兰德大妈是一个象征。这可能是马尔克斯表达他的意识形态倾向的一篇小说。
这种象征氛围的结构,在80年代中国小说家的创作中,后来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母题。

《外国文艺》这一期推荐的马尔克斯四篇小说中真正触动我当时心灵的,其实是那篇大约只有3000多字的《礼拜二午睡时刻》。这篇小说的一大半篇幅都在铺垫:在午后炎热没有生气的阳光下,一对沉默的母女在车厢里,她们带着一袋食品与一束报纸包着的花,默默地吃着简易的午餐。车到目的地前,母亲告诉女孩:“你要是还有什么事就赶紧做好,往后就是渴死你也不许喝水,尤其不许哭。”然后她们下车,走过小镇,进了教堂请求见神父。刚刚午睡的神父好不容易被请出后,要求是“借一下公墓的钥匙”。原来,母亲带着女儿是来看望一周前被作为小偷打死的她的独生子。而其中的悲伤只在这样冷静的描述中——
“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过去他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都拔掉了。”女孩插嘴说。
“是的,”母亲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就好像看到礼拜六晚上他们打我儿子时的那个样子。”
“哎,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神父说。
无需赘言,一切都在铺垫中解决了,这就是伟大优秀的作家。
优秀的作家给你以启示,却不等你的阅读感觉到累,就已经结尾了。
《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如果说,《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还不足以引起当时文学青年们的好奇心,这个中篇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则马上成为当时我们议论的热点了。在推介马尔克斯的竞争中,《世界文学》是明显落后的,这篇小说最早还是发表在1981年第六期的《外国文艺》上,译者是李德明、蒋宗曹。值得一提的是,此小说是马尔克斯1981年当年创作当年就翻译进国内的,我们都是先认识“谋杀案”,再认识《百年孤独》的。
这桩谋杀案的故事是夸张又真实的:新娘安赫拉·维卡略嫁给了富裕的巴亚多·圣·罗曼。在那场豪华的婚礼结束后的狂欢再结束后,罗曼发现了妻子不是处女而把她退回了娘家。而安赫拉·维卡略事先已经准备了伪装处女的工具而不屑于实施,就因为她认为那一切是卑劣的,因为她“决心死”。安赫拉·维卡略被退回后,轻易就说出了情夫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名字,于是她的两个哥哥就决定要杀死纳赛尔。
故事的悬念并非是人们普遍认为安赫拉·维卡略隐瞒了那个真实的名字而纳赛尔如何成为无辜者,而是凶手预先不断张扬了这桩即将发生的谋杀案,甚至作者马尔克斯要不断地强调“与其说维卡略兄弟急于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不如说他们是急于找到一个人出面来阻止他们杀人”,因为杀人只是为维护荣誉。但最终谋杀却还是按时发生了,各种各样事先知道了这桩即将发生谋杀案的人,都因各自原因疏忽或失去了阻止它发生的机会。这样的一个精心构置的结构,如果体会到这其间弥漫的漠然所要表达的冷酷,多少是一种浅薄的认识。马尔克斯通过他不紧不慢、极其冷静的叙述,其实要表达的是命运的作用。
这是第三人称冷静的推进与第一人称“我”对真相的追寻天衣无缝地交叉的叙述,马尔克斯小说的每一个开头作为线头拉开的开端都是特别优秀——
圣地亚哥·纳赛尔在被杀的那天,清晨五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主教将乘船而来,他要前去迎候。夜里,他梦见自己冒着蒙蒙烟雨,穿过一片榕树林,这短暂的梦境使他沉浸在幸福之中,但醒来时,仿佛觉得全身盖满了鸟粪。“他总是梦见树木。”二十七年之后,他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回忆起那个不幸的星期一的细节时,这样对我说。
自如的转换中,就完成了完美而极具诱惑力的叙述。马尔克斯自己说,对他而言,开头的第一句往往就是全篇的基调,它决定着结构,更决定着叙述风格的选择。何谓叙述风格?我体会到是一种气息,是这种气息引导着叙述的途径。当然,这也是后来我才意识到的。

在这篇小说的推进中,展开了清晰又不清晰的人物关系。有意味的是,安赫拉·维卡略在并无爱心的前提下嫁给了巴亚多·圣·罗曼,但从他退婚起,她却声称爱上了他,开始不断地给他写情书,而他究竟是死于酒精中毒还是真的重新走到了她的身边?结论是可以游移的。圣地亚哥·纳赛尔究竟与安赫拉·维卡略的失身有没有关系,安赫拉·维卡略的两个哥哥究竟怎样躲避这场谋杀而不及,小说也有意回避了去营造有关纳赛尔的疑问,小说中只是出现了那个名句——
给我一个偏见,我将使世界转动。
这是此案的预审法官在阅读纳赛尔的案卷后所作的批注。
马尔克斯在小说中省略了两个凶手的路径,却专注地描写纳赛尔的朋友克里斯托·贝多亚知道即将发生的谋杀后四处焦虑地寻找纳赛尔的错位,纳赛尔与他步步错过。最后的错位是纳赛尔死于他自己的母亲——他跑到家门口时,他母亲以为他已经上楼回了房间而闩上了门,两兄弟以为他平时都走后门而不走前门,而他偏偏走前门而被堵在了门前。结尾是细致如手术刀般的杀戮过程。最后的结尾还不忘残酷的细节——
他在最后一道阶梯上绊倒了,但是立刻又站了起来。“他甚至想到用手掸掉沾在肠子上的尘土。”我姑母维内弗里达对我说。
如果认真读完这篇小说,你会体会到马尔克斯真正有兴趣表达的大约是命运的无可逆转,其中重要的是一些暗示。当然,重要的不是有关命运这样大家都关心的主题,而是自始至终所营造的那种氛围。我尤其难忘的是谋杀前主教到来的汽笛与遍地鸡鸣声。这篇小说那种不动声色的谋杀氛围构置实在启发了后来许多小说家的构思,而最终那种细致又精疲力竭的杀戮,也成了启发很多作家描写残酷的源头。比如莫言《红高粱》中对肢解罗汉大叔过程的渲染。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翻译后,上海译文出版社迅速组织编辑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选》,在1982年10月以“外国文艺丛书”的一种出版。这部小说集中,除了《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与《外国文艺》1980年第三期推荐的四篇短篇,还组织力量增译了另外12篇,当时定价1.95元,印了4.2万册。小说集前有赵德明先生的序,对马尔克斯的生平与创作做了详细介绍。
上海译文出版社之所以用如此快的速度推出这部小说集,是因为拉美文学在当时的影响力已经迅速超越了他们所推荐的欧美作家,其中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翻译出版的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胡安·鲁尔福中短篇小说选》(当初定价0.79元,印了2.4万册)起到了爆炸性影响,其在扑朔迷离中打破时空寻找父亲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帕拉莫》成为当时文学青年的我们急切传诵的对象,“魔幻现实主义”成了最时髦的标签。
在这部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厚达700多页的小说集中,我尤其喜欢这篇《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上校是一个被冷酷的社会现实所遗忘者,这又是一个把辛酸埋在故事底下的小说,也可以说它根本就没有故事。主人公是退伍的年迈的上校,上校一直在苦苦等待着一封信,这是能支撑他生活的养老金,他等了15年,却一直没等到——没人给他写信。
用他律师的说法,因为他的申请材料在“成千上万的办公室里,不知经过多少双手传来传去,弄得谁也不知道在什么部门了。15年里至少换了7届总统、15届内阁”。这就是哥伦比亚的现实。上校有一个患哮喘病的喋喋不休的老伴,还有一只每天争食他们口粮的斗鸡。那只斗鸡其实是上校的精神寄托,因为它代表着儿子。在斗鸡场上,因为这只鸡,他唯一的儿子被活活打死了。

严格说,这篇马尔克斯30岁时创作的小说明显受海明威的影响,它的“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基本通篇是上校与他妻子的日常对话,在不断揭不开锅的贫困中等待,在其实是毫无希望的等待中应付一天天具体的生计:食物在哪里?还有什么能换来粮食?能不能将鸡换成钱?而那些正挥霍着钱的政客,上校对失去儿子的伤痛,全都在表面的琐碎对话背后。马尔克斯的叙述是那样的克制,没有一点愤慨的情绪流露。控制力,这才是一个优秀作家最令人赞赏处。
而这篇小说更令我感动的,则是上校身上所隐含的那种气质:他守护着对逝去儿子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守护着他自己的尊严。
而在我们的作品中,最缺的大约就是尊严。
《百年孤独》
这一年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2月,《世界文学》就发表了由沈国正、黄锦炎、陈泉翻译的马尔克斯代表作《百年孤独》的选译。那个著名的开头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以“二十世纪外国文艺丛书”出版的这三位译者的全译本中定稿成了——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个著名开头在1985年后,不知被多少文学评论家讨论过,他们由此提出小说归根结底是叙述的艺术,由此叙述的技术论就有了广阔的市场。但我敢肯定,这些文评家中真正有耐心读完这部尽管篇幅还不到30万字的小说者应该寥寥无几。其实这是一部越读会越感艰难、疲惫的书(尤其是后半部),真正有耐心把它认真读完的人其实不多。有意思的是,达不到这样纠缠着疲惫的阅读效果,还真难获得诺贝尔奖。诺奖要求的是像巨石般压人的厚重。
其实,马尔克斯自己也并不喜欢这部小说。

有关这部小说,最先触动我的,应该是大约1985前后,我读到一篇马尔克斯的访谈录,其中说到父亲带他去触摸冰块对他创作的意义。他说,他当时震撼的是,感觉那冰块是滚热的,由此他才意识到,小说原来是可以这样来写的。
《百年孤独》的第一章结尾,他就这样描述这个冰块(使用范晔获得版权的译文,南海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同)——
巨人刚打开箱子,立刻冒出一股寒气。箱中只有一块巨大的透明物体,里面含着无数针芒,薄暮的光线在其间破碎,化作彩色的星辰。
奥雷里亚诺却上前一步,把手放上去又缩了回来,“它在烧”,他吓得叫了起来。
那么,“面对行刑队”的开头与冰块,对这部小说究竟构成了什么意义呢?我以为,第一是时空恍惚,《百年孤独》是要感叹或反思马孔多的改变、沦丧、变成似是而非吗?从梅尔基亚德斯对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诱惑始,马孔多想打通与现代文明的道路受挫时,那是一个乡土的恬静的田园。而随着文明的脚步真的临近,在吉普赛人之后,就有了意大利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美国人,有了教堂,有了商店与妓院,有了政府,有了暴力与谋杀,有了士兵与战争,也有了铁路与汽车,那么,马尔克斯是在因此哀叹现代文明的侵袭与蚕食,使得布恩迪亚家族血脉舒展的村庄不存吗?
这越来越纷乱的百年中,乌尔苏拉其实是一个完整的见证者,她活了“一百一十五到一百二十二岁之间”。她看到了什么呢?小说中,在目睹百年沧桑的乌尔苏拉临终前,与她的孙子何·阿卡迪奥第二有这样的对话:
“您还指望什么?”他喃喃道,“时间过得真快。”
“话是没错。”乌尔苏拉说,“可也没这么快。”
这样的对话,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要被枪毙之前,她去探望他时,与他对话的重复。只不过当时,“你还指望什么”是她对儿子说的,“可也没那么快”是儿子的回答。其实,《百年孤独》的重要性,恰是在这样的时空关系——它真正要写的是百年世事纷乱中人生之可悲,每一个人都无法摆脱宿命。百年世事只是纷繁的背景,这就是乌尔苏拉在临终时所要强调的她的感觉:“时间其实只在原地转圈。”所谓“魔幻”,其实并不在飞毯、吃土这样的奇异,而是在正常的时空关系可打破、世间与冥界可以相伴共存这样的关系中。
文学是人学,所以,阅读这部小说的钥匙是在它对人物的思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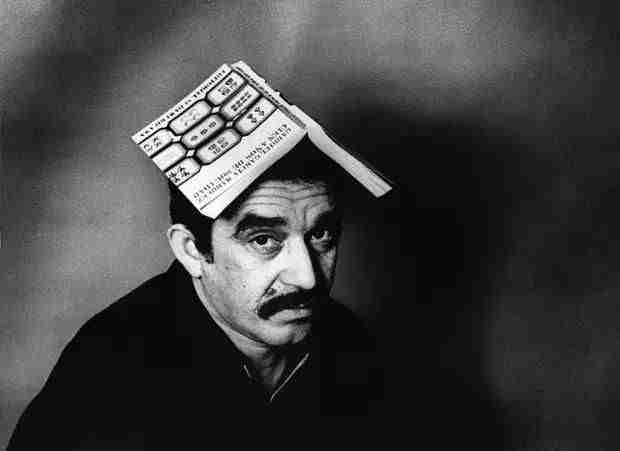
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
如果把乌尔苏拉视为见证者,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无非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与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何塞·阿尔卡蒂奥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以及阿玛兰妲。
牵引作为父亲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命运的是科学,他因此一辈子都因梅尔基亚德斯对他的诱惑而沉溺于所谓“科学”的发明,表面看,牵制他的新鲜层出不穷,最终其实由起点再回到起点,在梅尔基亚德斯的坐标之外,陪伴他的是一直追随他,被他杀死,在超自然力中永生的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牵引大儿子何塞·阿尔卡蒂奥的是欲望,因为他拥有的最突出资本就是他的性器,他因此而走出马孔多,远涉重洋,最后回归,无论拥有什么样的性对象,最终仍在原点。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呢?与哥哥比,他起先是性无能,然后是最无情者,他从追求自尊走向追求权力,在无情中出生入死。他曾经的好友蒙卡达曾这样说他:“你那么憎恨军人,跟他们斗了那么久,最终却变得与他们一样,人世间没有任何理想值得以这样的沉沦作为代价。”但他在拥有荣誉后,仍然回到了那个作坊,做他的小金鱼,做它的目的是把它销毁后重做。
与这三位男性比,最耐琢磨的是作为女性的阿玛兰妲,我们读小说,往往难以破解她与皮埃特罗·克雷斯皮,与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甚至与侄子奥雷利亚诺·何塞的关系。最后是旁观者,母亲乌尔苏拉提示我们:她其实是“世上从未有过的最温柔的女人”,她的无法解读是因为,她一直深陷于无穷的爱意与无法战胜的胆怯之间无穷尽的折磨之中,直到最后死神伴随她缝制自己寿衣的时候来临。
这就是宿命。不好好阅读体会这部小说,你不可能体会到,这才是冰块寒与烫的不同感受中马尔克斯真正要讲述的。可自从它1984年完整地推介到国内后,多少作家以它为灵感澎湃的起点,又有谁真正能够写出这样的宿命呢?许多知名作家,只不过都在时代变迁、意识形态控诉层面徘徊罢了。
在宿命这个冷酷的认知中,马尔克斯所写的每一个人物关系,都只不过是无为的挣扎而已。其实我感兴趣的,倒是他在其中所叙述的诗意:那个何塞·阿尔卡蒂奥穿过房间的迷宫寻找那个女人特尔内拉的气息;美人蕾梅黛丝随着鼓荡发光的床单飘然消失在“连飞得最高的回忆之鸟也无法企及的高邈空间”;阿玛兰妲最后盘好辫子走进了棺材,然后要来了镜子,40多年来第一次看见自己竟然与想象中的形象分毫不差。马尔克斯曾说,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使命是对诗意的寻找——“哪怕是现实最平庸的时候,也要使它充满诗意。”
没有这样的诗意,冷酷是没有价值的。
《霍乱时期的爱情》
我毫不讳言,马尔克斯的小说中我最喜欢《霍乱时期的爱情》,然后是《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再然后才是《百年孤独》。这其中漏了《家长的没落》(完成于1976年)。马尔克斯自己是很喜欢这部小说的,说它完全由散文语言写成,遗憾是我自己至今没时间读它,于是只能将它排除在外。
这种排序,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三部小说,《百年孤独》写得最早(完成于1967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完成于1981年)与《霍乱时期的爱情》(完成于1985年)因此比《百年孤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情节、节奏与叙述之间的关系。它们因此都强调了悬念的作用,照顾了读者的好奇心与阅读的可持续度。
我以为,从《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到《霍乱时期的爱情》,马尔克斯真成了一个结构大师。说实在,我最初阅读《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第一章,就被马尔克斯的果断所震撼。第一章刚刚阅读到阿莫乌尔预先策划的自杀,乌尔比诺医生根据遗书的指引,找到了阿莫乌尔隐秘的情人,以为这隐秘的爱情就是一条路径,却迅速转向以各种精微细节描写作为老伴的乌尔比诺医生与他妻子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和谐相处。
而当医生乌尔比诺准备去参加阿莫乌尔的葬礼时,他又因蹬梯子抓他心爱的鹦鹉落空而迅速死亡了,这时你才知道,阿莫乌尔的私情只不过是小说引子中的美丽诱饵,真正的主角是在医生葬礼上出现的阿里萨。在这一章乌尔比诺医生的葬礼结束后,阿里萨向医生的遗孀费尔米纳振聋发聩地表白:“我为这个机会等了半个多世纪。”这一年他76岁,她72岁。这个跌宕起伏的开头真的太精彩了。
马尔克斯写作这部篇幅其实接近于《百年孤独》的小说,一共才只用了六章。我首先是钦佩于他居然敢用26万字的篇幅,只写单纯的爱情(不掺杂任何社会意识形态),而且着重只写费尔米纳、阿里萨与乌尔比诺这三者关系。有关过程,表面看也并不脱俗套。第二章:阿里萨对费尔米纳殷勤、漫长而自我折磨的求爱过程,在过程的结尾却是,因她面对他,感觉到了他对她的卑微而失败。
第三章:相反,乌尔比诺医生用了完成不同于阿里萨的求爱方法,以不容置疑的态度,步步紧逼,当将猎物逼向绝境时,反而获取了婚姻。第四、第五章:用了最长的篇幅,来讲述阿里萨长达51年多的等待,其中有五花八门他度过自己畸形的思恋而赋予自己坚持之恒心的方法。第六章:当乌尔比诺终于被耗死后,阿里萨重新恢复了他疯狂地抒写情书的能力,他们重新开始,从拘谨的到放松的见面,最后坐上了幸福的航船,真正开始半个世纪等待后的心灵战栗的交会,开始“永生永世”浪漫的航行。
故事框架并非传奇,但如仔细阅读第四、第五章阿里萨与众多走马灯般的女人们的性爱经历,他说,他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来消解/维系对费尔米纳之爱。当初,他获得费米尔纳的爱时,也是住进妓女们的客栈的。这就使爱情这个主题有意思了:阿里萨对费尔米纳的爱情是坚韧的等待,等待的结果是有一个人必须死去;而维系阿里萨爱情的坚韧的,却不是清教徒的守身,而是不断在新的女伴身上萌生或者吸纳其爱,这爱非宣泄而是滋养与孳生。正是这样,他在51年后,才终于等到了乌尔比诺医生死之机会。而当他相隔半个世纪重新面对费尔米纳时,她看到的是,他已经从那个卑微地在公园长椅上可怜巴巴地窥视、唯唯诺诺地等待她的曾让她失望的人,变成了一个真正能如磁石吸附她灵魂的人。

马尔克斯与妻子和两个儿子
这是一种魔幻故事吗?不,这正是残酷的现实。马尔克斯说过,他的兴趣只是“间接地”正视现实。他要“间接地”表达什么样的爱情观呢?当然,婚姻非爱,“婚姻是个只有靠上帝的仁慈才能存在的荒唐的创造”,这是小说中乌尔比诺医生的观点。那么爱呢?“世界上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情了。”我能感觉马尔克斯要通过这部小说,表达爱的酸楚:当阿里萨经过漫长的等待,真正抚摸到他的爱人的身体的时候,触摸到的已经是“像装着金属骨架一样的胸部”了。
“让时光流逝,当会看到时光给我们带来的东西。”这是费米尔纳给阿里萨回信中的语言。这就是时光带给他们的启示。
我喜欢这部小说是因为,我从马尔克斯的叙述中感到了一种高贵,无论哪个人物,无论是如何的性本能冲动,都干净而绝不丑陋卑鄙。
这样的爱情,大约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可以模仿。王小波是借用过其中的一个细节的,那是乌尔比诺医生与那个黑姑娘林奇小姐匆忙的做爱。马尔克斯叙述说:“他连上衣扣子还来不及解开,鞋都来不及脱就心惊胆战地做起爱来,没有尽兴就惦着要离开。当他重新系上衣扣的时候,她还觉得刚刚起了个头。”马尔克斯称,“他恪守给自己规定的框框:做完一切,不超过做一次静脉注射的时间。”王小波转用到他的小说中,就称匆忙的性交只不过是“皮下注射”。
《睡美人的飞机》
《霍乱时期的爱情》应该是马尔克斯创作的巅峰,他之后再没写成产生巨大影响的长篇甚至中篇。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家,其实都只有一个短暂的辉煌期,似乎是气力用完之后,就再难呵气如虹了。
再偶然读到《外国文艺》上翻译他的短篇小说,已经是90年代某个在办公室里短暂午睡前的闲手翻到的了。篇名似乎叫《睡美人的飞机》:第一人称,描述“我”在机场办登机手续时邂逅一位美人。当时飞机延误,他到处寻这美人不见,登机后蓦然回首,却发现她就在邻座。美人起飞后倒头便睡,他就默默守候、享有这美丽。在黑暗中,他与她几乎同枕而眠,充分享有着她的呼吸。
这样的经历大约很多人都会偶然遇到。到清晨,他在盥洗镜内看到了自己的衰老与丑陋,而飞机降落前,美女苏醒了,他们没有对话,没有细微的接触,最终她抬手穿衣的时候胳膊掠过了他的脸。然后,飞机停靠后她走了,他无需惆怅。这样自然的陌生的相遇与离去,在极短的篇幅中隐含了极多微妙,读后在回味中就有了微笑,这就是我喜欢的马尔克斯。他有敏感的性感,否则也不会把《霍乱时期的爱情》写得那么迷人。
之后再读到《外国文艺》上刊登他的回忆录《活着为了讲故事》的选译,让我明确了,指引他小说魅力的其实是气息,没有了气息指引,他所构置的世界就会空洞而单调,所以他小说中最迷人也在绵长的气息。它也让我明确了,他小说中所描写的确实都是真实,如他所说,“虚幻只是粉饰现实的工具”,想象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坚实的力量,这是所谓“魔幻现实”真的含义。而我们的作家们却往往颠倒了彼此的关系,于是,所谓“象征”或“魔幻”,就都变成了字面上平庸的游戏。
大家都在看这些👇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
点击以下封面图
一键下单「解读加西亚·马尔克斯」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周刊书店,购买更多好书。
阅读原文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