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燕子”赵薇挨罚,五大板子打得对不对?聊一聊股权交易信披的对与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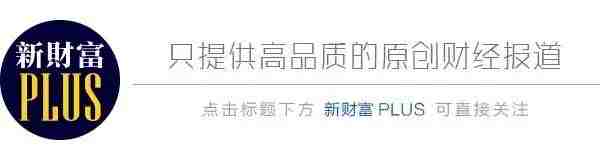
作者:张巍来源:xcfplus
“小燕子”这下挨了板子,不过下板子的不是哪个嬷嬷,而是证监会。昨日,证监会下达的处罚通知将“小燕子”赵薇和她的夫婿、公司,乃至交易对家一网打尽,最引人注目的大概是5年的禁入处罚。
根据证监会的处罚通知,大致可梳理出如下几个谴责要点:
1)空壳收购、贸然公告;
2)筹资安排虚假记载、重大遗漏;
3)融资失败、披露过迟;
4)银行拒绝融资后龙薇传媒的行动记载失实;
5)高杠杆、多变化。
借着明星夫妇受罚的热乎劲,今天就来谈谈股权收购的相关法律问题,特别是信息披露问题——证监会下板子的缘由。
01
法理解析:股权转让要不要披露?
上市公司的股东转让自己的股票是不是需要向公众披露?这问题大概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回答:转让前与转让后,大股东与普通股东。两两相交,也就是有四种情形。
首先,上市普通股东转让自己的股票,无论在转让之前还是在转让之后,都没有必要向公众披露,这几乎可称是常识。背后的道理也很简单,个人处分自己的财产,与他人无涉,也不必向他人报告,这是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好比我卖掉家里的旧沙发,无论在签下出卖协议之后,完成买卖之前,还是在正式卖掉之后,都没有必要向他人公开这笔交易——包括沙发厂和它的股东们。
其次,对于大股东买卖股票的披露问题,形式上又可以对大股东作进一步区分——具有实际控制权的股东,以及不具有实际控制权却符合大额持股信息披露规定的股东,前者是公司的内部人士,后者本质上依然是公司的外部投资人。不过,从实际持股比例上看,前者一般都会包含在后者之中。
第一类大股东——控股股东——由于是公司的内部人士,可能掌握比外部投资人更多的信息,因此,其股票交易状况即便不违反内幕交易规则,也会反映出其对公司价值变化的认识。而内部人士的这种认识无疑对完善市场信息,帮助外部投资人作出交易判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法律通常要求这类股东对其股份变化情况作出披露。比如,美国SEC要求持股10%以上的大股东在其股权交易完成之后两个交易日内作出披露(Form 4)。
不过,即便对于这第一类股东的股权转让交易,法律也只是要求其在交易实际完成之后方才作出披露,而不要求将尚未完成的交易计划公之于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股东归根结底也是市场上的投资人,而投资就要自担风险,原则上投资人没有必要去保护其他投资人的利益,或者说,投资人之间并不负有忠慎义务(fiduciary duty)。
在不违反内幕交易规则的前提下,控股股东交易自己的股票也不过是基于自身的主观判断——而非隐蔽的客观事实。而将未完成的交易计划披露出来,造成股价波动,有可能影响交易成功的概率,从而损害控股股东的利益。比如披露之后股价下跌,购买方就有可能变卦。于是,作为对外部投资人信息需求与控股股东私有产权保护的平衡,法律通常不要求将尚未完成的股权转让计划披露出来。
这一点在美国较为明确,而中国的监管规则却持不同立场。《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14条却要求将拟议中导致一方持股超过5%的股份转让协议也披露出来。上市公司的其他投资人或许能因此提早得到股权转让的信息,但对转让方而言却加重了负担。实际上,由于拟议中的转让是一项不确定事件,因此,在对此信息的处理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不确定的风险。这对于经验丰富的机构投资人来说,也许不是难事,而对缺乏经验的散户投资人来说,却可能错误理解“拟议转让”的含意,徒增困惑。当然,若在机构投资人占主体的市场中,这种披露要求也许总体而言对市场效率仍然有益。
最后,对于第二类大股东,也就是持股比例较大的外部投资人,由于他们并不占有内部信息,原本并没有对外披露其持股变化的必要。只是对于其中一部分有意实施收购的投资人而言,要求其披露持股信息有助于提前让目标公司及其他股东做好准备,避免收购措不及防地袭来,造成对其他股东的压迫。这才有了大额持股信息披露的义务,而对于没有收购意图的大额持股者,法律的披露要求也会相应降低(比如美国13D与13G披露的不同规则,参见笔者所著《资本的规则》第三十六节)。当然,假如对第一类大股东都不要求其披露转让计划,对这第二类股东的披露就更该限于实际完成股权交易之后了。
综合起来看,第一,通常股东都没有将其尚未完成的股权交易计划进行披露的义务,但在中国,协议转让5%以上股份的股东却有义务将尚未完成的转让交易披露出来;第二,大额持股股东有义务按照大额持股披露规则,对已完成的股权交易的结果加以披露,而根据持股比例和持股意图的不同,披露的具体要求也不同(例如,除了13D和13G披露规则的区别之外,美国法律不要求持股在5%到10%之间的股东履行Form 4的披露义务),这方面目前中国的规则尚未作有效区分;第三,普通股东无论在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前还是完成后,都没有披露的义务。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上面说的都是股东自己实施的交易,而不是上市公司实施的交易。与作为公司投资人的股东不同,公司本身就是为全体股东利益服务的实体,除此之外别无其应当独立谋求的利益,所以,对于上市公司实施的交易,比如资产买卖、公司并购,如果对股价变化可能造成实质影响,就可能需要披露——即便交易尚未完成。
然而,即便针对公司的交易,也不一定要求一旦有了交易计划就要披露。这是因为交易确定之前过早披露信息,反而有可能影响交易成功的概率,给股东造成损害。因此,美国最高法院在有关上市公司并购信息披露的著名判决Basic, Inc. v. Levinson中表示,上市公司没有必要仅仅因为信息具有重要性(materiality),就肩负其将尚未确定的并购交易磋商情况公之于众的义务。不过,由于该案刻意回避上市公司何时需要作出此类披露的问题,所以,目前美国的法律对于尚未达成确定协议的并购交易何时需要披露仍没有统一的规则。
02
法律责任:主动披露有何后果?
假如本没有披露股权转让计划、方案或者合同义务的股东主动披露了这些信息,后果又将如何呢?
先说股东可不可以主动披露尚未完成的股权转让交易。既然不作披露是股东享有的权利,那么,只要法律没有明确禁止,股东就可以自行选择放弃权利,主动披露相关信息。即使转让方案尚不确定——包括受让方的资金来源还没有着落,也不应妨碍股东披露现有计划。在交易完成之前披露交易信息,有可能影响交易成功的概率。不过,由于股东转让自己的股权并不以公司或者其他股东作为交易一方,交易成功概率的变化,只会影响到转让股权的股东,而与公司的其他投资人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对这些投资人而言,将交易信息提早披露出来并无不利,却只会增加市场的信息,有利于他们作出投资决策。
这与以公司或者其股东作为交易对手的并购颇不相同,因为一旦过早披露信息降低了交易的成功概率,那么,目标方的股东就可能直接遭受损害。不过,就是在公司并购的场合,法律一般也不限制交易方的主动披露——纵然交易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因为只要没有强制披露义务,何时将交易披露出来本质上属于一项商业判断。例如,美国上市公司收购协议中包含不确定条件——包括融资条件——的例子比比皆是;英国的收购条例(Takeover Code)更要求上市公司在出现市场传言之时就作出相应披露,而不必等待收购交易诸事确定之后再行披露。
然而,一旦作出披露,那么,无论是控股股东还是上市公司就都有义务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假如出现“重大”失实,作出披露者就可能要面临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在此,追究披露者责任的一个重要限制是不实陈述的“重大性”。对“重大”与否的判断自然离不开特定的场景和特定的事实,不过,作为一条基本原则,美国最高法院在TSC Industries, Inc. v.Northway, Inc.的判决中指出,判断“重大”与否,取决于合理的投资人是不是会认为相关的虚假陈述将“严重改变整体的信息背景”。
除却纯粹的虚假陈述之外,股东主动作出的披露还可能欲言又止,说一半,又藏一半。那么,对于藏起来的一半又当如何处置呢?法律上这便是监管信息披露中重大遗漏(omission)的问题。在此,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法律从不要求上市公司将其所有的重大信息悉数加以披露,因此,重大遗漏肯定不简单等同于没有披露“重大信息”。比方说,可口可乐的配方当然是有关可口可乐公司的重大信息,但没有任何合理的法律会要求可口可乐公司披露这种配方。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证券交易法》明确指出,违法的遗漏仅指“没有披露为确保已披露事实根据披露的具体情况,不致产生误导的重大事实”。换言之,主动说出一半事实的人就有义务把另一半也说出来(Choi & Pritchard, SecuritiesRegulation: Essentials, Aspen 2008)。因此,有没有重大遗漏,不能只看遗漏的事实本身是否重大,还要取决于未披露的事实与已披露事实的关系,只有前者令后者失真,造成误导之时,方才构成重大遗漏。从这个角度看,主动披露信息者是自己给自己蒙上了一层负担重大遗漏责任的阴影。
有关股东的主动披露,还有必要说明的是其是否会构成操纵市场。或许有人认为,股东有意选择特定时机披露特定信息,从而造成股价变化,再趁机交易谋得私利。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对操纵市场的内涵颇有误解。操纵者,本质在于扭曲由供求关系形成的市场价格,因此,操纵是指造成某种假象,迷惑市场参与者,使其作出错误的供求决定。换言之,操纵的核心是无中生有,与虚假陈述一样属于弄虚作假,只不过作假的手段不假于言辞,而是以交易行为来实现。
从这个角度分析,只要股东主动披露的信息不含虚假,那即便由此引发价格变化,同样是出于真实的市场供求,操纵便无从说起。就好比前日博通发布信息有意收购高通,市场顺势反应,此后即便买卖高通的股票,也绝无操纵市场可言。简言之,证券市场上利用信息实施的违规行为,要么是胡说八道,欺骗市场,那就是虚假陈述;要么是闷声不响,中饱私囊,那就是内幕交易。于是,既非虚假陈述,又够不上内幕交易的股东主动披露股权转让信息,要被认定为操纵市场,着实不知从何说起。
03
案例解剖:证监会的板子打得对不对?
理顺了法律的来龙去脉,再回头看证监会此番对赵薇等人的处罚是否恰当。
谴责一:空壳收购、贸然公告
证监会的第一项指摘是,赵薇夫妇旗下的龙薇传媒在资金不确定的情况下,“以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且贸然予以公告,对市场和投资者产生严重误导”。这一指控不得不说十分令人费解。上文已经详加说明,即便控股股东在完成股权转让之前没有义务披露相关交易计划(譬如美国法的规则),也不妨碍股东主动对此加以披露,尤其是披露业已达成的确定的股份转让协议。这种主动披露无从构成操纵市场,因此,只要不涉及虚假陈述,披露者就不应被追究责任。
而在中国,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原本就要求股东就协议转让5%以上的股份作出公告,而且公告的时间并不待转让实际完成。再者,《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既未禁止空壳公司进行公告,也没有要求只有收购资金确定之后才得公告。所以,龙薇传媒及其交易对手公告达成转让协议的行为,完全是履行监管规则要求的义务,又何来“贸然”之说?
假如脱离公告的具体内容,单就公告行为本身便可认定其误导市场,那岂非让按监管要求实施披露的人员都可能陷入误导市场的深渊?既然法规要求披露,那么,只要法规不误导市场,按要求实施披露这一行为本身就不可能误导市场,要追究误导市场的责任只有在考察了具体的披露内容之后。否则,岂不是成了“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第一板,看来是打错了地方。
谴责二:筹资安排虚假记载、重大遗漏
证监会的第二项指摘,主要针对2017年1月12日龙薇传媒在答复上交所问询函中有关收购资金来源的陈述。将尚未完成的交易公开披露给投资人——无论出于主动还是法律要求——都无可避免地为投资人增添了评估交易实现可能性的需求。而投资人要准确作出评估,就有必要掌握交易方的融资安排,因为资金能否到位无疑是影响交易成功概率的关键因素。为此,有关尚未完成的股权转让交易,其融资条件就不能不说是一项“重大”事实。
由于龙薇传媒在1月12日的信息披露中的确未能如实陈述其实际进行的融资努力,也没有披露其时融资计划实施的进度,更没有如实说明金融机构融资与银必信借款之间的关系,投资人无从有效估测交易实际完成的可能性。所以,不能不说这一份信息披露文件存在重大的不实陈述与重大遗漏,证监会的这一板看来打得不偏不倚。
谴责三:融资失败、披露过迟
证监会的第三项指摘是,龙薇传媒于1月20日得知银行无法提供贷款之后,迟至2月16日才将此信息发布。从知悉到披露整整花了27天,就算除去期间春节放假一周,也足足耗费20天。对于融资失败这等有关交易确定性的信息披露如此拖沓也着实难言符合“及时”披露的要求,看来证监会的这一板也打得准。
另外,有关2月16日公告中将无法完成融资的原因单方面归于银行贷款审批未通过,却未提及银必信也没有准备足够资金这一点,确属遗漏无疑。由于1月12日的公告表示银必信与银行将提供基本数量相当的收购资金,因此,仅披露一处融资失败,却隐藏另一处融资同样出现问题,可能令投资人错误寄希望于另一家提供资金规模相当的融资方。这一遗漏似乎也符合“重大”的标准,证监会的指摘不无道理。
谴责四:银行拒绝融资后龙薇传媒的行动记载失实
证监会的第四项指摘是,1月12日与2月16日两次公告均提及如未能取得金融机构融资,龙薇传媒将积极采取行动,与股权出售方及其他银行进行沟通,而这与融资失败后龙薇传媒的实际行动不一致,因而属于虚假记载。对于1月12日的公告,当时龙薇传媒尚不知银行融资失败,因此,其有关失败之后如何行事的叙述不过是针对未来事件的一个承诺,而谈不上对既有事实的不实记载。
至于2月16日公告中的有关内容,尽管可以说记载失实,却未必达到“重大”的程度。一个合理的投资人更多关注的是行动的效果,而未必是行动本身。既然结果是没能取得融资,那收购方此前是否作过努力对投资人来说就无甚紧要了,因为这种信息对于判断交易成功的概率并没有多少作用。就市场的实际表现看,2月16日复牌之后,万家文化股价已呈一跌再跌之势,看来投资人已经充分明了融资失败的含义了。如果从以上两个方面看,证监会的这一板好像是打偏了,或者有些多余。
谴责五:高杠杆、多变化
在列明龙薇传媒披露行为以及具体披露内容的违规之后,证监会又以批评的口吻指出龙薇传媒此次收购交易采用极高的杠杆比例,以及在短时期内多次变更股权转让方案,及至最后终止股权转让,而双方未追究违约责任。尽管证监会未能说出这些行为违反了那些法律法规,但显然认为它们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信心”。
杠杆收购本身亦正亦邪。一方面,高杠杆无疑加大了收购的风险,并因而增加被收购方破产的危险;但另一方面,杠杆收购也有利于挤出收购方的自由现金流,有助于克服代理人成本问题(Jensen)。归根结底,杠杆收购不过是一种交易方式,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假如被收购方认为收购方杠杆过高,影响交易的确定性,或者会对收购完成后被收购的资产造成严重风险,便可以拒绝高杠杆的收购方。而向收购方提供贷款的机构自然也会权衡杠杆比例与还贷风险,从而拒绝过度的杠杆贷款。实际上,龙薇传媒的融资方就都没有接受提供融资的请求,因而所谓的51倍杠杆,实际不过是一句空话。
至于收购方案多次变化,以及双方放弃追究违约责任则更是交易方行使其民事权利的表现——变更合同与放弃违约请求都是市场经济中交易主体的基本权利。当然,如果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自然可依《合同法》相关规定追究责任,但除此而外,第三方——包括行政机关——无权对交易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横加干涉。
假如承认交易当事人有变更合同的权利,那么,其依规变更公告的行为也就理所当然,倘若交易变了,信息披露不变,那倒真的成了违规。实际上,监管规则既然要求提前披露尚未完成的交易,就必然要容忍披露信息的屡屡变化,因为未完成的交易原本就不确定,就多变。其实,与当年安邦与万豪争夺喜达屋的竞购大战相比,万家文化的这几番公告变更恐怕还真是小巫见大巫呢。
这样来看,若是证监会再想以高杠杆、多变化为由加重板子,还真有点打错了地方的意思。处罚决定所谓“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信心”,更像一句追究责任的套话。既然这些行为只是“造成万家文化股价大幅波动”,那又如何影响了“市场”的秩序?而所谓中小投资者的信心,受损的恐怕也只是对万家文化的信心罢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意见,本公众号发布此文仅出于传播更多观点之目的)

原创内容,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如需转载,请联系小编(微信:weiskywalker)

过往文章: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