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大文学家张恨水孙女,母亲为不让其捡粪种田,送其走上学医之路….
平均阅读时长为 8分钟



【版权文字,未经授权禁止商业转载】

张进,中国现代文学大家张恨水的孙女,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喜欢数学和物理。在那个人人都要下乡或被派往三线建工厂的艰苦岁月里,历经艰辛的母亲不想让独生女再受苦,加上看到医务室里的医生无论如何都不会去捡粪种田,因此高考时决定让女儿学医。正因为如此,张进报考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儿童医院做医生,之后又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在39岁那年,将医生视为自己事业的她又义无反顾地重返校园读医学博士。一晃15年,她在自己选择的从医之路上亦苦亦甜地前行着,而这一切都源于她的初心不改和执着。
本周,我们来一起听听她的故事——
白
1

我出生在北京,于西四的砖塔胡同长大,那里有爷爷的宅子。在我很小时父母被下放到农村,之后又转往湖北荆门市搞三线建设,我留在爷爷的宅子里。但那时文革已开始,家里不能请人照顾了,我就被送到离爷爷家不远的李奶奶家,父母每月付给李奶奶15元钱,让他们照顾我。
那时,爷爷得了中风,但因没人照顾,生活也很凄凉。1967年爷爷过世,那时我只有几岁,除了对爷爷的院子、书柜和茶碗等还有印象外,其他没有任何记忆了。

幼时的张进和爷爷张恨水等亲人在一起。
我从小觉得自己家和别人不太一样,也不太喜欢。而我又是在李奶奶家、一个穷人家长大,自小我就把李奶奶家当成自己的家,因此那种心态一直很复杂,而这种心态一直延续到我上了大学。有一天一位同学在宿舍里聊天,说她在马路上看到报贩吆喝说:看报,看报,鸳鸯蝴蝶派代表张恨水!那时我突然忍不住地说道:张恨水是我爷爷,他不是什么鸳鸯蝴蝶派代表!
多少年来我一直不喜欢听别人说爷爷是鸳鸯蝴蝶派,认为这不够革命,因此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现在年纪大了,回头想想也无所谓了,究竟什么派,那都是研究人员做的分类罢了。
我在北京读完小学三年级,又到了父母三线厂所在的湖北荆门市。那时当地教育水平落后,我直接上了初一。因为年纪和个头都是班里最小的,因此老受欺负,捡粪时也捡不过人家,总是到了最后一拨才能当上红小兵、红卫兵。
转眼到了高考时。我的父亲张二水当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清华大学石油冶炼系,一年后该系从清华分出,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的前身),父亲后来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

张进和爸爸张二水在一起。
因为父亲学的是工科,从小他和我讨论的都是数学和物理,我从小也喜欢数理化。高考报志愿时父亲想让我和他学相似的专业,但母亲不同意,说一定要给我找个今后有饭吃但不用受苦的工作。在干校时种水稻、捡粪、拉钢筋等重体力活都干过的母亲,见到医务室里的医生却不用去捡粪种田,就说让张进学医吧。
那时北京有北京医学院和北京第二医学院,前者毕业后全国分配,后者北京分配。好不容易从三线厂回到北京的父母舍不得让我离开北京,因此让我选择了北二医。
1982年我进入北二医儿科系学习了5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北京儿童医院的耳鼻喉科,在那里工作了2年,这对我一生影响特别大。
那年我才23岁多,尽管很年轻,但因为儿童医院每天来求诊的人特别多,因此就特别忙,我一天要看50个病人,有时一天要做20个扁桃体切除手术。那时全国唇裂儿童都被送到北京儿童医院,我所在科室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缝合唇裂。尽管自己不是主刀仅是助理,但通过观察,以及偶尔动手做手术,让自己的缝合技术等得到很好地锻炼并受益至今。

张进医生在北京举行的高峰论坛上做报告。
当时很多病患都不喜欢看年轻医生,一些医生也不喜欢看小孩。但有位家长带着儿子来看病时一直找我诊治。那位家长说,尽管你年轻,但长得顺溜面善,我信任你。这些让我到今天都记得,也给了自己很大鼓励。
在儿童医院做医生的经历至今难忘,那时科主任还带着我和其他年轻医生到内蒙古做手术,给了我很多荣誉,到今天我都忘不了。
我和孙澜涛结婚后,当时还在中国文化部工作的他被派到纽约中领馆,我则通过留学来到了美国,在纽约史坦顿岛上一个学院读生物。因为没钱我也四处打工,不仅在洗衣店工作过,每周只挣50元,还帮人家看过孩子。
后来有位同学建议我到哥大公共卫生学院读研,说在实验室做助教可免学费。经过一番辛苦,我考上了哥大。2年后硕士毕业,我也顺利地在纽约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实验室找到工作。
在实验室里我做研究员,和瓶瓶罐罐打交道近10年。这10年里我的儿子小虎出生,澜涛也攻读完法学博士。但10年来做医生的愿望依旧在我内心强烈地存在着,觉得实验室的工作根本不是自己的人生目标。39岁时,我决定重返校园实现自己继续当医生的梦想。
在美国考医生其实有两条途径,一种是直接考医生,按照“三部曲”一步一步地考执照,然后再去做住院医生。但我大学时学的是儿科,加之对美国医疗系统也不了解,于是在39岁时考进纽约科技大学医学院开始攻读医学博士。
重返校园的第一堂课就让我很难忘:教你握手,即当做为医生的你走进诊室向病人介绍自己时,如何和病人握手。一般中国女人握手时仅会伸出几个手指头尖让人握,以展现自己的妖娆和矜持。但老师告诉我们握手时必须把整个手伸到对方手掌中,且要用力握,以展现你的真诚。
考试时还有“见病人”的考试,学校请来一些演员扮演各种病人,这些病人会把你见他们时的表现一一打分,同时学校还把你的表现录下来让你看。这些课程是我在北二医上学时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事。
4年的博士学习可以说是非常艰难和痛苦。我重返校园时儿子才五岁,每天都是丈夫接送他,那时所有的活动和聚会我都不参加,每天就是上学、考试、读书。
有次独立日假日,澜涛带着儿子去参加派对,我一人留在家中苦读书。突然间我感觉自己崩溃了,2、3个小时都念不下去,像病了一样。我忍不住给住在华盛顿的大姑打了电话,她劝了我许久。还有一次在学校里考试,一位老师批评了我,我跑到厕所里狂哭起来,泣不成声。
回想起这4年的学习,的确辛苦,但也值得,它让我了解了美中医学的差别,也掌握了美国的医疗知识、理念和方式。若没有这4年的学习,也就没有今天我给各族裔病患看病时的自信。

张进和丈夫孙澜涛带着儿子访问爷爷的故居。
博士毕业后,我到位于Far Rockaway的圣约翰主教医院做住院医生,一切从头做起。在美国,住院医生是地位最低的医生,尤其第一年里最辛苦,给你最多的值班,最多的夜班,在高压下培训你。
那时我老值夜班,早晨9点下夜班,晚上7点又要赶回医院值班,全是澜涛接送孩子。为了能看孩子,早晨下班后我赶紧回到家,将儿子送到学校,再睡几个小时,起来为父子俩准备点吃的,又返回医院。每天都是这么风风火火的,也忘了什么是女人,甚至连女人怎么乐、怎么打扮都忘了。
那时我当年的大学同学,有的在国内当了院长,有的做了教授,有的成了名医和博导,但我却从头做起,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想不开,跟自己过不去!但一看到病人要抢救,看到那些孤独的老人,也就没时间去想这些了,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张进医生和同事们。(本文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张进提供)
经过3年的住院医生培训,从2009年起我开始了执业医生的生涯。最初我在贝赛的一家诊所工作,2年多后这家诊所的老板因为离婚官司而关了门。我又被猎头挖到做快速诊疗的连锁医疗机构UMD做医生,在它位于曼哈顿联合广场的诊所里工作,接触的病患99%都是年轻的白人。
有次诊所来了一位金发碧眼的帅哥说他脖子不能动了,诊治后我发现是落枕了,便给他打了封闭针。之后帅哥又向我要医生证明说明他今天无法做Gym,我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他是模特,每天必须做Gym。等病人走了,我和护士赶紧在Google上查看,发现该人是从欧洲来的一个知名大模特。
我在UMD做了4年,因诊所所在地区有很多同性恋,由此也对同性恋文化有了深刻了解。去年7月,我应邀参加了北京儿童医院主办的“2016内分泌遗传代谢疾病及性腺疾病高峰论坛”,为大家介绍了“纽约社区变性者/同性恋常见疾病及问题处理”,和同行做了交流。
2016年12月,我想独立开业的想法终于开始付诸实施,从选址到装修诊所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尽管诊所不大,但被病人比喻为像让人放松的SPA。这的确是我的初衷,希望能按自己满意的方式建诊所,让它成为和病人们讨论治病方案及当今健康生活方式的地方。
我的诊所尚在试营业中,去年12月法拉盛快捷诊疗中心开张了,我被聘为医学总监。尽管快速诊疗在纽约已不少,但在华社还是新生事物,之前自己从事快速诊疗多年,经验丰富,加上又能让自己的缝合技术等大展拳脚,因此很喜欢在这里工作。
屈指计算,我在美国从医之路已有15年。虽然从39岁时重新起步,但回想起来一点也不后悔。若当初我没有重新回到医学院做医生,我想我会后悔终生。
记得有次别人问我:谁对你影响最大?儿子替我回答道your patient!是的,到今天我都难忘一个病人。
博士毕业后我在第一个诊所工作时遇到过一位病患,他的脸部有些疤痕。寒暄后,我看了他的化验报告发现他的胆固醇有些高,于是建议他做些运动。他说,我现在终于敢骑自行车了,我问为什么?他和我聊了起来。原来在他20多岁时的那个人生最糟糕时刻:妻子和他离了婚,工作也丢了,他骑着摩托车上了495高速路,一辆车撞上了他,从他戴着头盔的脸上压了过去。在医院救治3个月后他出了院,和朋友去超市买东西时一个小女孩见到他后大哭起来。回到家他看到镜中的自己,顿失生活的勇气,几次想自杀,但被人们送到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20年来,他前后接受了十几次手术,才有了今天的模样,现在也才敢上街骑自行车。
听完他的经历,我告诉他应该为今天拥有的东西感到特别骄傲。他的泪水流了下来,我也被他的坚强所感动,他也让我感受到做医生的价值和意义。
当然,这些年我的付出也很多,甚至连家庭生活和婚姻都受到影响,但我不后悔,因为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学习和成长。我又回到了诊室,做回我喜欢的医生,别管给哪个族裔看病,我一点也不后悔。
编辑: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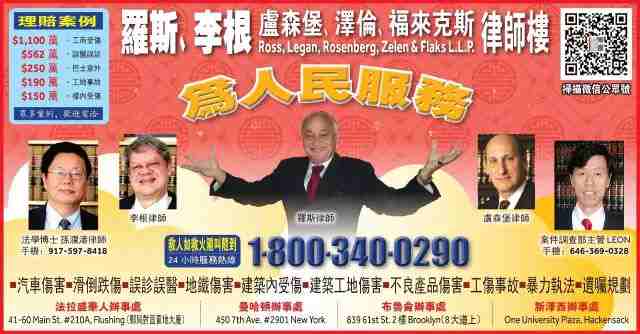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