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之后,成名之前


在纽约的夜晚,游人最喜欢逛的是时代广场。
从五大道的第42街拐进去直走,第一刹那闯入人眼帘的就是二十四小时滚动的LED屏,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永不畅通的车流。时代广场的这一片繁华正茂,在大约一百年前曾是歌舞剧院的天下。那个时候,看剧是一件高雅的事儿,而“百老汇”这个名字也因此打响了名声。
传统意义上的“百老汇”在地理上可以这样定位:从曼哈顿区西41街的Nederlander Theater往北至53街的Broadway Theater。这一片区域内的所有剧院都是百老汇旗下的,共计38个剧院,100多个舞蹈团,将近60个乐团。每一个夜晚,这里都歌舞升平。游客会花40美元到150美元买一张门票,坐在19世纪修筑好的剧院里看表演。
这就是纽约百老汇,是每个戏剧演员都渴望踏入的殿堂。

现状
今年刚刚毕业的刘冠谷是一名戏剧演员。他来自台湾,见面时给人的印象很普通,扎着短马尾,穿着休闲,中等个子。乍一看,并不像学表演的。他私下的确有另一个身份,纽约一家中餐馆的服务员。
跟人介绍时,冠谷都会说“哦,我是一名演员。” 如果又问演过什么,他会毫不含糊地说出一堆“闻所未闻”的剧名。冠谷不觉得难堪,但谁又知道对方在期待什么呢。
一般演员最爱考虑的问题就是成名,但冠谷想,30岁之后再考虑走红的问题吧,目前他只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份工作薪水不必太高,能让他每天吃一顿十五美元的午餐,付得起一个月九百刀的房租就够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冠谷曾努力地找过一些大公司试镜,当然也包括百老汇的。
在试镜的这一天,冠谷会在早晨七点起床,八点半赶到面试地点,向工作人员提交证件照、简历和要表演的两个片段。每一次面试的人都很多,冠谷常常排队到一点,中途吃个饭再回来继续等。这份“无所事事”的等待会持续到下午两点半,没排到的演员会被毫不留情地告知“下次再来”。冠谷曾经幸运地排进过,但没有一次接到面试官复试的电话。后来他才知道,百老汇的面试才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
“几个月前我和朋友聊天才知道,其实这些试镜都是内定的,只是美国工会要求必须有流程而已。说白了,我们就是陪衬品。人家导演要是早就想好了这个角色要谁演,其他面试的人无论再怎么表现良好,都不可能有机会。”
冠谷本身并不擅长跳舞唱歌,不适合演音乐剧,于是他放弃了试镜百老汇,继续开始打黑工攒钱、准备签证、网上投简历却永远“石沉大海”的日子。他不管这些经历叫“付出”,他说这是“基本”:“大家20-30岁时都这样,但这才不是最煎熬的,最受打压的是你根本不知道下一站在哪儿,精神层面的。”
“不过O1(在美艺术从业人员签证)签证快有消息了,很快就知道答案了。”
在这些人中,小佩比较幸运。今年六月的时候,她抽到了H1B(特殊/临时工作人员)的工作签证,在将近二十三万的申请人群里,成为了那幸运的百分之三十(总申请人数大约八点五万人)。她说,“哇,我的天,感觉自己被流星砸中了。”

今年25岁的小佩和笔者通话时还在老家重庆。她的这份签证申请是为了回美国继续跟着杜克大学的表演系教授工作。在教授的剧团里,小佩做导演也做演员,后来因为干得不错且是整个剧团里唯一的中国人,教授愿意为小佩提供需要的合同、推荐信之类的文件。万事具备,小佩找到一家美国华人律师公司,准备签证。
刚开始申请时没那么顺利,小佩感觉自己受到了律师公司的歧视。“你们这样的人就是美国现在最不需要的人,创造的价值又少,又没有直接的经济回报,也不是做technology的。美国总统现在要赶走的就是你们这样的人。你要是有几个钱,想申就申吧,反正也抽不中。”
被归为“这样的人”的小佩给律师交了7000美金的申请费,后来发现自己差点被骗。她吐槽:“其实申请签证真的很简单,律师那边要做的工作就是填写一些资料。但是客户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啊,他在后面做什么鬼动作,你都无从知晓。”后来,幸亏学法律的朋友一个电话打过去,把对方质问得“问什么答不出什么”,公司这才给小佩换了律师。
小佩本科在波士顿大学读的是哲学,因为家人好像一直对艺术行业有些偏见,觉得没前途,所以阻止了小佩本科报考表演系的决定。
后来毕业,小佩收到了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实习机会,妈妈百般调侃,“哦呦,不用带那么多东西啦,反正过几天就回来了。”谁知,小佩一走,就再也没回来过。

在北京的那段日子是难熬的。小佩带着满满的激情来到国家大剧院,却突然发现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每天一上班就是开大会,听领导讲述自己欣赏的作品和价值观念。开完大会就要在办公室里端水、擦桌子、收快递。有时,小佩和同事们有了新想法,就得“求爷爷告奶奶”地和领导约时间面谈。小佩偶尔也会跟着演员们一起排练些历史正剧,她经常听见导演说:“啊,这个人物她此刻是十分悲伤的,你的眼泪要这么哗啦啦得流才行。” 小佩渐渐意识到,在这里演戏, 一颦一笑都要遵从指挥,太没劲,于是心想,“woc,我还年轻,我要做事儿。”
她动了离开这里的心思,六点下班后就跑到北京各种艺术工作坊学习表演,晚上再精疲力竭地奔波回月租3000元的小屋。由于实习没有工资,小佩为了能负担一些工作坊的学费便接了很多翻译的小工作。她整日都往返在地铁上,盯着黑色玻璃窗上自己的影子,思考未来该做什么。
生活
这几年,冠谷一共演了十几部话剧,最满意的一部作品是哥伦比亚大学青瓷戏剧社的 《 A Beautiful Country》,讲述了各行各业的华裔在海外打拼的故事。这家名叫“青瓷”的戏剧社成立于2014年,今年的社长是Alex,一名热衷戏剧多年、哥大哲学系的大三在校生。和Alex一样,《A Beautiful Country》的大多数演员都不是科班出身,有的只是爱好戏剧的新手。尽管如此,Alex很肯定的说,他们的戏已经尽力做到准百老汇的灯光舞美标准,至少是学生社团里最专业的;演员们也都很靠谱,像冠谷,“真的是那种很想做一个专业演员的人,不是大家所谓的‘明星’ 。”
冠谷之所以要演这部戏是因为它的主题,他说:“虽然没有片酬,但这部戏的内容是我最满意的。我还是对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剧比较感兴趣,尤其是跟Asian American相关的故事。我总觉得既然要演戏,为什么不演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故事呢,毕竟我还年轻。”
为了排这部戏,冠谷翘掉了晚上打工的时间,一直排练到半夜十二点多回家,再接着准备签证的资料。不仅没有片酬,甚至有时团里没钱还要大家伙筹钱支援,冠谷没办法,经济紧张时就必须在打工的店里解决伙食,省点饭钱。
历经艰难的两个月后,《A Beautiful Country》于四月在哥大一个剧场上映了三天,冠谷作为主要演员戏份挺多。他演戏时很有张力,光脚穿梭在舞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造型很“缭乱”,台词不多,但眼神总是亮晶晶的,像另一个世界的人。上映的三天里,能容纳将近一百人的观众席日日坐满,总计300多人的票房,Alex很高兴,说这是华人戏剧社里比较高的票房了,他也终于有钱缴纳场地租赁费了。

《A Beautiful Country》海报
和冠谷不同,小佩周围学表演的朋友们毕业后就回了国。由于纯戏剧的舞台太少,大家都开始陆陆续续地演网剧、上综艺,接商业活动。渐渐的,朋友们发现,中国的表演相较于国外落后了很多,大部分海外已经淘汰的技巧,国内仍在使用。大家都说,留学的经历好像并没有给他们加分,一切还是要从零开始,学习最传统的表演,似乎倒退着走了。
一旦离开了学校就好像失去了维护单纯世界的保护伞,所有的东西都在一瞬间扑面而来,让人招架不住。现实教会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们,什么叫做妥协,什么叫做“不得不”。朋友圈里渐渐开始有一些小广告:某相亲节目现招募嘉宾,相貌佳即可,每期5000元。综艺节目里,最高的,三四天可以赚六万,而一集剧情再烂的网剧,片酬也可以达到几千块。甚至有人为了适应这个系统,被公司逼去整容。
在生计面前,大家都放弃了负隅顽抗。

梦想
在北京待了一年多后,小佩去了上海一家艺术工作坊上课,她就是在那里认识了杜克大学的教授,Jaybird O’Berski。那一周的工作坊彻彻底底颠覆了小佩对表演的认识。具体的技巧倒没教多少,但老师让小佩感受到了什么是用心表演,什么是搭档之间的互与助。一周的训练结束后,小佩左思右想,最终决定以visiting的身份,跟教授到美国杜克大学学习。
杜克大学的氛围让小佩觉得舒适。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国际生,周围人的友好让她逐渐放下了戒备。她也在那时演了自己的第一部话剧,《玩偶之家》的一个片段。她扮演年老的女主人公娜拉,结尾时,死在丈夫海尔茂的怀里。那是一个很短的片段,但小佩和男演员搭档得很好。她闭着眼睛,认真听海尔茂低声歌唱,眼角流着泪,好像真的变成了娜拉。配乐结束,娜拉和海尔茂都没反应过来,直到观众的掌声响起,她们才起身,擦干眼泪,鞠躬下台。小佩记得,周围的很多朋友老师到现在都还常常说起这场戏。
后来的日子愈加顺风顺水,每天起床后,小佩都觉得自己充满了干劲儿。一条鱼,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水域。

对于未来,小佩没有具体想过。她现在每个月能拿的工资不多,一部剧顶多挣500美金,最差的时候只有100美元。日常生活需要靠每年暑假回国打工、开艺术工作坊支撑。想要“买买买”时,就不得不靠家长接济。尽管如此,小佩也没想过换一个大城市打拼。周围同学都去了纽约,觉得机会多一点,兴许能多点收入。但小佩不想,在她眼里,纽约不是谁都适合去的地方。
“去的城市大不大无所谓,重要的是和一帮人合拍。我觉得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应该和他所在的平台匹配才对。而我现在还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所以不想到纽约这个大地方,变成一滴小水珠。”
冠谷对于未来的目标更具体一些。他说:“我的梦想就是将来有一天能拿Oscar的最佳男演员,可是亚洲演员在美国圈里真的很难混。你说Jackie Chan为什么这么火?因为他会武功啊!所以美国人只有需要那种会功夫或者戴着眼镜呆呆的角色时,才会想到中国人。但是我不干,我不愿意被束缚在这样的框架里。”
采访的时候,冠谷还在面馆打工。晚上下班后,他要赶回家准备签证的资料。他打算在这里留下几年,找份正经工作,尽快摆脱打黑工的日子。母亲说,不如回台湾,一边打工,一边等待机会,但冠谷还在犹豫。他心里有个东西,被现实深深地埋着,却又挣脱着要破土而出。
他和所有在纽约生活的人一样,为了某种目的而来,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方向。这个城市是快的,没有时间让你冷静思考,麻木了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就像你在街上叫住一个人,对方突然停下、抬头,满眼茫然和疑惑。你问他,“忙什么呢?”他会瞪你一眼,留下一个冷漠的后脑勺离开。

日子忙忙碌碌的,总感觉黑白颠倒。有时在餐厅忙着给客人上菜,冠谷会突然忘了自己来纽约的初心。幸而这个时候,餐厅的伙计会突然拍一下他的肩,“嘿,赶紧干活,别忘了下班去排练。”


作者:秦之琳
美编:羽晨
图片来自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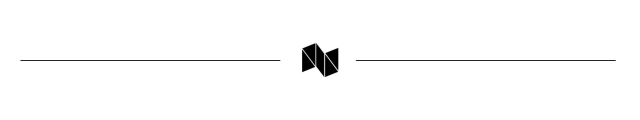
人|故事|經歷|青年態度
北美新媒体平台
N E B U L A R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