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天梯》背后的蔡国强:我这个人还挺能整的

蔡国强今年的一个明星“项目”,是他的首部纪录电影《天梯:蔡国强的艺术》今天在国内院线公映。上海、北京和数十个城市点映后,该片豆瓣评分据说已经到了8.6。
拍摄团队的卡司惊人,再次佐证了蔡国强的国际江湖地位。他在新泽西州的由一个上世纪20年代马场改造的乡间别墅,由当代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亲手打造;而以他为主角的这部纪录片,则请到了奥斯卡金像奖凯文·麦克多纳(Kevin Macdonald)担纲导演。

拍摄历时两年,地理跨度从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上海、北京,从花炮之乡浏阳到蔡的家乡泉州。影片两条线索。伏线是蔡国强的世界,讲述他上世纪80年代从泉州出发,走向上海、东京、纽约,30年来在不同文化间成长,成为享誉全球的爆破艺术家。他在泉州的亲人和朋友悉数都在影片里,就像他们曾经在他世界各地的展览现场上出现过一样。主线是记录蔡国强最新爆破作品《天梯》的创作,影片文案写得非常温情——
“一座500米高的金色焰火梯子嘶吼着拔地而起,与无垠宇宙对话。这是蔡国强少年时代仰望天空、摸云摘星的梦想,20多年来,他在世界不同地方屡试屡败,却从未放弃。2015年6月黎明,泉州小渔村惠屿岛海边,在国内技术专家和当地数百村民的帮助和见证下,他再次一搏,把《天梯》作为献给百岁奶奶和家乡的礼物。”蔡国强实现了他要“放个最厉害的焰火”给奶奶看的梦想。他说,拍摄期间,父亲和奶奶身体就都不好了,后来就去世了。
2015年在中国实现的《天梯》,其实是个累积了数次失败和中止后才完成的作品。辰巳昌利说,一般的艺术工作,大多是由策展人和美术馆员工等艺术相关人员在合作,《天梯》却完全是靠有很多坚信它可以实现的人们一起合作参与而实现的,尽管他作为技术总监20多年来一直也曾对这种实现半信半疑。

蔡国强,《天梯》,2015,实现于惠屿岛海边,福建泉州,6月15日清晨4点45分,历时约100秒;火药、导火线、氦气球,蔡文悠摄,蔡工作室提供
回头看来,之前在国外那么多次的失败,都是对这件作品的成全。只有在泉州,在艺术家真正生长的“母题”(Motif)里,这一把“连接地球和宇宙”的《天梯》才是真正的艺术巨制,而非一场令人惊叹的奇观。
大部分时候,辰巳说,他们的艺术计划很少能在最早的设想状态下实现。“艺术里没有成功或失败。这是我和蔡的共同认知。但这也是自我安慰。实际上我们都不想失败。要谈失败的话,例子多的是:在斯德哥尔摩,水上的导火线中途不断熄灭;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型的中国串联风筝飞不起来;在布里斯本和神户,铁皮小船沉没在河里⋯⋯以作品来讲,无法完成的案例不可枚举。”

蔡国强,《发情山》,2016,火药、画布;共3屏,总尺寸239×450厘米,赵小意摄,蔡工作室提供
由于爆破的不可预测,在做蔡的作品时,不论做了多么齐全的准备,团队都会担心能不能顺利。但作为一起工作了26年的伙伴,辰巳说,他从没有看过蔡露出痛苦的表情。年轻的时候曾有拼命的表情,但年纪大了以后也渐渐没有了。能够镇静地从头开始,对于蔡国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可能因为我和蔡是同年代的人,一直以来有一种很久很久以前就是朋友的错觉。我们的共同点,是长大成人后,仍然希望持续少年时期的梦和玩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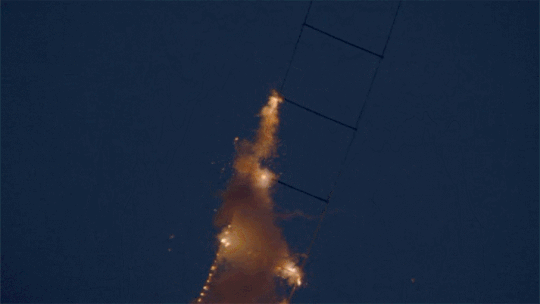
影片中间有个镜头印象很深刻:蔡国强只身走进美国内华达核实验基地,沉默地,以手举起一把点燃的火焰。在白日的炽热和广袤的荒野之中,火焰的光芒如此微弱,但是你很难忘记镜头中那个单薄的背影。一簇微火,比起多年后艺术家在黄浦江上盛放的那一船“白日焰火”,它好像更有一种原始和朴素的力量,在回答“艺术何为”。
影片最后,《天梯》的余光和人群尽皆散去。妻子吴红虹一个人站在远处,突然哭泣起来。蔡国强离开喧闹的人群,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成功带来的巨大兴奋之后,是万端感慨。

我既不是主流的那一套,也不是反主流的那一套
——专访艺术家蔡国强
“当你变成更有经验的动物,那种生猛劲头和皮毛的光泽却可能不如以前那么闪耀了。”

蔡国强在北京工作室
“艺术怎么样”
三联生活周刊:有些评论强调你独立于西方体系,好像你只按照自己那一套体系来做艺术。但我觉得,实际上你还是非常了解西方怎么想的。
蔡国强:他们知道我对艺术史问题的判断,我写过这方面文章。我认为艺术家是好动物,而不是动物学家。艺术家是实践者,是要去攀岩、去格斗的,所有思考其实要转化为你的艺术态度、你的理念及作品的力量。人们会以为我在做中国艺术家展的时候,会更欣赏那种材料上有突破的人,比如像我这样用火药。其实不光这样,而是方法论、艺术语言和艺术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多哈展览(注:2016年3月《艺术怎么样?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蔡国强担任策展人),你选择艺术家的主要标准是什么?看方法论?
蔡国强:对。或者说虽然他的方法论还没有形成,但他在整个求索的过程中没有丢掉这个主轴——到七八十岁才形成也不一定,这个很难的,但是要专心在这方面,不是只看市场或者利用中国政治一些主题就完成任务。
不管是从商业还是政治,大家都很知道西方希望中国做什么,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中国艺术家很聪明,这个聪明被我们的邻居日本和韩国都看得很清楚,他们就失去了对我们的尊重。也许我们有些人并无所谓,因为日韩市场不大,说得很土就是这个样子。可艺术的根本还是在于,你有没有创造出回答艺术史的答案。你的艺术确实可以包含政治的、社会的主题,你的成就可能会换来拍卖的价格,但是,不要把价格和价值,把政治主题和艺术上要说的内容混为一谈。
(多哈的展览)可能也让西方人有一点点不舒服。我想告诉他们,中国艺术家也可以不谈政治和社会,他们有自己的人生,有悲欣交集,有个人情感挫折,为什么非要说那些(政治社会内容)?所以《纽约时报》的报道题目你也看到,叫《重新定义中国艺术家》,记者主动写道:“在西方人眼中,中国艺术家要么像高古轩画廊(Gagosian)旗下艺术家曾梵志那样,是一种市场现象,要么就是艾未未那样的叛逆者。”因为这样会有事情好写。
我有时对西方人说得比较不客气,我说你们把中国看得太简单。当我们去议论西方文化和政治问题的时候,西方人很容易就提醒你,“这是很复杂的,难民问题啊什么问题啊都不是你们讲得这么简单”。但是当他们议论我们的时候,同样也会太简单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到美国闯荡的时候,有这种底气吗?
蔡国强:没有必要,因为我根本无所谓东西方问题。我在日本一直做人与自然、宇宙的主题,为的就是要告别那一种永远在讨论东西方的二元论。日本有西方参照的同时也有自己的文化,所以才形成了安藤忠雄、三宅一生这种人物。他们很清晰:我们不是西方人,从生理到心理都不是,可同时也不能只是花道、茶道、书道,不能只做日本文化这种装饰风,应该想怎么走才能既是国际的,又是有东方灵魂的。日本人一直都强调灵魂,如果你的艺术没有灵魂,在他们思想里面根本没办法产生同样的影响,但这样也使他们一直与世界保持一种有距离的“疏远感”。
很多事情造成我们的艺术不能跟西方一模一样。就像近代以来,我们哪个艺术家能在性的艺术表现上像西方那样的好?如果要做性主题的艺术,一定要扎根我们自己的生理和我们的情欲。

蔡国强,《大地》,2017,芦苇、木板、反光高分子膜;麦田:约8×19.8米;镜面:8× 20米,蔡国强躺于作品《大地》中,普希金国家艺术博物馆,莫斯科,2017年。赵小意摄,蔡工作室提供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你2013年在巴黎塞纳河上做了个50对情侣的“一夜情”,那么直白,跟你所说的“我们的情欲”相差很远。
蔡国强:我是孙悟空,我不是一般人(笑)。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好坏问题,而是你永远在试图做着一种“另外的”——日本人经常用这个词,也说“发明”。大量艺术作品你会被感动到,说这件作品做得真好,但不能马上认识到它“发明”了什么东西。其实艺术史很严酷,就是要“发明”。这样说话可能会让人感觉“太堕落了”,因为整个后现代主义就要规避掉这些。但后现代主义留下的几个大一点的影响,还是“发明”了,比如“发明”了艺术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还是太少了,那种让世界看看艺术其实可以这样做的人,艺术其实可以这样被嘲笑和玩耍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中国一直说要“好玩”、要“乱搞”,因为现在都太普通了。最近应该不少追求“我们离开政治吧,就做纯艺术吧”,但要小心,不过是美国艺术学校训练学生的那种做法而已。我觉得要有天马行空的人物出来,气质上根本是那种“崇拜尊敬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它们都是你的营养”,但又是,“我不是来当学生的,是来跟世界玩几下”的这种人。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自己初到美国是什么心态?
蔡国强:我到美国后就对日本人开玩笑说,“碰到对手了”。这样说话,日本人其实也不是很高兴吧。在美国我刚开始我自己那一套什么都要坚持。像我1996年参加Hugo Boss奖第一届展览,做了《成吉思汗的方舟》,作品里有个发动机,很吵,把隔壁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的影像吵得一塌糊涂(看不了)。人家给我一个英文的合约文件,我看也不看,在电梯上就签了给他。对方说:“我们开了几天会才做出的,你怎么连看都不看就签了?”我说:“第一,我看不懂;第二,我也不会执行。”然后我在人家展厅里面吃东西,被人家大喊了一声,就感到很不爽。后来慢慢都适应了,签合约也会交给工作室的人看,也不会在人家展厅随便吃东西了。当然我还会很在意,有哪些东西我不能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哪些东西是你不能改变的?
蔡国强:就是你的艺术不是要来讨好这个系统,你是要来破坏这个系统。当然破坏有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候是大获成功的,不一定每次都成。有时候我也在系统里面被规范住了,就像孙悟空不是永远都没有那个框,还是有那个框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看到的基本是你成功的例子,好像没有你说的这种“不是每一次都成”。
蔡国强:“成功”或“失败”这个词用得不好。我是想说,不是每一次都如我想象。就像在古根海姆回顾展这件事情上,弗兰克·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这个人(注:古根海姆艺术馆的建筑设计师)太牛了,历史上所有在古根海姆做展览的人都太在意去适应那个展厅,很想去迁就它,顺着建筑旋律做艺术。我是希望破一下,所以故意在美术馆的螺旋中庭吊了一批汽车和灯管,让它杂乱无章。但如果有点不满足的话,就是这个回顾展更多把我的艺术形式和方法论进行学术上的整理,但对我更深层的艺术态度和理念探索,尤其对看不见世界和精神的追求,讨论还不够。好在一个艺术家不只做一次回顾展,而是不断地,可以留给更多美术馆做。比如后来在洛杉矶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个展,我就写了99个故事,谈我与看不见的世界的对话,来帮助学术展开。

蔡国强,《撞墙》,2006,99只真实大小的狼复制品、玻璃墙;狼:混凝纸糊、石膏、玻璃纤维、树脂和绘制毛皮;尺寸可变。图为《撞墙》于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展览现场,西班牙, 2009,艾瑞卡·巴罗洪娜· 艾蒂摄,图像版权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所有
三联生活周刊:据说你这个展览,300万美元的成本为他赚了500万的门票?
蔡国强:对,展览很受欢迎,打破古根海姆美术馆视觉艺术家个展参观人数纪录,门票和衍生品收入加上赞助,扣除成本,还让他们(古根海姆)基金会赚了钱。这个展览巡回到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56万人看,那个城市总共才40万人。但为什么说还有一些不如愿?就是我自己的学术目标没有达到更高。
三联生活周刊:更高的目标是指什么,破坏艺术系统的愿望吗?
蔡国强:也不仅是艺术系统,也包括艺术史的问题。所以说艺术家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老了还在成长和发展,只不过有些时候是成长了却未必有没成熟的时候那么好。就像动物,当你变成更有经验的动物,那种生猛劲头和皮毛的光泽却可能不如以前那么闪耀了。
“我很会折腾”
三联生活周刊:当代艺术家一般习惯性地反对既成体系。但我发现从奥运会开始,你对和政府机构合作一直比较有兴趣,比如北京和上海做过APEC这样的纪念性艺术项目。
蔡国强:从个人角度,我经常说我怕谈这个,主要是怕把自己说得太正经。我其实没那么正经。如果说一个比较搞笑的想法,也许是因为我很喜欢凑热闹,把一些大事情都当成自己能够玩的,把国家大事做成自己的作品,喜欢往这种热闹的地方去凑。就像你刚才说的,一般艺术家都不这样,我为什么这样?因为历史上那些不一般的艺术家全是迎着上去的。
三联生活周刊:比如?
蔡国强:达·芬奇、拉斐尔、格列柯⋯⋯格列柯带着自己的画布从希腊出来,到意大利,再到西班牙,就想获得教皇或者皇帝的支持。问题不在于他们想获得支持,而是他们寻找到这个支持以后,又在里面摇摆和痛苦,这才创造出不朽的作品。伦勃朗也是,他就是很想卖画给那些商会,这才画了那个永垂不朽的《夜巡》。
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你要和普拉多美术馆合作绘画展览,第一个展厅是关于你和格列柯的对话。为什么格列柯给你这么大影响?
蔡国强:格列柯我有点弄懂了,其实是2008年奥运会以后。当时我有反弹,很自然的事情,吃了中餐就会想吃西餐,所以我带女儿沿着格列柯从生到死的地方走了一遍。我们带着他很多画作的印刷品,看他在哪儿画的这张画,眼前都看到了什么。他画过的山谷、城堡,我们都走了一遍。
大概有一个月,从他出生的希腊克里特岛出发。他来自于这种岛,很像我的家乡泉州,也是带着点迷信——当时欧洲的宗教很高大上了,但是他家乡的宗教有点像东正教,是比较偏僻的一种。格列柯去威尼斯的时候,很想接近一些主流,但很快就感到人家很看不起他。在意大利待不下去,又到西班牙马德里,想跟国王和贵族接近,还是扎不进去。后来他就到了托莱多,拼命想卖画给大主教,那里的主教比较喜欢他,所以他就一直留在那里,创作了很多作品。
走完这条路以后,我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他了。我也是从故乡出发,去上海,去日本,到美国,冥冥之中走了一条类似格列柯的路。然后我也是因为自己朴素的生命色彩,和与看不见的神明的关系,同整个社会潮流有距离。我就很喜欢这样。在中国你看这30多年有各种艺术运动,但很难看到我参与其中。

蔡国强,《河流》,2017,火药、画布;共13屏,总尺寸3×20米,图为火药画《河流》爆破瞬间,全俄展览中心(VDNKh)22号馆,莫斯科, 2017年。33工作室拍摄,蔡工作室提供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那时候你没有被艺术运动接纳?
蔡国强:不能说人家不接纳,是我不主动去跟人家凑。到日本后我又是一个外来者,像一匹狼一样,从东京以外的福岛的一个渔村,慢慢把日本搞得乌烟瘴气。最后我离开的时候,基本上日本有做当代艺术的美术馆都做过我的展览。我很会折腾。在美国也是,平时不参加人家什么事,人家的展览开幕我也不去,好朋友的才去看一下。
三联生活周刊:总是一个人,然后热闹地打开一个世界。
蔡国强:对。我总是跟自己开玩笑,总想着造一个大鞭炮要吓人一跳,结果没吓着别人,只是吓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别人评价你做作品气场很大。你怎么理解“气场”这种东西?
蔡国强:我是很在意风水上的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搞爆炸这种事情,全世界的人一听都会有一点紧张和担心,但是一见到我就马上不担心了,因为看起来我的样子彬彬有礼,说的话很有道理,怎么保护、怎么点火、为什么安全,会担心的事情都提前先说了,人家就很安心,说这个人看着有胳膊有手很正经的。还有一点太重要了:他们听完我的方案会怕,但不是怕出安全事故,而是怕如果不同意我的话将来会后悔——投了反对票,他自己也就看不到好玩的事情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想说,你总能激发别人强烈的好奇心而不舍得反对你?
蔡国强:对啊,我很喜欢自己有这种时候,就感到“我这个人还继续挺能整的”。一个人年纪大了,做久了,很多时候做的东西都是套路。最后自己也就在套路里面了,但他不知道。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39期艺术专访《蔡国强:在全世界“玩火”》。感谢王琪、周缘、肖楚舟对本文的帮助。部分图片由蔡国强工作室提供,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点击以下封面图
一键下单「新租房时代」
▼点击阅读原文,今日生活市集,发现更多好物。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