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切除丁丁的手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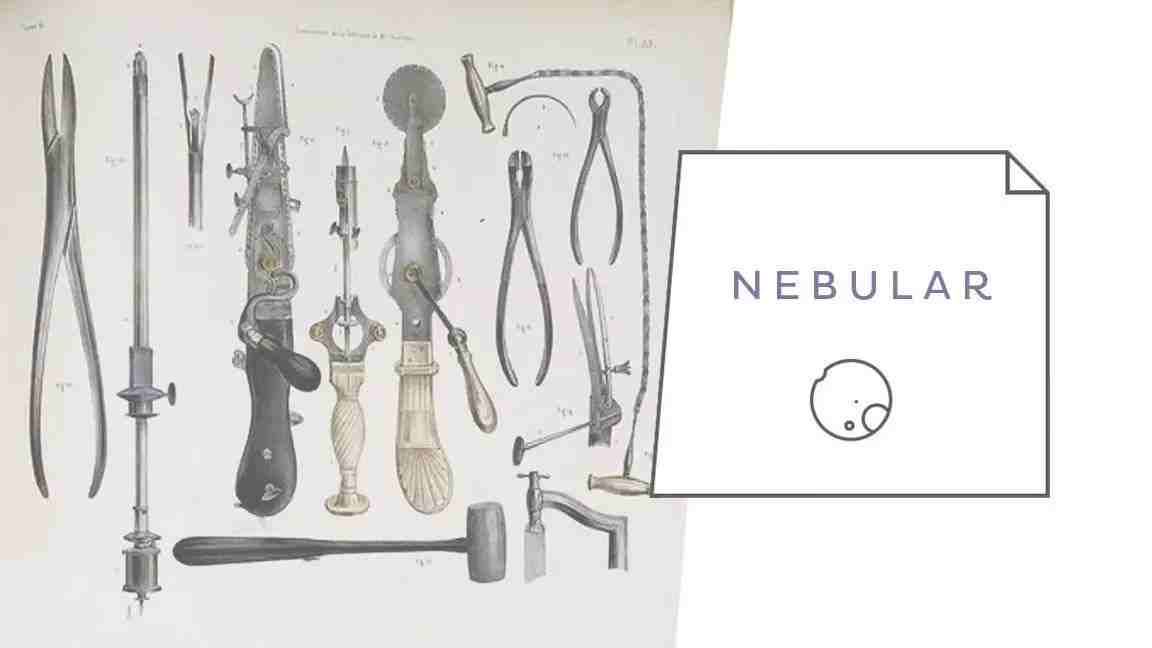


大家好,今天是5月20号。一个庸俗的,原本不是节日却被强行用来秀恩爱的日子。
祝愿情侣们今夜都能愉快的为爱鼓掌。单身的,well,我不知道能对你们说什么。(摊手)
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再也不想为爱鼓掌的男人的故事。
他不想变性,也没有性功能障碍,但他就是想移除掉自己的生殖器。这一要求被医生拒绝,医生说,“你的鸡巴不仅仅是你自己的,也是社会的,你老婆的。所以,你无权说切就切。你要获取精神鉴定,你的老婆和领导都要签署手术协议书。”领导说:“不要以为切了,就能一了百了。”
文章中并没有明说这哥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是不想被自己的下体操控上体,又或许这是一种通过直接抹去“中指”的存在,而对生活竖中指的终极方式。
在这个万众秀恩爱,满屏520的日子里,不妨也异想天开一下:
对人生和爱情厌烦到想要切掉生殖器是一种什么体验?

我想做一个切除丁丁的手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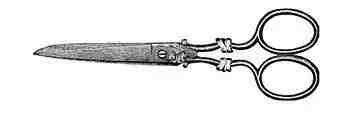
文|杨波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反常(id:fanchangshit)
a.
某日凌晨四时许,张良平把自己的老婆秦静香给肏了。他肏得不错。
如果秦静香没有记错的话,两人上一次过性生活还是两年前。并且,她还记得,那场浮皮潦草的性生活,是两人一边看优希麻琴刚刚升任步兵后的第一部作品《八头身的耻态》,一边过的。
尽管这两年来她还是跟其他人陆陆续续过过不少性生活,但当张良平把他的鸡巴主动探过来时,她的心里,还是涌出了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
令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第一次结束之后,过了不到半个小时,他竟又把她肏了一次。
这一次,他肏得依然很不错。
不用说,这一次她的心里涌出来的滋味,比上一次更加令她说不出来。
令她更加万万没有料到的是——
还好,第二次射完,张良平默默地哆嗦了一下,睡了。
b1.
同一天上午十一时许,张良平出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七医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徐州九七医院泌尿科第三诊室里。凌晨的两次性生活加上近三个小时的排队候诊令他看上去疲惫不堪,但这间诊室中的医生看起来似乎要更累一些。那医生佝偻着躯干,生死不明地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然后呢,然后他抬头看了一眼张良平。他的这个动作极其细微不明,如一个似打又似未打的嗝。张良平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看见了他就将头重新垂了回去。他已经累到几乎没有办法用脖子把脑袋撑起来好好看一眼他地患者的地步。那样子,就像一个年近百岁,瘫痪多年,脑萎缩到只有核桃那么大的老寡妇——童年丧父、壮年丧夫、老年丧子,在这近一百年里她业已听过无数噩耗,而现在再给她听一个后,她的样子。
“医生,你好。”
“嗯,你有什么问题?”
“不知该怎么说……”
“不知该怎么说也得说啊,是不是?”
“是。我想做一个切除鸡巴的手术。”
“鸡巴?你是说环切包皮吧。看样子你也快50了,这么大年纪的人还切包皮,罕见。”
“不是切包皮,医生,我想把整个鸡巴切了。”
听到这句话,医生终于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张良平。
“看着不像啊。”
“什么不像?”
“没什么。你的男性生殖器发生什么病变了?”
“我的男性生殖器一切正常,没有发生任何病变。我仅仅是想请你们帮我把它切除而已。”
“这位患者,请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吧。这里不是派出所,也不是伦理法庭。既然来都来了,就不要隐瞒病情,否则耽误了治疗,受罪的可只有你自己。”
“我真的没有隐瞒什么;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什么。医生,我为什么要向你隐瞒什么呢?”
医生摇摇头,叹了口气,他一边熟练地在张良平面前摆出这副“拿你们这些人真没有办法”的样子,一边戴上一双嫩黄色的弹力橡胶手套,唤道:“你过来,站在我的面前。”张良平应声而至。“把裤子脱了。”张良平把裤子脱了。“再往下,一直脱到膝盖下面。”张良平照做。
b2.
检查完毕,张良平看出来医生有一些不高兴,便赶忙将因检查时的触捏而勃起的鸡巴塞回裤子里,连连道歉说:“对不起,我的鸡巴自小就这么敏感,尿个尿都会硬。我没有别的意思,请医生你千万不要误会。”
医生摆摆手,依然板着脸,说:“我不是为这个生气——谁没有搞硬过一两根阴茎呢?特别对于从事我所从事的这个职业的人来说。我之所以脸色不悦,是为你感到可惜。说实话,在你这个年纪还能把生殖器保养得这么好的人,我见过的不多。如此出色的一副生殖器不知多少人做梦都想拥有呢,你却要把它切除掉。这真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我意已决,这种话就不必再说了。”
医生默默地看了他一眼,递给他一张名片。
“我的建议是,你不如先打一个疗程的雌性荷尔蒙试试。不过瘾的话,至多再做一个丰胸手术。我们医院整形外科的水平很不赖,你拿一张我的名片,可以打折。”
“医生,你搞错了……”

“先听我把话说完。这样就会有一个回旋的余地,到时候如果你觉得做女人还有没做男人带劲话,随时可以回头。否则,你想一想,如果把生殖器切除后再后悔,即便给你植个新的也肯定不如旧的用起来得心应手,更不用提绕这一大圈浪费掉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事后后悔的例子并非没有,其实不少。经我手的就不下十个。
“医生,我……”
“我什么我,不要总急着插嘴,先听我把话说完。你渴望拔草除根、以此明志的急迫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们都觉得自己已经是女人了,但你们其实并不是。如果真是,你也不会来找我做这个手术了对不对?所以,不如先尝一尝做女人的滋味再做决定吧——那滋味,可跟你想象中差距不小——别不信,这话,我以一名人类生殖系统专家的名义先撂在这儿。”
b3.
“医生,你从哪里看出来我想变性的?”
“你不是要求切除自己的男性生殖器吗?”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想成为一名女性,这甚至不意味着我不愿继续做一名男性。我只是雇请你们切除我的鸡巴,仅此而已,切完即止,不用再麻烦地安装任何别的器官。”
“你想当太监?”
“现在社会上有这个职业?”
“没有。”
“所以即便我想当太监,也无处去当。”
b4.
“不要贫嘴。那究竟为什么你想把它切了?”
“这个说来话长。医生,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我只是想询问一下,是否一定要回答你这个问题,你才能决定帮不帮我做这个手术?”
“不是。无论你回不回答我这个问题,我都不会帮你做这个手术。”
“哦?这倒是奇怪了,既然无论我回不回答这个问题,你都不会帮我做这个手术——那你问我这个问题做什么?”
“你质问得对,这个问题超出了我职业管辖的范围,你就当我没有问过好了。”
b5.
“抛开这个问题。医生,给我一句爽快的吧——这个手术到底能做,还是不能做?”
“你这是在为难我。”
“难?难道在技术上有什么难点?”
“切除男性生殖器?不要开玩笑了,莫说切除男性生殖器,就算在此之后再给你安装一副乃至几副其他男性乃至女性乃至不止于一种的其他哺乳动物的生殖器官,在技术上,对目前的医学来说也一点不难。问题并非出在这里。”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你想想,假设一个人到医院请医生把他的头切下来——别这么极端,即便他想做一个切除手指的小手术,而他的手指本身健康无恙,你觉得医院会同意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医生旨在救死扶伤,以维系及修复人的健康为目的,基于此,切除或伤害一个人健康的器官有悖其职业初衷。然而,若一个人部分的健康会导致其其他部分乃至整体的不健康呢?譬如他总是止不住用手指去抠自己的眼睛。前几天有一条新闻,说一个不幸陷入网瘾的中学生左手持刀,将自己的右手剁掉了。他想借此戒瘾。当然,在其他人的强逼和你们医生的伙同下,他的右手又被迫被接了回去。你或许想说,他的右手就算没有被接回去,乃至他设法将左手也一并剁了,他若想上网还是可以上,就像另一则新闻里,那位身残志坚、用舌尖敲键盘上网的无臂乡村女孩那样。但很可能还会有另一种情况发生——剁手对上网在客观操作上造成的妨碍,尤其是此事本身对其精神造成的刺激,果然有效地令他戒除了网瘾。至此,他当初对缺一只手和身陷网瘾这两种人生状态的比较和选择获得实现。我认为,包括他的亲属及你们医生在内的其他人尽可以不认同他的上述比较和选择,但无权干涉,因为他没有要去剁你们的手,无论如何,他剁的只是自己的手,并且,至关重要的是,这是他独自一人做出的决定。”
“住嘴。作为病人,你扯得太远,而且错漏百出,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我现在告诉你两个常识。”
“第一个常识是,医疗系统不过是整个社会体系的一处执行终端而已,它只能奉令行事,而不能有任何独立、自控的道德、伦理立场。它就像你刚才举的例子里那只砍掉右手的左手。如果说救死扶伤这个词含有某种情感成分的话,那它就不是医疗的本质——事实上,即便仅从字面上来解释,救死扶伤也跟我们毫无关系,甚至背道而驰。
“譬如紧抓计划生育那几十年里,因为但凡脱离母体的活体婴儿便在法律上获得承认为一条生命,于是怎样将那些二胎及以上的婴儿在脱离母体前弄死便成为医生的课题和工作。一些被计生人员绑回来的孕妇已届临盆,我那些仍将剪刀捅进她们的子宫将胎儿剪碎的同事们,我想,他们的生命观也许跟法律中的规定不尽一致,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下手时的冷静和专业。

“堕胎在我国获得授权,在有些国家则违法,这由堕胎对社会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来决定,而与医疗本身无关——同理,对于你,自我阉割对社会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个判断,医院既无权做,也做不来。”
“你搞错了。那位剁手中学生的手并不仅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整个社会;你的生殖器亦如此。你或许认为你的屎属于你自己,但当你将它屙在厕所时,城市下水系统就不得不对它负责;你若将它排在闹市时呢,环卫工人和心怀普适价值的市民们则不得不怒气冲冲地出面。实际上,你身上的一切器官,你的一切都不属于你自己,它们全部属于社会,这是第二条常识。由此,至少出于礼貌,当你你试图切除、伤害或改换它们前,请先去问问它们真正的主人是否同意。你的某个器官从属于社会的程度与你切除、伤害或改换其之后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成正比——简单说就是看一看你这么做之后对其他人造成的影响有多大。刺青、舌环这些对身体极其表面化的篡改都因没有事先征得社会的同意而成为反社会的暗示,却对比一下你的诉求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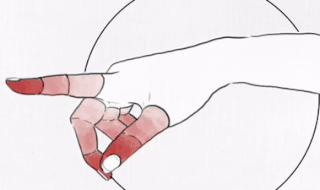
“你若跟那位中学生一样冲动,自己动手的话,或许在剁的那一刹那,你们各自独在于社会之外,但紧随着你们各自的器官啪一声落在地上,全社会便不得不过来收拾这个烂摊子,跟拾掇跳楼者的尸块一样。请千万不要自称可以自力自为、自得其善,自己种的苦果自己咽——你根本就咽不下去,更何况,你们自残的目的就是明里暗里地去让社会负责——你一早就清楚你的器官是社会产品,于是将之毁掉以让其他人感到惊吓、难堪,乃至造成混乱。与之相比自杀反而要好一些,至少那具尸体不会跑出来为自杀的后果添油加醋。所以,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迟迟没有将自残列入刑法。
“还好,你没有自己动手,而是求助于医院,这意味着你将这一自残行为从一开始,在决定和操作之前,就纳入了社会操作之内。你个人对此的决定不过是一个动机,而算不上决定。接下来,你若坚持要在体制内摘除你的生殖器官的的话,你也必须取得社会的同意。”
b6.
“那么,我怎样去征得社会的同意?”
“你有没有结婚?”
“有。”
“你想一想,在切除掉生殖器之后,作为一个没有生殖器的丈夫,你会不会对你妻子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
“多少会有一点。”

“既然有影响,她的书面同意就是这一手术的必要前提之一。依此逻辑——一个人多数生活在家庭和工作之中,这也划定了他的影响范畴——你老婆代表你的家庭,继而有你工作单位盖章的书面同意则是另一个必要前提。
“另外,除了家庭和工作之外,还有一个人势必将会遭到此事的殃及,且无论跟你的家庭还是同事相比,其受到殃及的程度都要剧烈得多。你想一想,这个人是谁?”
张良平想了想,说:“我想不出来。”
“这个人就是你自己。”
“什么?医生,不要开玩笑了。我立刻就可以写一份同意手术的声明。”
“在写这份声明之前,你必须向我证明这一声明是具备社会效力的。即,你须去找精神科医生开具一份证明你的精神系统健康到足以令这一声明具备社会效力的书面证明。”
“为何做出自阉的决定,你已解释得足够清楚。你的这些解释不仅逻辑通畅,甚至令我颇有感触。请你不要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我很可能也会做出跟你一样的决定来。”
“泌尿科的医生想必已经跟你解释过,你的器官并不属于你自己,而是属于社会的道理。不止于此,你的精神系统也具备同样的属性。你要明白,无论医身还是治心的医生,他们对于你的病变是否会给你本人带来痛苦毫不介意。治疗不过是你的痛苦在社会的反射的再一次反射——通过这一系列反射,包括医生在内的所有社会参与角色的目的是,你的痛苦不会再对社会造成任何负面作用——为此,这一过程虽多数终结于你的痛苦的减轻甚至消失,却也有部分终结于你的痛苦的转嫁或加深。”
“依此理,对于精神科医生来说,判断一位患者的精神是否正常,与这一精神有没有为该患者造成痛苦无关——常见的情况是,精神异常者非常愉快,他们仅是在精神正常者眼里显得痛苦——毋宁说异常罢了——而是由可否将这一精神状态纳入某一既定的社会精神类型来决定。换句话说就是,你是否罹患精神病取决于你是否跟其他人一样。”
“变性人现已逐步获得社会的认可。你如果穿了一条裙子,哪怕文个唇线来,事情也会好办得多。那样,我便有理由将你确诊为尚未但一定会失志于做一位女性的性倒错患者;你尚被你自己瞒在鼓里——之所以已无法忍受继续做一名男性的痛苦,是因为你想成为一名女性。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你也反复强调,没有一丝愿跟我串供的意图。”
“也不能怪泌尿科古板,他们这么做,或许来自经济上的考虑。所谓商业上要不不要买,要买买全套的霸王条款——摘除阴茎又花不了几个钱,安条阴道可就贵了。”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人,之所以不相信女权主义那一套,因为我知道有一点女人永远比不过男人。这一点就是,谁也没有办法有效地阉割女人。只因女人的生殖器天生跟男人不一样——它不是便于切除的噘出体表的一骨嘟,而是蜿蜒拧巴着陷入体内的一眼深洞——鸡巴割了就没了,屄洞挖了呢,则会留下一眼更深更大的洞。”
“不要跟我提什么切除卵巢。切除卵巢只会令那眼无法切除的屄洞更加可笑而已。你知道一个基于切除了卵巢而得意洋洋地号称业已完成自我阉割的女权主义者最可笑的地方是什么吗?她最可笑的地方在于她仍可以被肏。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对于肏她的男人来说,她是否完成她那自称的自我阉割连个屁都不算。”
“张良平,尽情享受你的特权吧。”
“太监也有性欲。不要以为切掉鸡巴就能一了百了。良平,不瞒你说,大概二十年前吧,我也曾涌出过跟你现在一模一样的念头,且激烈得多。我那时根本没有想过去医院,甚至恨不得跟魏忠贤一样,恶狠狠地,找个磨盘,再找块青石,把它砸碎。现在有时回想起当年对自己的鸡巴的那种不共戴天的恨意,还有些不寒而栗。”
“幸好对它们的迷恋转移了这种恨”,领导指了指摊开在他桌面上的一堆书,“在这世上,没有比哲学更能有效地取代鸡巴的东西。”
我们给大家开一道脑洞题:
情既相逢必主淫,说的是爱情这东西就是性的引子。不然那么群老爷们谁爱贴着姑娘家家的捏着嗓子发嗲呢。
性没了,要这引子有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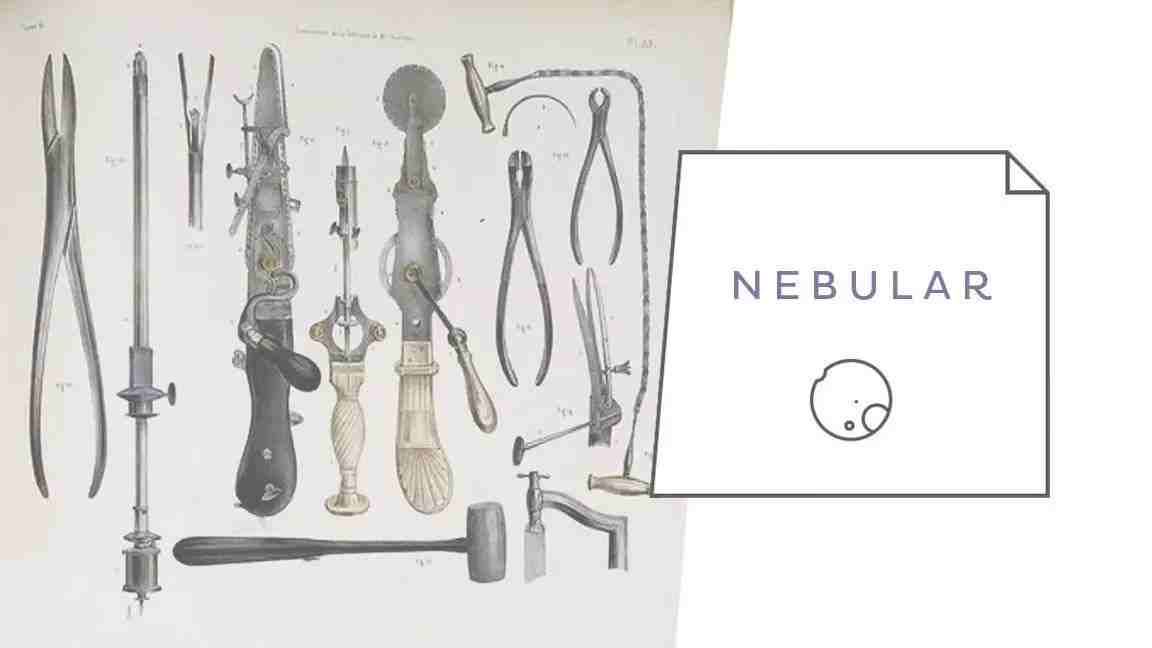
作者:杨波
美编:阮佳镱
图片来源于giph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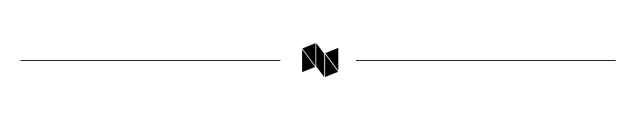
北美新媒体平台
N E B U L A R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