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荷华堕落


全文共6073个字,平均阅读时间6分钟。
“护照和那个什么20都带了么?”
“I-20,带了。”
“落地了换上卡就给我跟你爸发个微信。”
“嗯。”
“行,注意安全。去了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
“知道了,登机了要,挂了,你快去忙吧。”
张洋慌忙地挂了母亲的电话,他确实在北京首都机场,但他手中的登机牌目的地冷峻地印着“成都”。他所乘坐的飞机没有像母亲知道的那样去往美国,事实上,在被美国拒签了三次之后,他可能十年之内都无法入境了。“我两个多月之前就被学校开除了,没敢跟我妈说。”
飞机从北京到纽约要飞14个小时,他还有14个小时可以失踪。14小时之后,他必须要给自己没有去学校找到一个合适的说词,一个不能真实的说词。
张洋21岁,本应该是美国爱荷华大学商学院大二的学生,却因为成绩不足2.0(满分4.0,2.0为及格)在他大学中的第一个暑假被学校开除。他收到邮件时人在郑州,家还和他记忆中一样,“燥热,少风,灰蒙蒙的”。
他记得很清楚:那个凌晨,邮箱里有48封未读邮件,很多是广告邮件,图片配色鲜艳。模特明快的笑容里埋藏了一封信,信中语气平淡,学校政教处惜字如金,“Yang Zhang同学,我们抱歉的通知您,您已被我校从系统中清除,请…”
他只读到这里,就关掉了邮箱,在之后的两周里,他一次也没有查过邮件。他苦笑着说,“不敢细看。”不敢细想这意味着什么。
成都是张洋最后一个战场,在他意识到被开除这件事已无法逆转之后通过互联网找到了一个美国的中介,咨询老师信誓旦旦的向他推销了解决方案:重新申请一个社区大学,在社区大学上一年学再转到一个不错的学校,他们中介和很多社区大学都有合作。他最后选择了西雅图的一所学校,中介费是5000美金,这本来是他妈给他的下个学期的学费。
可F1签证申请被拒了,连续三次。中介解决不了签证的问题,也不会退款。
张洋最终的幻想寄托于一个假的旅行计划,他在网上预付了全程的酒店,租车以及大巴车票等费用,准备去申请旅游签证,在这段日子里,张洋每天晚上都向主祷告,“先回去,只要让我回去就好。”他是个还算虔诚的基督教徒,“事实证明,神救不了你。”
旅行签证的申请还是被拒了,这是第四次,他站在成都领事馆路边,“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原来我没有地方可以去。”

18岁的孩子
张洋觉得,自己的留学生活是空白的。好像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躲在宿舍里看电影,没去上课,不知道要干什么。”
又好像,说不太清楚。
2014年8月,他所乘的飞机从北京出发,在太平洋上横向地划了一条弧线,15个小时之后,落地芝加哥,这是张洋第一次到美国。正值开学季,芝加哥海关外面挤满了赴美留学的年轻人,那一年,他就读的大学录取了1000名中国新生。
在他们的想象里,美国是开放的,自由的。张洋不明白这两个词的深意,只是对这种生活充满向往,“我们学校的招生宣传册上就这么写,给孩子一个机会自由地成长。”
“我从小成绩就不是很好,中考特别难熬。我感觉最初选择出国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逃避的成份在里面。”不用经过高考的考验就能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机会,而且在2010年,国际高中的招生门槛相对当地的重点高中来说低很多。“我妈当时只关心送我出去钱够不够,钱够。”那收获大于付出,是赚了的。
“留学完全是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某美国大学国际学生办公室的老师强调,“每个人适应的速度不同,但是,有很多学生在来之前没有意识到困难所在。”
“和我想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以为大学过的应该是那种,动次打次的生活。”张洋所幻想的,是一种在心理上丰富积极的生活。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学校常邀请美国的优秀大学生来校交流,学长学姐精心打扮,把他们生活中最精彩的部分挑选出来,集结在十分钟的演讲里,张洋听得热血澎湃,“那时候觉得最好的人生就是过上他们那样的大学生活。”
事实上,“留学生”看似是一个群体,但这个群体数量之庞大,足以包含无数完全不同的圈子。有一群人坐实了国内人对留学生的偏见,跑车,奢饰品,日出一千刀。有人把自我降到最低,试图从美国生活里汲取他所能吸收的所有,他们西装笔挺的,只会和你在电梯间相遇。“我一会儿要去参加一个meeting,这周还有4个project要due,你要不要来join in啊,介绍你认识一些人呀。”
也有人把自己过得和美国毫无关系,外卖游戏,出租的房子里活飘着一股高中男生宿舍的味道。
圈子之间相互视而不见且难以跨越,这种分层的核心是自我判断。是认识“我”在过去的18年里,最终成长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洋面对的的是对于他来说过难的课业,并且因为对自己认识的模糊,找不到自己所属的圈子。他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也丧失了对生活的积极性。
大学上了一年,张洋很难回想起自己都上过哪些课。他每天躲在宿舍里,一天可以看3部电影。长达八季的美剧可以一集不落地全部看完。他经常翘掉周五的课,坐6,7个小时的大巴跑到别的城市去找高中同学叙旧。热水化开一包小肥羊的火锅底料,中国超市买的羊肉卷一泡进去,红都没退完,就被几个人抢到碗里,那是他最开心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是高兴的,但是每个人回到房间之后愁些什么,不会跟别人说。”
大一的最后几个月,他连考试都放弃了,本该在考场的他选择待在宿舍里看着分针指着数字画圆,然后点一份水煮鱼外卖。
孤独,空虚,逃避,他觉得自己被某种情绪控制了。他在朋友圈里分享了电影《被解救的姜戈》里的一首歌,“面对恐惧我发现了真理,没有人告诉你前方有路。但我已走得太远不能回头。”
“说起来像个废物。”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如此。
我问他,“你知道会有人说,能力不足或者课程太难都是借口,学校会给成绩不好的学生提供很多帮助。你如果更努力一些,及格不是一件难事。”
张洋坐在我对面沉默了一阵,回想起这些事儿时很坦然。被开除之后的日子改变了他,让他学会了理性地分析自己犯过的错误,“你说得对,我那时不明白丰富的生活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张洋高中所读的国际班里23个人,21位都来了美国读大学,一年之后,有9人被确诊为抑郁症。和张洋相似,在第一学期就面临被开除危险的,还有梁爽。她将自己大一面临的困境归结为,“步子太大,扯着蛋了。”
“我本来申不到这么好的学校的,不过我们班考ACT是抄的。”作为大学申请中对于学习能力的主要测试,他们的考试地点就在自己学校的会议厅,考位可以随便坐,桌子前后之间的距离很窄,胳膊伸直了能够到前面同学的卷子,而监考老师是他们学校初中部的英语老师。“卷子我都没看完,成绩比我一年来所有模考的成绩都高。”
刚进学校的梁爽和张洋一样,什么都学不会。“开学家具都没置办齐就考试了,五道题我一道都看不懂。”学期结束之后她同样被学校警告,若没有明显进步,将被开除学籍。她形容当时的自己,虽然18岁成年了,但能力和思维都差很多,好像没有什么成长,“一个被时间吹胀的孩子。”
“知道自己要被开除的一瞬间,好像一下就长大了。”
大一的第二个学期,梁爽花了4天的时间,在评分网站上从学校几百门课程里筛选出来了五门最好拿分的。“我起点GPA太低了。虽然这些水课学不到什么,但是没办法,好课内容太难,我还应付不了。”
留学本来就不是一个改变生活的动作,留学是生活本身。如果你本身是一团糟,留学会完整地呈现,并且放大它。梁爽以前期待毕业的自己是一个具备专业技能和知识的人,现在她觉得大学最大的价值在于教育她,大学不重要。
“生活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积极一点换专业,咬牙学习。适时选点水课。走偏的买答案,找代考,代写。自担因果呗。其实出不出国没什么区别,你所面临的、必须要解决的仍是那些最基本的问题:你未来想要干什么,你能不能克服你性格上的怯懦,你愿不愿意改变。如果真有什么不同,大概就是学费太贵。”
和张洋一样,梁爽也一直被灌输着一种思想,美国的大学尝试成本较低,今年顺利以荣誉学生称号升入大三的她觉得任性的尝试有一个前提,“你要有钱”。
截止2017年,她所就读的学校学费一路飙升,比起她入学的时候,整个大学的教育资费已经上涨了20万人民币。“这些钱不是我的,我觉得自己花了父母这么多钱,选了水课,没学到什么,也挺埋怨自己的。但是没办法。”

被美化
张洋学校的教授在一次招生会上这么描述,“一个优秀的国际学生要有一定的学习能力,语言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应该如何考核,“比如我们要求学生提交高中的学业成绩,中国的高中是很严苛的,如果你能在高中成功,那你一定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还有他们如何认识自己的文书,也能从中看出他们的思想是否成熟到进入美国大学学习。当然,还有语言成绩。”
“我们当然希望提供优质的教育,而考核标准是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判断他们是否能够适应我们学校的生活。当然,现在我们收到的申请质量越来越好,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多。”2016年,总共有11万9千人申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托福平均成绩为111分,SAT成绩2200分。申请学生的质量和数量仍在持续上升。
有些事情,是这位教授所不完全了解的。张洋位于全年级前百分之五的高中优异成绩是自己优化过的。学校老师对他的评价也是自己写,由别人翻译的。申请文书,更是留学中介的专职人员根据“丰富的经验”撰写的。而张洋,只是2014年15万留学申请中最普遍也没有特点的一个。
你在某雅思培训机构留下电话,下一周可能会有五个中介跟你打电话咨询你是否报考了雅思,对留学申请有没有兴趣等等。
除了文书之外,核心考试买卖答案和代考是中介的另一条业务线。因为无法核实考生成绩的诚实性,2017年2月,美国大学理事会取消了去年6月和11月除美国本土以外所有地区的SAT考试成绩。
高考有他的弊端,美国大学这种申请方式也有,但如果直面申请作假,就必须要直面申请这种方式在中国招生压根行不通。这个问题没有办法根治。“我个人就遇上过一个拿到了申请后因为材料不属实被开除的案例,但是因为每个孩子都会申请5到7所学校,所以换另一个学校入学就好了。”
中介工作的核心思想,用现在的互联网术语说就是一种用户思维。他们基于自己的经验,站在大学招生的角度思考,如何才能将孩子打造成一个会被看中的申请者。“我也是机缘巧合才做中介的,西北大学英语专业毕业之后一直在做房产销售。10年我们城市房地产开始不好做了,反而留学咨询开始大爆发。如今干学服已经6年了。”
对于中国家庭来说,选择将孩子送出国读书,早已不是一个有钱人会选择的小众的教育方式了,在一次国际班招生分享会上一位家长咨询梁爽,“阿姨问你啊,阿姨想把房子卖了送儿子出国,你觉得怎么样?”
梁爽说,“我听完都傻了,卖房这么大的事情你问我干嘛。”事后她又想了想,“好像也只能问我,可能是我们能接触到的,对留学认识最深的人了。其他留学产业中的人都有利益相关的问题啊。”
把美国大学美化给国内的家长们,这是中介除了将孩子美化给美国大学之外的,第二个工作。
中介老师解释,国内的教育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对于每一个家长来说,孩子长大了,没有时间等你优化和解决。比如孩子的创造力,比如教育资源不平等。“每个家长来咨询的核心其实只有两个问题:一,出国对孩子好不好?二,出国多少钱?我们就说,出国好。要是对孩子好,多少钱都值得。”
事实上,对于很多国内的留学中介来讲,出国意味着什么,有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好,是不是一劳永逸地用钱解决了教育的一切问题,他们不了解。一位留学咨询老师一个学期可以同时负责4到5个学生,他们在与中介相处5至8个月之后基本就会完全不联系,和中介鲜有交集。
他们看到的是存在于朋友圈的“假相”。在冬天中国被雾霾笼罩的时候,美国大城小村的蓝天白云,春假里留学生世界各地的旅行照片,纽约的高楼,坎昆的大海,加州的阳光,和奥兰多迪士尼里一张张毫无忧虑的笑脸。这些都被他们存下来,用于展示给下一届学生和家长。
最后,迎来送往的一届届学生,和当年的梁爽及张洋一样,幻想着“自由”,满心期待地选择出国。并支付4万到10万费用,换取“专业”团队的申请服务。

“窄门”
第四次申请美国签证被拒之后,张洋回到老家。他骗自己的父母,“签证被拒了,去不了。”
妈妈帮着他找了一个工作,每天早上从城南坐一个小时地铁到城东,赶在八点半之前上班,晚上五点下班再坐一个小时地铁回家。主要的工作是更新公众号和网站,也干一些销售的活。“公司就分为销售部和财务部,员工基本都是老板的亲戚,一个月拿3300块钱,根本不够花。我们公司卖一些工地用车,一辆车两三百万,老板说卖出一辆车就给你奖励1000块,但是我干了六个月,一辆都没卖出去。”
他也想过,从此就混社会算了,那么多没上过大学的人不也成功了吗?可转念一想,他有什么能力能在这个社会上活下去,“我刚上班的时候和同事在楼梯间里面抽烟聊天,我那天带了一包大苏,随手发给他们。他们都没抽过,觉得48块钱一包的烟,太贵了,老板才抽。我就想我自己,要是大学没毕业怎么办呢?”
他删光了十月之前所有的朋友圈。美国的生活对他来说已经很遥远了,虽然算算,也只是一年前而已。“大学认识的所有朋友都变成了朋友圈点赞的关系。“
张洋觉得自己第一次,开始“迷茫”了,他认为这是件好事儿,迷茫代表着自己开始思考,有意识了。“我的大学生活空白,就是因为无意识的生活促成的。”
后来在教会里有一个之前在中介供职的姐妹告诉他,其实这种情况可以考虑考虑去别的国家——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很好进的。”
他那个周末放假就联系了城市里牌子最大的中介,网上的地址描述是从地铁D口出来,经过LV和Gucci的门店,看见Chanel右拐,走到头,坐电梯上8层就到了。他第一次去,只谈了两个小时,就觉得重拾了希望,“特别顺利,中介一听我的情况就介绍了几个和我相似的案例——被美国大学开除,通过他们中介,成功转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或者新南威尔士大学,都是世界一流学府。中介费一万多块钱,我妈想都没想就把钱交了,反正所有的可能都比现在这样好。”
交钱后不到一周,他收到了悉尼大学有条件录取的通知书,只要他补递一份雅思的成绩单就可以入学了,如果成绩不够6.0,只需要再读三个月的语言。
他当晚就更新了朋友圈,“已成功转学至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感谢之前认识的所有人,我们有缘再会。”因为没有国内的高考成绩,他必须要再上一年预科,学费是一年三万澳元,合不到十五万人民币。
张洋愧疚地笑笑说,“没有想到这么容易,但确实是最好的结果了。”
未来在新的学校,他还是想进商学院,也打算学习哲学,“怎么面对自己,这件事很重要。”
国际高中毕业两年,他再也没有回过学校,“我为了在美国念大学准备了四年,可我好像并没有准备好。”他有同学暑假回国,相约回去看看,他拒绝了。后来听说任课老师大多都换了新的,认识他们的已经不多了。规模也从一届一个班,扩张到了一届五个班。之前的班主任见到他们特别高兴,一番寒暄之后说,“我们学校出来的学生,和中介送出去的学生不一样。学术能力都没什么问题,都能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她说话的时候,旁边坐着高一新生的家长。
我最后问张洋,你后悔最初出国吗?他好一阵没说话,然后开口,“《马太福音》记,‘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毁灭,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可能美国这个门对我来说太宽了,路也太大了。”
2016年7月,正值盛夏,他再一次站在了中国边检的蓝牌之下,等待他的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四年的大学学业,和澳大利亚的冬天。
本文收录在NEBULAR第二期杂志
点击下方图片获取更多杂志详情
▽


作者:鸵许
美编:阮佳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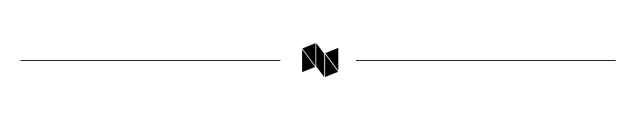
人|故事|經歷|青年態度
北美新媒体平台
N E B U L A R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